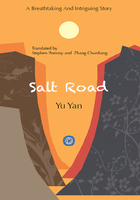爱酒,几乎是这个星球上所有人类群体的共性。尽管各个民族或国家可以如数家珍地宣称,是他们最早发明或发现了某某、某某玩意儿,却无人敢说,是他们最早发现了酒。因为,凡是有人食用粮食的地方,自然就会酿出酒来。当哥伦布在美洲东海岸的巴哈马群岛第一次遇见印第安人时,就发现他们也有酒。
酒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从皇家的盛筵到普通百姓的家宴,酒永远是筵席上最关键的凝聚剂。从文人雅士到绿林好汉,无不都为酒神魂颠倒。陶渊明爱酒,李白更嗜酒;画家无酒绘不出好丹青,书法家无酒挥不出好笔墨。但中国人爱酒,是重在气氛,重在那酒精的威力,而不过分讲究酒质的高低。虽然李白曾赞赏过汪伦和纪叟的酒,但那主要是在抒情,也带有些夸张,那酒则未必真的就是极品。中国人对酒质的评定基本上是以种类、牌子和陈期为主,很少去追究那酿造的具体年份。因为中国古代的酒基本上都是用粮食酿制而成的,不同年份的粮食的区别主要是产量的多少,年份的差异对酒质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这里想说的“白马酒庄1947”的小故事,不太可能来自中国的美酒。
欧洲的酒大多也是用粮食酿造的,特别是俄国、北欧和英国。譬如说,苏格兰著名的威士忌就是用大麦(barley)酿制的,而俄罗斯最著名的伏特加则是由马铃薯、玉米、小麦和大麦许多杂七杂八的粮食酿制的。所以威士忌和伏特加除了陈期的长短外,生产的年份不重要。苏格兰的威士忌和俄罗斯的伏特加虽算是名酒,然而同由葡萄酿造出来的法国葡萄酒(酒精含量一般不超过15%,以法国西南的波尔多最著名)或法国白兰地(酒精含量在28%以上,以波尔多北边的科涅阿克Cognac最著名)相比,则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了。就连最老到的伦敦品酒大师,也都会把眼光盯住波尔多和科涅阿克,不会去顾及什么苏格兰和俄罗斯。
葡萄酒最大的特点,就是十分依赖当年的气候,不单是葡萄生长期内的气候,也关系到葡萄酒发酵期间的气候,甚至还关系到把几种不同的葡萄酒掺和时的成分选择和比例。因此波尔多每年的极品葡萄酒就像指纹一样各不相同。葡萄酒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随着陈期的延长,它会慢慢地“醋化”,过了几十年,最后就成了一瓶醋。这就是为什么葡萄酒必须保存在14度左右的低温酒窖里的道理。一般的葡萄酒,如果没有特别精心的保存,那么不到二十年就全成醋了,就如同中国的黄酒会变醋一样。只有烈酒才能够保存几百年。
一次,亚洲的一位品酒大师拜访了英国最著名的葡萄酒评论家和品酒权威休·约翰逊,问他一生中所品尝过的美酒佳酿中,是否真有一瓶酒能算得上是举世无双的。约翰逊毫不犹豫地回答说:“ChateauChevalBlanc1947!(白马酒庄1947)”他回忆起那个晚宴上,当侍者郑重其事地把斟着仅仅是杯底部分那一点点“白马酒庄1947”的高脚深酒杯小心翼翼地送上来,每个人端起酒杯,先晃动一番,然后用鼻子闻香。那一刻,整个房间鸦雀无声,所有的客人全都沉醉在销魂的酒香里。名不虚传的“白马酒庄1947”被誉为二十世纪的极品。有人甚至还夸张地把它说成是有史以来的极品,这就有言过其实之嫌了;因为葡萄酒很难保存过五十年;既然没有人能体验一百年前的葡萄酒,那么就很难把“有史以来的极品”这桂冠送给“白马酒庄1947”,尽管它有可能是如此。
要说波尔多的葡萄酒,哪怕是几厚本书也讲不完,所以不得不长话短说。
法国西南靠近大西洋的波尔多地区历来是穷乡僻壤,这里的土壤贫瘠而多石。但这种劣质土壤却可以种植葡萄,加上这里南方的夏季炎热,阳光充沛,种植的葡萄特别适宜于酿造葡萄酒。经过数百年来对葡萄的精心栽培和酿酒工艺不断臻于完美,波尔多已经成为葡萄酒的最高象征。波尔多的葡萄园区主要分布在从东边流入吉伦德河湾(Gironde)的多尔多尼亚河(Dordogne)的两岸。从十八世纪起,它的南岸一直是优质葡萄酒的主要产区,到十九世纪中叶的1855年,在波尔多地区正式定下的五种等级里,北岸圣艾米隆(SaintEmilion)的白马酒庄(ChateauChevalBlanc)还被列在等级以外。然而它的崛起也出人意料,经过潜心的栽培和研究,白马酒庄在1862年伦敦大赛和1878年巴黎大赛中两次获得金奖,从此独占鳌头。波尔多的红葡萄酒是用几种不同特色的葡萄掺和酿制,以调和香、味、酸、甜和涩的平衡综合效果。一般来说,红葡萄酒大多是以赤霞珠(Cabernet-Sauvignon)葡萄为主要成分酿制,但白马酒庄的红葡萄酒却是以香味为特色的品丽珠葡萄(CabernetFranc)为主要成分,约占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是本地的梅洛(Merlot)葡萄。除1862年和1878年的桂冠外,白马酒庄在1893、1899和1900等年份的佳酿都引人瞩目。
谁都没有料到1947这个糟糕的年头会爆出举世无双的极品来。虽说葡萄需要充沛的阳光,但这一年的夏天实在是太热,以至于许多葡萄被热得枯死,收成下来的也是残败不堪。葡萄生长要阳光,但葡萄酒的发酵酿制却不能热。偏偏这年九月的发酵酿制期间也是热得如伏天一般,白马酒庄的人员不得不同波尔多的屠宰场和鱼市场抢冰,用来为酒窖降温;甚至因为冰不够,就病急乱投医,把冰块直接扔进发酵的酒缸里;这可是酿酒的大忌,因为冰会把酒冲稀。总之,这一年可算是一团糟。然而,葡萄酒的好坏,往往不是当年就可以显露出来的,它至少得陈上几年才会露出庐山真面目。当人们在来年抱着怀疑打开酒瓶,竟然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惊喜。上面提到休·约翰逊品尝的“1947”没有说是陈了几年,但从记载来看,陈了三十年的“白马酒庄1947”还魅力不减当年。它成了一个神话。当年曾有多少葡萄酒迷们,他们的最大愿望,就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品尝到“白马酒庄1947”。物以稀为贵,随着酒迷们对这世纪极品梦魇般的追捧,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瓶“白马酒庄1947”的价格已经高达上万美金,却依然挡不住酒迷们的疯狂。
到2000千禧年,“白马酒庄1947”已经陈了五十三年。对于绝大多数的葡萄酒,五十三年已经足够让它们完全变成醋。但奇货可居的“白马酒庄1947”则当然地受到了保存者的分外呵护,居然还能喝。当然,五十多年的葡萄酒,能喝已经算奇迹,至于香和味还能够保留多少当年的韵味,就难说了。
在亚洲一座世界大都会里,付得起万金的酒迷们依然不肯放弃那个梦。他们从2001年初,就开始了寻觅“白马神话”的努力。先由几位头面人物出面委托法国葡萄酒代理商为之觅宝,盼望着能从海中捞起一个月亮来。代理商为慎重起见,表示除非白马酒庄正式表明愿意帮他们进行鉴定,否则他不能接下这价格五位数的生意,因为他不愿为一瓶变成了醋的葡萄酒而失去朋友。
不到两个月,就有了“白马”的下落,经法国波尔多圣艾米隆的白马酒庄开瓶鉴定,确证为真品。但酒龄过了半个世纪,已经蒸发掉了一点;他们由专家负责,用酒庄珍藏的原酒把瓶子添满,换上新塞子,贴上新酒签,并指示说,要等半年后才能开瓶。这匹白神马终于在年底前运到了亚洲这个东方大都会。
第二年正好是农历马年。马年伊始,六位“白神马”的痴迷们聚在了一起,终于可以一品那梦寐了一生、折腾了一年的“白马酒庄1947”了。这瓶身价数万美金、如“上帝眼泪”般珍贵的神酒被小心翼翼地分成了六个小半杯,除酒瓶底内还残留一些酒渣,那琼浆还相当清澈,色泽偏红,完全不像一般老陈红酒的铁锈色。这白神马为马年带来了最好的祝福。问君其味如何?似乎都没说。“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但其中一位记者毕竟城府不深,居然私下说出了这样的扫兴话:“那些酒评家废寝忘食、搜遍枯肠得来的形容词,都不过是些花言巧语!”
这位记者其实只说对了一半。他要是能早二三十年圆梦,断不会如此失望。因为,这瓶五十五年的“白马酒庄1947”虽然还没有完全成为醋,但也差不多是醋了。我相信,休·约翰逊当年品尝到“白马酒庄1947”那一刻的体会,绝不会是花言巧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