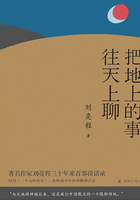作为短篇小说家的门罗
她选择了短篇小说,尽管这种艺术形式常常被误以为比不上长篇小说,她却将其淬炼至完美。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
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82岁的加拿大短篇小说家艾丽丝·门罗,颁奖理由非常简洁:“当代短篇小说大师”。在诺贝尔文学奖100多年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颁奖给短篇小说作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门罗本人在得知自己获奖后则表示出乎意料:“我知道我在候选名单上,但我从没想到过会赢。”随后门罗对加拿大媒体表示,希望自己的获奖“能让人们把短篇小说视为一门重要的艺术,而非一个你写着玩的东西”。
纵观门罗的文学生涯,短篇小说创作是她始终如一的坚持。她至今共创作了14部短篇小说集,近200个短篇故事。除了诺贝尔文学奖,2009年门罗还获得了曼氏布克国际文学奖时,评委会一致认为:“近乎完美的写作……作为短篇小说家,艾丽丝·门罗的每一篇短篇小说作品所具有的深刻感、哲理性与精确度,大多数长篇小说家都需要借助主人公从生到死的漫长一生才能够表述。”而2012年的崔林文学奖亦强调,“门罗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能力,能够以简洁、意蕴深长、且超越时空的故事带给我们生活的启示。”除此之外,门罗也被誉为“作家中的作家”,她的作品整体质量相当统一,具有极高的艺术感染力,其忠实的读者中包括了约翰·斯坦贝克、乔伊斯·卡罗尔·欧茨以及A.S.拜厄特等众多著名作家。其中,美国女作家辛西娅·奥兹克第一个将门罗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契诃夫”,并且大胆预言:“(门罗)将会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更长久地被读者记住。”而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则在评论中这样感叹:“她的故事具有其他作家长篇的深度,表达着伦理、情感以及历史的各个方面。”A.S.拜厄特更是炽热地欢呼:“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她的作品完全改变了我对于短篇小说的成见,同时也影响了我的创作方式。”门罗确实凭借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改变了短篇小说在大众读者以及专业作家心目中的印象。
与长篇小说相比,短篇小说的历史要短得多,主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发展起来,代表人物为俄罗斯的契诃夫和新西兰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一般而言,短篇小说被认为不如长篇小说的原因往往是短篇小说篇幅短,人物不多,叙事结构相对简单,因此,作家在决心创作长篇巨作之前常得到建议“去写点儿短篇练练笔”。但只创作短篇小说的人就有被揶揄“写不了长篇小说”的危险。例如说,虽然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也是非常优秀的短篇小说家,但是他的获奖作品是《老人与海》,而非其短篇小说创作。与海明威,以及其他许多优秀的作家不同,门罗近60年的创作仅集中在短篇小说这一种文类上。因此,虽然作家早在10多年前就开始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决选名单上的常客,今年门罗的最终获奖还是会被一些人视为“爆冷”。在诺贝尔文学奖迄今112年的历史上,一共评选了109次,获奖作品主要集中于诗歌与长篇小说创作,以及少数剧作。而这样的文类分布,在各类文学奖项的评选结果中,也相当典型。究其原因,也正是因为相对年轻的短篇小说还缺乏足够的时间积淀为自己赢得重要的评论关注。《短篇小说理论》的主编查尔斯·梅就在《序言》中感叹:“相对于长篇小说评论汗牛充栋的文学理论批评,短篇小说的严肃研究确实少得让人难为情。”
短篇小说家的边缘地位还在于:短篇小说不如长篇小说好卖。例如,门罗的处女作《快乐影子之舞》最早在1961年就被加拿大的赖森出版社提上了议程,但是实际出版的过程极其拖沓,直到1967年才实际启动,其中既有编辑调动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因为对于“短篇小说集不卖钱”的商业考量。事实上,《快乐影子之舞》于1968年正式出版时,全加拿大的发行量仅为区区2500本。虽然该作品一经出版就在评论界获得了一致的称赞,并于1969年春天一举赢得了加拿大国内最高的文学奖项:加拿大总督文学奖,还得到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亲自颁奖,但它依然无法避免作为短篇小说集“叫好不叫座”的尴尬——直到4年以后,《快乐影子之舞》初版的2500本在出版社里居然还有库存。当然,随着后来门罗不断地推出高质量的新作,她的口碑渐渐在加拿大文学圈、北美文学圈、英语世界文学圈,乃至世界文学圈扩散开去,她的书也越来越好卖,不断登上畅销榜,并一再打破销售纪录。譬如,1998年门罗出版《好女人的爱》时,短短9个月这本书就再版了5次共计6万册。至2004年《逃离》出版时,初版在加拿大卖了7万多册精装本,6万多册平装本,在美国卖了10万多册精装本,平装本则超过20万册,英国的销售数据则是8000册精装本,以及7万册平装本。门罗确实凭借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改变了短篇小说在大众读者心目中的印象。现在,在加拿大的出版界,流行着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短篇小说要想好卖,就得是艾丽丝·门罗写的。”只不过,当门罗的名字开始成为销售的金字招牌时,短篇小说似乎依然任重而道远。
但是,为什么门罗会选择短篇小说这一种相对边缘的文类来开辟自己的文学事业呢?她的选择与坚持,既有客观因素,也有强烈的主观导向,确实非常值得进一步探讨。
首先,听听门罗自己的解释吧。在《门罗作品精选集》的“导言”中,门罗说,她选择创作短篇小说而不是长篇小说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她每天要做大量的家务,根本无法保证长时间高强度的写作,而那是长篇小说创作必不可少的。这一描述就门罗早期的创作现实而言确实如此。门罗的成名很晚,她出版第一部作品时已经37岁了,之前她的身份一直都是默默无闻的全职家庭主妇和三个孩子的母亲。在那个时代的加拿大,女性知识分子还并不多见,通常社会并不相信女性可以从事任何严肃的职业,同时通常男性也并不会在家里帮忙家务——那是女人的事。虽然门罗的第一任丈夫吉姆·门罗非常支持妻子的追求,但是作为妻子和母亲的门罗每天的首要责任依然是要保证全家人的三餐、打扫整座房子,必要的时候甚至要在家里的书店帮忙做收银员。在这种情况下,门罗所能自己支配用于写作的时间非常少。她只能边洗碗边构思,然后等孩子们午睡的时间,或者洗衣机洗衣服的时间,把想法记录在纸上做整理,这种状态确实不利于长篇小说的写作。应该说,门罗最初对于文类的选择确实是受到其作为那个时代的女性所面临的现实制约。
同时,门罗本人并未提及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因素。门罗最初开始写作的时候,加拿大文坛的职业化程度非常低,加拿大文学整体尚不发达,出版业也很不活跃。一方面,相对于美国社会,加拿大整体经济水平不高,有闲阶级基本不存在,国民更为务实,更少有时间与兴趣去发展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另一方面,加拿大国土广阔又相对人口稀少,使得书籍印刷与运输难以形成规模效应,费用居高不下,反过来又严重影响了销量。加拿大出版社因此往往难以和美国出版商形成竞争,而商业价值比较弱的短篇小说集之类的出版计划也就更难获得出版商的支持。但有趣的是,短篇故事集虽然不如长篇小说好卖,单个的短篇却更容易在杂志上敲开大门。也正因为此,作为文坛新人的门罗会聪明地选择了短篇小说这一文类作为创作的切入口。1951年,艾丽丝·门罗开始向加拿大广播电台,以及各类商业文学杂志投稿,比如《梅菲尔区》、《城堡夫人》、《落叶松评论》、《蒙特娄人》等等。她的第一个短篇故事《陌生人》发表时,作家年仅19岁。加拿大广播电台的罗伯特·韦弗专门写信向她解释说,节目通常采用的故事需要控制在2100个字数以内。因此,门罗的早期创作篇幅都受到了严格控制,门罗在创作时必须要考虑杂志的版面要求。她必须尽快、尽量地卖出自己的作品。
新的问题在于,尽管存在着这些现实原因,在门罗创作的中后期,她的创作条件已经大大改善,她不再有太大的人事与经济的压力,已经能够保证从容与自由地去创作,那么,为什么门罗依然坚持了短篇小说这一文类?事实上,在门罗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获得了加拿大最高文学奖项“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后,她的出版商非常希望这位年轻的女作者能趁热打铁,出版一部长篇小说以便在市场上大卖。门罗也确实努力去尝试了。在《女孩和女人的生活》书稿刚刚完成的时候,她写信给编辑将这部作品称为“在长篇小说和长系列故事之间”,而她的出版商则在市场营销上完全地将其定位于“成长小说”。现在评论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这部作品虽然拥有统一的叙述人和主人公“黛儿”,各故事之间人物也相互关联,但是每一个故事的叙述独立、完整,并不能等同于长篇的章节:门罗的创作方式还是更接近于短篇。类似的情况在《你以为你是谁?》出版的时候再次出现。此时的门罗本人比出版商更希望创作出一部长篇小说,作家和编辑都花了非常大的气力试图将故事素材作为小说章节处理,并使各部分逻辑联系更为紧密。书稿一改再改,但最终在已经确定排版的情况下,门罗还是毅然决定将书稿撤回,最后出来的结果依然是“系列故事”的形式。这也是门罗最后一次尝试长篇小说的写作。
有趣的是,短篇小说往往被人误解为“女性文类”,不仅是因为很多女性都对这一文类有偏爱,更是因为女性被认为比男性缺乏逻辑性,思路比较散乱,难以胜任长篇小说的构思,因此短篇小说作为“女性文类”也就比不上作为“男性文类”的长篇小说。而1994年,门罗也曾在《巴黎评论》的一次访谈中坦言,她几次想创作长篇小说,但是却发现“我永远都不可能写出长篇来,因为我就不是那样想的”。门罗是否在承认,短篇小说比不上长篇小说,同时女性作家比不上男性作家呢?事实上,门罗的写作偏好与她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密不可分的。门罗认为,长篇小说隐喻着一种连贯性,然而在真实的生活中这种连贯性是不存在的,人们从一种经历到另一种经历,彼此往往是不相干的。门罗本人的哲学观强调生活的碎片性与含混性,而不是什么整体性和绝对性。以短篇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她感觉更容易聚焦人生“经历的紧张时刻”。门罗以她独有的敏锐,以一种类似剪纸的方式娓娓道来,读者看时仿佛东拉西扯,不成形状,然而曲终人散掩卷而思,却总能在淡淡的讲述中发现某种如临深渊的恐惧和明净似水的醒悟,使得门罗的“平淡片段”具有了与乔伊斯的“顿悟”和伍尔芙的“重要时刻”同样丰富的质感。
值得注意的是,短篇小说这种艺术形式不仅仅在女性作家群体间比较流行,在诸如新西兰、加拿大与美国之类的新兴国家也极受欢迎,与其相对的则是在文学传统更为悠久的国家,诸如英国与中国,长篇崇拜的现象最为明显。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这种偏向与门罗的选择究竟有无联系呢?美国著名作家与文评家弗兰克·奥康纳在其《孤独的声音》一书中指出,相对于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历史较短,因而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的限制也少,能够享受到更大的创作自由,更能帮助沉默者发声,往往在比较落后的地方以及身处权力边缘的人群中间比较流行,例如,美国南方的短篇小说就非常繁荣。加拿大的情况也是如此。而门罗,作为一名加拿大的女性小说家,在加拿大文学尚不繁荣的年代,以一个大学辍学的家庭妇女的身份开始小说创作,她一直是属于非主流的边缘人群,因此,她能够感受到短篇小说这一文类对其特殊的吸引力也就不难理解了。
同时,门罗创作的也并不是传统意义的短篇小说。她走得更远。她的“超长”短篇小说与“系列”短篇小说模糊了长篇与短篇之间的界限,不仅于此,门罗的短篇小说也挑战了虚构类写作与非虚构类写作之间的界限。正如在传统观念中,长篇小说被认为高于短篇小说,虚构类写作也被认为要高于非虚构类写作,因此,带着自传性质的小说作品往往被贬低为缺少创作力。但是,门罗的短篇小说彻底改变了这一偏见。她的很多小说都带有很强的自传与回忆录性质。小路尽头的房子,拮据的家庭经济,雄心勃勃的母亲,沉默寡言的父亲,孤寂敏感的成长,封闭压抑的小镇道德……这些都在门罗的经典名篇中反复出现。门罗有意将事实、想象与感觉融合为一体,使过去的作品彼此重合与相互补充,从而表达出更为深邃的人生哲学。也正是因为门罗短篇小说创作的这种勾连性,门罗的作品尤其需要整体阅读:意义层层叠叠,犹如曲径通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