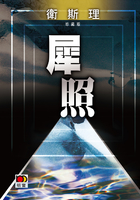我们齐刷刷地站在操场上。
全校的师生没人胆敢出声。
幸福的眼睛,因为自己还站在队列里。
迷惘的眼睛,猜测着要发生什么事。
敬意的眼睛,看着那些戴着红袖章的人。
友情的眼睛,告诉同伴可别揭发自己。
张大的惊异的眼睛。
泣诉着哀怨的眼睛。
操场上停课参加批斗会的每一个幼稚的孩子,正“幼稚”地接受大人的指导,高声呼喊口号。
“打倒现行反革命郑熙!”
就是这个郑熙,教会了这些孩子写自己的姓名。
一九六六年,我同班的孩子都诞生了一个红色的意识,手握“红宝书”歌舞。这是一种叫“忠字舞”的集体舞蹈,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七亿中国人都会跳。这是现在热衷于街舞的歌仔所不熟悉的。
二十一世纪的一天,我与一位姓梁的同学邂逅在“知青饭店”,他刚刚新买了一个大书橱。他的孩子是街舞迷。
“和您说,是我爸红,还是我红。”以为一向应对自如的我,面对这个新新人类竟然哑口无言。
“秩序仍须有海洋看押,住在北里巷的你我他,还有一位看着我的美眉,是从海岛里来的夏娃……”此时,我的智力十分低下,听不懂这个叫“大荒”的孩子执笔的歌词。
那个有“现行反革命”身份的郑老师,痴呆地站在操场上。
他不说一句话,甚至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
他好像没有感觉。但我分明看见了他的嘴唇在动。微微地,不易察觉地。
“背下来。”一个大嘴巴,好响。他的脸色好难看。嘴唇也是这样微微动着,一句话再没有说。一个男孩子捂着脸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继续背诵“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人人都要背诵下来。
我们害怕挨打。背地里没人叫他郑老师,“郑狠子”是我们给他起的外号。
回家的路上,我问:“痛吗?”那个被扇了嘴巴的同学,他叫大义。
“其实,不怎么痛。”大义摇摇头。
“不信。”我说。
“‘傻丫头’也被打过。不信你问她!”
“回家父母问起,怎么说?”我问道。
“不,这不能说。”
“为什么?”他越是不想说出来,我越想打听。
“你发誓,绝不告诉别人。”大义有点不情愿。
“好!我发誓。”我学着电影里地下党员的样子,举起了右手:“绝不告诉别人。”
“好像应该举左手……”大义有异议,但口气不太坚决。
“管它呢,反正是发誓。”我真怕他反悔,急忙敷衍。
“我也说不太清楚。反正,被‘郑狠子’打过,就不会像阿鱼那样了。”
“真的?”太意外了。
“是‘傻丫头’的妈妈说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太好了!”我喜出望外,伸手一跳,趁机戳了一下他刚才被扇的脸。
“哎呀!”他大叫一声,向我扑来。
“你不是说不痛吗?”
“不痛我扇你一下试试!”
我急忙跳开:“瞧,那边有个人。”
我趁他愣神的工夫,撒腿就跑。
郑老师的旁边站着一位戴眼镜的男老师,可能有三十岁。
他脸色发白,像严重贫血。
我一时也想不起他的名字。
上次,小礼堂里,被批斗的就是他。他是高年级的老师,爱讲故事。
“你就是地地道道的牛鬼蛇神!”那个发言的女人声嘶力竭,“你给学生讲鬼故事,其实,你就是个披着人皮的活鬼!是的,你是不在乎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的师生们,你们看,他两只眼睛滴溜溜地转,那是在伺机反扑。”
那个会讲故事的高年级老师,嘴唇紫红,一动也不动。
他像是在倾听,倾听别人的意见,看下次再讲《聊斋志异》时,有什么改进。
“我们革命队伍里混进了这样一条癞皮狗,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同志们,你们看,他混合着恶臭的灵魂,贼心不死啊!这个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那女人唾沫四溅,斗志昂扬。
有人跳上台来。
戴眼镜的老师头上被扣了一顶白白的高高的尖尖的纸糊的帽子,像电影《红色娘子军》里的恶霸“南霸天”被枪毙前的样子。
“把资产阶级的臭小姐胡爱华给押上来!”
胡爱华是我们的音乐老师。一张清秀的脸,白白净净的。谁见了她,都以为自己的脸没洗干净。一对柳叶眉,一双杏仁眼。一米六七的身高,苗条的曲线。女人见了嫉妒得要命,男人见了容易想入非非。
两个身穿绿军装头戴绿军帽的年轻女将,一人一只胳膊押着胡老师,站到头戴白帽子的男老师身边。
“我是一个黑孩子,黑孩子,我的祖国在黑非洲。黑非洲,黑非洲,黑夜沉沉不到头”。音乐课上,音域非常宽厚的嗓音,把我们带进了非洲的丛林中。我们不了解非洲,但在《世界人民大团结》那幅画里,我们见过黑黑的皮肤,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牙齿的非洲人。就在这个礼堂里,胡老师还把我们几个孩子打扮成非洲孩子的模样,表演非洲人民追求解放的音乐剧。为了启发我们理解非洲人民遭受的苦难,她还给我们讲述夏衍的《包身工》里的“芦柴棒”的故事,让我们几个练节目的孩子,难过得直揉眼睛。
全校的人都知道,校长大人最喜欢找胡老师谈话。谈些什么,刚才那个“斗志昂扬”的女人最关心。一次,校长大人找胡老师“谈话”,胡老师就给校长讲了一个故事:“东汉初年,光武帝召见宋弘,一边跟他谈话,一边却心不在焉地东瞥西瞅。宋弘一看,原来,周围屏风上画着一个个搔首弄姿、娇情百般的美女,皇帝心思全在欣赏女色呢!”校长大人急切地问:“后来呢?”“后来,”胡老师讲故事的声音非常温柔,“宋弘作为一个臣子,完全可以敷衍了事,但他却义正词严地打断了光武帝的兴致,说:‘皇上,没有一个向往道德的人会像您这样喜欢女色的!’光武帝一听,不好意思了,赶快撤了屏风,跟宋弘谈起正事来。”
看到胡老师被押上台来,刚才那个唾沫星子四溅的女人,像被打了一针强心剂,精神头儿更足了。“呸,”她向胡老师的脚下狠劲地吐了一口唾沫,“啪啪”照那张漂亮的脸蛋就是两巴掌。“你这个臭不要脸的!资产阶级的臭小姐,”看到那张漂亮的脸上起了几道红红的手印,她有些得意忘形。她跳着脚继续骂,“你这个破鞋,骚货,浪女人,早就该进监狱呆着的野鸡。也不撒泡尿照照,一个彻头彻尾的狐狸精,竟敢拉革命干部下水,你还故意给校长讲故事……”她意识到什么,看了一眼台下,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然后,挺了挺身子,回过头来,想继续进行她的“控诉”。
正在这时,一个年轻人冲到台上,用手势示意她下去。她只好悻悻地从右侧台阶走下来。换下那个女人的男人,外号叫“太甚”,因为他习惯用“太甚”一词评价任何事情。他是校长暗示出马的,可能是校长怕那女人说出胡老师给他讲故事这档子事,让自己难堪。
“你,太甚。竟然侮辱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是‘黑孩子’!”
台下有几个女孩哭了起来。
“你听,你把革命的红苗苗摧残成什么样子?”这个人真是太甚,大白天胡说八道,“你说,你的名字什么含义,是不是‘不爱中华’?”
一位教历史的女老师尿了裤子,她望了望门口,那里有戴着红袖标的人走来走去,于是只好低下头。
操场上。
批斗会已经开始了一个小时。
胡爱华、郑熙、戴眼镜的男老师依次排开。他们的身后分别有两个戴红袖标的年轻小将,架着他们的胳膊,使他们的身子向前弯曲,头快触到了地上。原先挂在他们脖子上的牌子,已经对应在他们眼前,横躺在地上。他们的两边,各有四五个“小反动”,都自觉地撅在那里。阿鱼和黑娃也在他们中间。
世界真是乱了套。年轻美貌的胡老师,居然也是阶级敌人。
我的思想开了小差。
和杨叔叔一样爱上我家玩的一位伯伯,是个画家,姓金。那时,各种建筑物的墙壁上画的巨幅宣传画,都是他画上去的。有《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有《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还有《心中的太阳永不落》,好多好多。
一天,晚饭后,我正趴在我家的小饭桌上,照着一本黑板报宣传画册,临摹一幅《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我怎么也画不好孙悟空拿金箍棒的手。
金伯伯进来了。见状,向我要了一张报纸那样大的白纸,拿起我文具盒中的蜡笔,三下五除二,一幅孙悟空倒提金箍棒,手搭凉棚,高站云端的蜡笔画跃然纸上。我羡慕不已。从此,金伯伯便隔三差五地来我家,教我画画。
我有绘画天赋,也是金伯伯告诉爸爸的。
我学画的本子一天天多起来。
一天课间,一个高年级的女生来借我的绘画本子。我的画本常被同学借去翻看,这是我感到骄傲的事。
一堂课过去了,我正想着要回我的本子。借了我本子的高年级女生,让我到老师的办公室去拿。
“你借去的,为什么交给老师?”
“去了你就知道了。”她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地面,长了一颗黑痣的嘴角不屑地翘了翘,我一直以为她那张嘴棱角分明,美得让人倾倒。
我的绘画本子,已经摊开在一位女老师的办公桌上,那页赫然画着我从杨叔叔送给我的明信片上描摹来的北京天安门。
“为什么这里只是个方框?”女老师——她就是现在台上的胡老师——指着画面的正中问。
“我画不像,没敢画。”我小声回答。
“哦……”女老师像是在思索。然后,把本子合上,递给我,“以后要注意啦。”她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说给我听。屋里没有别人。
我连“谢谢”都没说出来,就轻轻地退出了她的办公室。
大概是女老师告诉了我的妈妈。那晚,母亲破天荒打了我的屁股。
在我的哭声中,我的几本绘画本子,都成了母亲灶堂里的火苗。
郑熙力图挺直身体,缓解一点腰的酸痛,但是押着他的人使劲往上一抬他的胳膊,他的头又低下去了。我惊奇地发现,他课堂上经常架在鼻梁上的眼镜,竟然不见了。
天空聚集了乌云。要下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