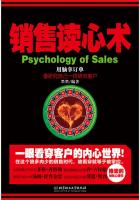有弹性的工作听起来很有意思,而且实际上也的确很有意思。人们将会有很多不同的工作,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只有一个可以用来代表生活整体的职业。人们将不再只从一个工作中求得金钱、地位及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可以在不同的工作和生活中,求取不同的东西。也就是说,或许金钱来自某项活动,而地位则来自另一项在经济上不能提供多大报酬的活动。这将是个比较适合于狄奥尼索斯型人的世界。
这也同时会是个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世界。
狄奥尼索斯是从专业主义中获得保障的。一个医生,只要守法,便永远是个医生。他并不见得一定是个好医生,但即使是个坏医生,也一样能开业。
然而其他自我雇用的人,不管是艺术家或工匠,都没有所谓长期性的契约来让他们过活,而是得仰赖他们的技能或专业知识。因为可以贩卖的技能,是让弹性生活得以存在的一个最根本的保障。
但是,一项技能要能贩卖,必须先被认证——至少在实际开业的前几年必须如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所做的工作本身就会是一种文凭。不过,没有人会不需要某种确保你有能力做某事的证明,就要你去做第一份工作。因为在名片上印上“铅管人员”或“宣传”,并不能保证这个名片的持有人就能做铅管工人或是宣传。
换句话说,证书是必要的。但是,可叹的是,证书本身并不是一个充份、足够的开端。
狄奥尼索斯的社会里,证书可能可以保证获得工作与金钱的机会,但假如工作(或者至少是有报酬的工作)不再是我们一辈子生活的全部,假如在我们的工作生涯之中或之后,有许多时间做其他的事,那么单单是证书,就不足以定义你,或是你的成功了。然而,却能让你超越你的正式工作,也超越你的证书。
因此,用资格证明社会来取代雇用社会,或许可以让社会发展出更多的样式,更多成功的定义,是更多美好的生活与自我实现。
一个全然的雇用社会,将生活割裂成“工作——休息”。传统上,虽然许多人一直都以为,像家人、庭院、运动,或社区之类工作以外的事才最重要,但是成功都被定义为工作上做出了重大成绩。
雇用社会在本质上是物质主义者与终身事业主义者的。因为此二者是雇用社会用以激励人心的武器。
如果没有人需要金钱或职业上的提升,阿波罗式的架构便会丧失掌控力。
一个比较倾向狄奥尼索斯的社会,毋庸置疑地仍会有许多物质主义者。我们应该对此心怀感激,因为我们需要他们那股创造富裕的能力。
不过,那里也必须同时有其他的模式可供选择。因为生活的品质并不完全仰赖物质。
有些人会运用他们新获得的自由与时间,发展其他的兴趣。比如多做一些旅行,或过更简单些的生活,把心力放在家人身上,参与一点地方的政治、志愿工作,或就只是多阅读一些书报,多看一些电视,或多和朋友谈谈天。
我希望,成功将会有许多不同的面貌,而终身职业主义者的专业化,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已。
对一些人来说,这种在成功途径上的解放,可能会令人感到困惑,选择的余地太多了,也常常会比没有选择的余地更让人无所适从、更苦恼。
如果金钱不再是主要的衡量标准,生活的目的也就变得不太明显。那么,我们要怎样评判他人〉又怎样评判自己呢?当“前途”的定义不只一种两种,而是有很多种时,我们也许无从判断我们未来的女婿和媳妇,到底有没有“前途”。
我们前面提到的“新典范”,像是为生活提供了各种可能性的自动餐馆,是一种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资格证明和生活型态的机会。
这将会走向一个很有趣而且富有变化的社会,然而也会是个让许多人感到困惑不安的社会——特别是那些本质上就不是狄奥尼索斯的人,或是那些不易获得资格证明,因而看重雇用社会的常规与安全感的人。
可悲的是,剩余下来的阿波罗文化将会表示,那些最难去适应雇用以外生活的人,将会最先被迫进入这种生活。
资格证明的社会并不是每个人的梦想,而且还有可能形成另一种阶级划分——有资格证明的人和没有资格证明的人。
四、新的问题
新组织模式、工作与生活所带来的,令人兴奋的种种可能性,不应当使我们因此而看不见问题的威胁,特别是下面三个主要的问题:
我们要靠什么来生活?
我们要如何教育自己
我们要如何保护自己?
这些是新的情况可能引发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彻底了解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将社会中的人分成这样两大类:一类是有工作、能赚钱的人;一类是不能工作赚钱的人。
那将会是一个充满嫉妒与仇恨的社会。
在那样的社会中,赚钱的人会痛恨要付很高的税来养活那些不能赚钱的人;而这些不能赚钱的人反过来会痛恶自己的依赖心理,并嫉妒这些能赚钱的人,还有他们所拥有的特权与优越的生活形态。
金钱和教育可谓通往自由的道路。没有它们,我们在生活与心理上就会受到羁绊。劝告人们“骑上摩托车”去找工作,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正如某个英国劳工部长所言,假如人们没有“摩托车”,更别提小轿车(而在当时,英国失业的人口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人拥有摩托车);假如他们无法卖掉他们的房子,或是在廉价住宅中找到另外一个房子;假如他们缺乏新工作所需要的技能专长的话,说什么都是枉然。
这样看来,金钱与教育是任何社会对其公民,特别是那些比较不幸的公民,所能做的最切实际的投资。
不过,这必须被视为是一种投资,而非勉为其难的施舍。倘若没有做这种投资,我们或许就会走入墨林·达菲(Maureen Duffy)笔下的那种社会去。而且,这是一种不能等社会全体下决定的投资。如果各组织想要最后能活在一个值得活的世界的话,他们就必须自己带头去做。
墨林·达菲笔下的社会
墨林·达菲在《Gor-Saga》这本小说中,描绘了一个新世界,当作故事发生的背景。在其中,专业性工作的精英体制接掌了一切。科学上的高度发达,使得组织里的职员得以控制信息资源,并拥有支配人们生活的权力;甚至,可以去创造他们想要的生活。
被逐出这个社会的,是那些没有适当工作、住在城市边缘空地,或深入乡间的“废物”。
暴力到处充斥,甚至为了效率,连那些志愿性的义工机构,都得变成像武装游击队一样。
城市变成了少数有钱人与观光客聚集的地方。在大部份的市郊,则必须要有通行证。
那儿有火车、公车、电视、与各种生活上的装备,然而生活只有对那些有资格证明的少数人来说,显得适宜而美好。对其他大多数人来说,它就像个丛林。
在这个丛林世界里,“文字加工者”(word processor)变成是机械化心智者的客气说法;而“领津贴者”则是泛指无法养活自己的任何年纪的人。
1.我们要靠什么来生活?
坦白地说,如果我们只工作向来工作时数的一半,如果我们在雇用时期之后,还有两倍长的日子要过,那我们——不管是就国家还是个人而言——就该为退休的日子储存四倍的钱。
尽管有人会争论说,至少在英国,因为这种投资具有节税功能,所以人们已经在退休金上过度投资了好些年,不知不觉地在为未来作准备了。然而,这样的事实际上并没有发生。
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如果退休金能够普遍地被视为个人累进的资本,而不只是他度过雇用阶段之后,所应得的一种工资或薪水,那么人们的确是在为那些未来的岁月做准备。
假若不是这样,早早离开雇用阶段的人,还有那些经常变动工作的人,便会丧失在原组织 的大部分保险金,等于是为那些留下来的人积累了更多的退休金。
假如组织希望人们更容易流动、将一些工作对外包出去,或多设兼职工作的话,就必须认清现代组织生活的真面目,还有被截去顶部的正式职业与弹性生活的真面目。
狄奥尼索斯型的人有个人的退休金计划。而所谓的“可携带型退休金”(portable pensions),必然会在狄奥尼索斯型的人,越来越受组织内外欢迎的情况下,变得越来越普遍。
然而可携带型退休金方案,费率无可避免地会非常昂贵;或是,以相对的方式来说,金额总数会较低。因为这些方案无法记录所有较早离开与经常变动的人,在保险统计上的资料。
因此,在这种新情况下,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会变得更穷,除非我们能想出办法做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