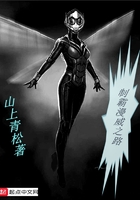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有非常狭隘但一致利益的小团体。这些联盟团体发现,将国家资源转移到自身上所获得的利益,会比试图增加资源总量还来得多。也就是说,他们玩的是分配的游戏,而不是创造的游戏。他们具有排外性,对老成员来说,新成员根本不算什么。他们排斥创新以求保护自己的市场或选区。他们放慢改变的脚步,使得政治生态更分歧。
工会就是这种聪明中的一个;工会中更重要的是可以控制产销量与货价等的“卡尔特同业联盟”(cartels)、商业协会(trade associations),与专业团体(professional bodies)。
战争、革命与国界上的变动,会破坏这种情况。动荡的局势,将摧毁负面力量存在的环境,反而是带来了经济上成功的前景。
四、征服反抗
假如阿波罗的效率是为了胜利,那么组织就必须征服反抗阿波罗效率的力量。前面我们已指出抗拒阿波罗式文化的三个主要方法,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征服每一个抗拒力量的方法如何。这些方法的效果是我们必须首先加以考虑的问题。
对抗阿波罗的“第一个重要特征”,与大型阿波罗组织难以管理的复杂性有关。不过,我们不应该接受失败:我们难道不能扩大个人的能力幅员,并为他们装配先进的电脑辅助设备吗?电脑已经在董事会办公室出现了,有一些程式可以评估任何决策组合所可能产生的结果,并几乎同步地输送到决策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难道这种便利无法再进一步?教育接受管理的人,不正是解决能力幅员这个问题的解答吗?
的确,在探索一些有关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上,电脑对管理的帮助,有很大的潜力。就像不同的经济选择所产生的影响与结果,可以透过电脑的模拟,操作、审查出来。因此,理论上,所有选择的结果,都可以呈现在管理者的面前。
现在,人们正投入许多心力,试图找出一个大致上可以将组织中的资讯、货物、活动,或金钱的流通,加以模式化的应用方式。毋庸置疑地,到时候,这种模式就可能会非常接近真实状况,而比现在这种过于简化的情形更有帮助。
至于是否可以模拟出模式背后人类的情绪、需要与信念,都还只是另外的问题。身为人类的精髓,在于有能力驾驭我们的未来,而这种“人类精髓”正是模式化管理中无可弥补的断层。
到目前为止,用教育来扩大能力幅员,就如同寻找下落不明的“圣杯”(Holy Grail)的尝试。我们可以通过练习、教导、训练来教授技术、传达讯息,并使学习者获得技巧。不过要有所领悟、懂得整合复杂性,或是能想像或着手一些你可能无法在有生之年看到成果的事,这些繁杂的思维能力是相当少见的。
有些人认为这种能力只有由遗传才能继承下来,或至少是在生命早期宝贵的几年中获得;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我们可以学习用抽象概念来思维。后者认为,通过研读历史、经济学、商业个案、甚至文学、哲学,可以帮助个人提高抽象思维的能力。
然而对于这点,我们实在拿不出什么证据。而且如果这种能量可以在成熟之后学得的,那么大部分的实习经理所必须上的训练课程,可就不止花费一般的四个礼拜了。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说:到目前为止,电脑和教育都还无法提供一个走出阿波罗式文化困境的可能或快速的途径。
教育帮得上忙吗?
对大部份的人来说,教育是指学些有用的东西,不管这是指学些事实,还是技术。依这种看法,大多数更高深的教育,其有用性的最大期限约是十年。十年以后,不是所学的知识在先进的科技与新发现之下显得落伍,就是个人已经转移到另一个不再需要这些知识的层级或职业。想想,有多少四十多岁的人还在用他在大学或专业学校所学的东西呢?
不过,较高的教育或许能开发和提高我们面对复杂环境的反应能力、处理争论而不只是事实的能力,以及处理特殊与抽象事物的能力。
听听人们在谈些什么。他们能推理吗?他们只是处理事实,把意见转变成事实,而避开逻辑性的讨论吗?这和他们的教育背景有关吗?
邓宁(J.H.Dunning)在一份美国与英国小公司相对获利性的研究中指出,一九六八年,在美国和英国的公司里,有大学学位或同等学历的行政主管,比没有这种学位或学历的人,多赚了许多。同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情况在美国与英国中几乎完全一样,而在美国公司中,有大学学位或学历的行政主管之比例,却比英国高出许多。
这种跨文化的比较并不只适用在美国。根据汉迪(Handy)在二十年后所指出,跟西欧国家或日本比起来,在英国有学位的行政主管是比较少。
就管理能力上来说,这代表着什么吗?或者,这只是反映出不同的文化风尚而已?
抗拒阿波罗式文化的“第二个重要特征”,与阿波罗式文化本质上的“罗”有关,阿波罗式文化使人际关系越来越疏远。对抗这一个特征的方法不是去否定它,而是接受在任何社会或组织中,一定会有一些乏味的工作这件事,也因此,角色就必须比个人重要。
在大多数人看来,工作是为了让我们得以享受生命中其他部份的欢乐,而必须去做的事情。当然,很幸运地,有一些人的工作正是他们的兴趣与爱好之所在。不是曾经有人将幸福定义为“因嗜好而获得报酬”吗?然而对其他人来说,尽可能让工作变得不那么痛苦,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事。让工作中的身体舒服(但是你怎么令铸造业工作中的身体舒服呢?)、让雇用的合同能够公平,最最重要的是,较为艰难的工作,无论是在金钱还是在休闲的时间方面,都应该要有够高的酬劳。
这里出现了一个颇具争议性的现代难题——“工作-报酬”这个等式并不明确。当机智的协商或威胁性的战略,可以不需要工作就获得许多钱时,代表往后工作得较多,不见得能够赚到较多的钱。甚至当因为生产增加,而获得更多的报酬时,法律上的个人税赋,往往剥夺了个人大部分的劳动成果。倘若今天,工作的报酬变得不再划算的话,错是出在报酬,而不是工作。然而,一个致命的缺失却潜藏在这个长久以来的争议之中:一个人报酬所得常常正是另一个人不情愿付出的东西。弗瑞德·赫希(Fred Hirsch)在一本叫做《社会的成长极限》(The Social Limits to Growth)的重要书籍中,称这种两难困境为“富裕社会的假承诺”。
它是这么认为的:只要你不在意别人拥有你所得到的东西,那你就会提供同样的红萝卜,它的作用就是个一般性的激励诱因。到这里为止,看起来还不错。丰富的物资、较好的暖气设备、更多的休闲——这些是所有人可能会希望其他人和自己一样拥有的东西。但是有些东西是我们想要的,而且根据“定义”,是其他人不能拥有的,因为这些东西要靠“比较上的”优势来获得。
英国的私人教育就是这些东西当中的一个——倘若每个人都能享有,那么人们就不会那么想要得到它了。仆从也曾经是这些东西里的一种,然而我们无法都做主人,否则谁来服侍我们呢?一个周围大自然的景色没有遭破坏的房子是一个看上去很独特很赏心悦目的房子,然而如果所有的房子都是周围大自然的景色没有遭破坏的房子,那上面那个房子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它不过和别的房子“彼此彼此”罢了。
一旦我们从一般性的物资转移到比较特殊性的物资时,就会碰到这种没完没了的矛盾难题:“当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你就不会想要它了;因为,每个人也都得到它了。”也就是说,大多数人不能享有少数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