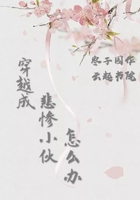她摸索到床头的衣衫,一件件地穿上,又借着月光走到童车前,弯下腰去最后一次亲了亲小年软软的小脸,眼泪终是止不住落在孩子的眉角上,她哽咽道:“小年,妈妈对不起你,你一定要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地长大,知道吗?”
他们房间里的灯一直是开着的,桂巧本是想进来替他们关上的,待推开门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怔了怔,试探着叫了她一声:“夫人,你…”
初阳方才缓缓地直起身子来,对桂巧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又从仇少白的腰带上拔下了枪来,问她道:“汉生呢?”
桂巧还未能完全回神,木然地指了指楼下,道:“汉生还在门外守着。”
唐汉生显然也没有想到原来她早就已经清醒了,在听到她对他说出自己的决定时,更是吓得乱了心跳,道:“夫人,使不得!先不说现在小少爷还小,正是需要母亲的时候,白爷,白爷若是醒来发现您已经…”
他话未说完,便见初阳已是熟练地将子弹颗颗不落地重装在了弹匣里,拉了拉保险,道:“我不能死,他更不能死不是吗?至少他活着所有的事就都还有希望,而若是他死了,那我一样也不可能独活。”
唐汉生叫了一声“夫人”,还想说什么,却是突然被她拿枪指了太阳穴,她眼睛里的寒意像是要刺穿人的身骨,只让唐汉生不自觉地有些打怵。
她道:“带我去见陆向天,我需要知道他们的详细计划,时间就要来不及了。”
陆向天与饶戚是铁骨铮铮的汉子,两人都想不到于初阳竟来了这样一招,本是要果断拒绝的,却又终是抵不住她一字一句戳人心窝的话,她说:“仇少白要活着,他活着你们才可以有下一步,而你们活着,上海才能活。”
如此大情大义只叫他们两个真男人都佩服。
他们选定的碰面地点是一个清静的湖边茶亭,原本与山本女士约定的时间是上午七点,陆家军与饶戚的人早就连夜做了埋伏,而初阳却是故意拖延了些许才从车上走下来。她今日穿了一件与仇少白几乎一模一样地黑色长衣来,乌黑的长发被盘进那圆顶毡帽里。寒冬腊月,雪花飘飘落落,下得不大却又停不住,只不过站了几分钟的光景,身上就已经簌簌地飘满了一层薄雪,她的身子打了个颤,又转头远远地看了一眼冰寒雾重的湖面,方才记起,原来今天是冬至了。
山本女士早就已经等在茶亭里了,而她的身边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带着狼子野心重新回来的于正业,他竟真的成了卖国汉奸,此时正殷勤地在山本身边说着什么,引得原本面无表情的她突然有了笑意。然而他如何都想不到的是,他费尽了心机,做好了一个又一个圈套等来的竟是自己的女儿。
那短短的几步路,却像是将这两年来的点点滴滴都回放了一遍,初阳方才惊醒,原来这一路她记着的最美好的瞬间,便是在校庆的舞台上,一低头,便能看到仇少白与爸爸同在台下。那日的仇少白穿得前所未有的正式,她曾几乎要认定了,他是要对爸爸提亲的。可是事情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他害得爸爸身败名裂,而爸爸却拼了一切只想置他于死地…
初阳将帽檐压得低低的,由两个日本人引着到了茶亭里去,端端正正地坐下了。
山本女士客客气气地给她斟了一杯茶,开口却道:“仇夫人好胆识。”
她便也不再伪装,方才抬起头来正眼看着两人,恰有一片冰凉的雪花落在她的眼前,只叫她目光中于正业的脸都要模糊了。于正业有些惊恐地动了动,几乎就要站起身来,她却是极力佯装冷静,道:“外子突害疾病,不能前来会约,初阳斗胆来见,还望山本女士莫要责怪。”她一边说着,一边取了茶放到嘴边,大体看了看早就等候在不远处的日本列卫队,那些人手里都拿着冰冰冷冷的长枪。
于正业用颤抖的声音叫了她一声“阳阳”。她却只是报以一个极淡的笑,转过脸对山本女士开门见山道:“今日初阳受外子所托,特意来与山本女士传达关于重开跑马场的决定。”
山本女士笑了笑,“哦?那决定如何?”
初阳眼看着天边乌沉沉的铅云愈来愈重,想着又将是一场大雪要来了。寒风几乎要将她发顶的帽子吹翻了,她便做了一个打冷战的动作,将那毡帽取下来扣在矮木几上,道:“实在有愧山本女士看得起,外子终还是决定不能做那遗臭万年的卖国贼。”
于正业当即大呼一声:“阳阳,不准胡说八道!”
那山本女士方才明白过来,她来竟是为了戏弄自己一番,不禁大怒:“八嘎!”而正因为这一声大怒,那些候命多时的列卫兵纷纷将手中的长枪举起,齐齐对准了初阳。
于正业见此,更是担心到了极致,他小声劝慰着山本,又对初阳道:“阳阳,爸爸不管今天为什么是你来应约,最好速速回家去,让仇少白在晌午之前赶来,他尚还有条活路。”
初阳却是突然失了魂魄一般笑了,看着他道:“回家?于老板,我的家不早就在你的争权夺利中被仇家报复没了吗?”
于正业脸色一变,痛心疾首道:“现在不是儿戏,阳阳你不要闹!”
初阳却是倏地从袖口中滑出了一把枪来,正是仇少白贴身带着的一把威力极强的德国伯宁特。她趁着两人都未有所防备的这一刻迅速地拉开了保险顶在了山本女士的头上。
于正业回头看了一眼蓄势待发的列卫兵,心都要跳出来,道:“阳阳,放下枪,你不能这样任性,爸爸就剩你一个女儿了…”
她轻声笑了,道:“爸爸,可是一切都已经回不去了,你知道的,现在的上海已经被你的这些‘主子们’害得千疮百孔,我来就是为了做一个真真正正有良心的中国人。你们以为做的这些阴谋诡计中国人不知道吗?跑马场不能让,上海不能亡,而仇少白更不能死,至少不该死在爸爸你的手里…”
那些列卫队已是慢慢朝着这边靠近了,于正业听她说着这些话,脸色越来越苍白。
当山本女士趁着两人说话之时从口袋里拿出枪来迅速对上初阳胸口的时候,陆向天与饶戚也纷纷带着人冲了上来。
几乎就是在一瞬间,那些列卫队已被猝不及防地打倒了一半,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些人是如何出现的。
到底是血亲胜过一切,就在山本女士已被彻底激怒要对着初阳开枪的那一刻,于正业突然挡在了两人中间,那一枪实实地打穿了他的身体。
初阳握着伯宁特被他推着向后踉跄了几步,大喊一声:“爸爸!”
于正业却已是摇摇晃晃地倒了下去,他拼尽最后的力气,道:“阳阳,快走!”
而此时山本女士突然用日文喊了一句什么,在陆向天与饶戚的背后竟又出现了一队日本兵,而原本平静的湖面周围竟也涌出了上百个士兵来。山本女士对着初阳大笑道:“你们中国话还是有意思的,这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对吗?”
初阳心中大惊,面上却依然保持着冷静,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朝着山本女士猛然开了第一枪,在山本女士不可置信之时,她却是补了一句,道:“中华文化岂是你们这些日本人说懂就能懂的?现在叫‘置之死地而后生’!”说着便又倏地从腰间摸出了另一把伦勃朗来。
陆向天与饶戚在与外围日军抗战,这小小的茶亭里便只剩了她一个,山本女士捂着已是血流不止的胸口,大喊了一声:“打!”
初阳极快地在乱枪中旋了一个圈,双枪齐发,连带着山本在内,所射之处,皆是枪枪入喉。
然而与此同时,那些日本兵也都毫不犹豫地对着她一起开了枪。
昏昏沉沉的天寒风狂啸,那似是如何都下不大的雪也如鹅毛般纷纷扬扬地落了下来,血从她的身体里溅出来,染红了亭中的地板…
她的身子摇摇晃晃地倒进了那赏雪湖中,惊起一片涟漪。她眯着双眼看着漫天的大雪,脸上突然露出一个凄美的笑容来,像是突然又回到了那个总是冰冷荒芜的训练场上,他坐在木椅上,看着她总是轻而易举地完成他教的新任务时露出的笑,他道:“小丫头,原来你才是那个不可多得的射击小天才…”
湖水在她的耳边咕咚作响,仿佛一瞬间又将她带到了耳目山上,那里山清水秀,有着美不胜收的夜景,他温暖的双手拥着她,一字一句地教她唱着:“星星笑点头,地上人相幽,荷包指尖香自留,两情相悦低头羞…”
寒彻身骨的西风呼啸着自远方而来,呜呜地嘶吼着,蛮横地掀起了湖面的层层涟漪,挟着簌簌的雪一点一点落在她的眉角上,似是有着千斤般重,竟是压得她的眼皮再也没了支撑的力气,而她的身子也终如一只断了帆的船,那样摇摇晃晃、凄凄惨惨地沉入水中…
“初阳!”
不知迷迷糊糊到底睡了多久的仇少白终是因为一个极可怕的噩梦惊醒,他倏地从床上坐起身来,发现身上已被汗水湿透。窗帘被严实地拉上了,屋里的昏暗让他分不清现在到底是什么时辰,只是下意识地伸手去碰身边的位置,竟早已经冰冰凉凉没了她的身影。
童车里本是安睡的小年突然哭了起来,仇少白揉了揉酸痛的双眼,大喊一声:“桂巧!”便下了床将孩子抱进了怀中。小年原本是极听话的,此时却是哭得那样大声,撕心裂肺一般,惹得他心中也一阵阵地发疼。
桂巧立刻便推了门进来,战战兢兢道:“白爷,您醒了?”
他极不耐地挥了挥手,心痛如绞,问:“夫人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