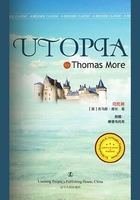商品经济对于文艺的影响,不仅反映在文化市场的供求关系上,更主要的还在于因思想观念的更新而带来的审美意识上的变化。
商品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产生了市民思想;市民思想强调个性的自由发展,对于以皇权为核心的“服从”和“大一统”观念,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力反映在各个方面,文学艺术自然也不能例外。
中国的商品经济虽然出现得较早,但由于长期以来处于农业社会,而且政府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所以商品经济发展缓慢,直到明代中后期才有明显的成效。市民社会的出现和市民思想的抬头,大抵也就在那个时候。于是,在思想界涌动着一股个性解放思潮,而在文艺界,则出现了以突出个性、强调感情为特征的革新运动。我国的这场文艺革新运动,虽然不及欧洲文艺界的浪漫主义运动那样旗帜鲜明和波澜壮阔,但就其基本特征和社会意义看,则有着相同的性质,都是资本主义思想在文艺上的反映。
当然,这场文艺革新运动,还与明朝的政治情况和文人的境遇有关。
明朝是推翻了元朝的异族统治,而重新建立起来的汉族政权,对于一向重视民族观念,同时又受过异族统治者歧视的汉族士人来说,开始是抱着欢迎态度的。但依靠农民起义的力量而取得政权的朱元璋,推行的却是一种打击知识分子的政策。他一旦坐稳了皇位,就大开杀戒,不但杀了许多掌握实权的士人,而且还祸及只作“供奉”用的画家。有名的“元四家”之一的王蒙,就因为在左承相胡惟庸家中鉴赏过绘画,而陷入胡惟庸案,“瘐死狱中”;赵原,是被征集到中书省的画史,只因应对忤旨,就被“伏法”掉了;盛著,在内府供事,本来是很被赏识的,却因画天界寺影壁,以水母乘龙背,不称旨,即遭“弃市”。真是动辄得咎,难以存活了。
到得燕王朱棣从他侄儿子手中夺得政权,因方孝孺不肯为他草诏,而被诛十族,更杀得士人战战兢兢,循规蹈矩,如履如临,不敢有所创造了。后来他更责令大臣编纂出三本士子必读书:《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以程朱理学为准则,进行科举取士,就更规范了士子的思想。这反映在书法上,是台阁体的流行,在文学和绘画上,则是复古主义当道,缺乏创造性。
但是,文化专制主义总是不能长久的。而且物极必反,“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推行得久了,弊病百出,必然有反对它的理论出现,这就是强调自我的心学,虽然它同样打着儒家的旗帜。心学也并非什么新事物,它起于宋代的陆九渊,而且将源头追溯到孟子那里去。到明代中晚期,提倡心学的人也颇多,而以王阳明影响最大,故称阳明心学。阳明心学强调“致良知”,讲究求乐自适,这大大地唤醒了士人心性的觉悟,而且逐步形成了思想上的对抗力量,辐射到文化界的各个领域。单就文艺而言,就有李贽的童心说理论,汤显祖的主情派戏剧,袁中郎的性灵派诗文,冯梦龙的市井通俗小说,并出现了像《金瓶梅》这样全面描写市民生活、反映市民心态的长篇小说。而徐渭的出现更早于李贽和汤显祖,他还在后七子复古主义统治文坛的时候,便喊出了革新的声音,而所受到的压力当然也就可想而知了。他后来的疯狂,虽说有生理上的原因,但环境的压迫,是不可忽视的诱因。
徐渭是个全材,不但诗文很有影响,而且剧作《四声猿》和曲论《南词叙录》亦惊绝一时。据商维浚:《刻徐文长集原本述》中说,袁中郎在友人家中初读徐渭剧作和诗文时,“忻然手翻,篝火达旦,凡读一篇一击节,直恐其尽,至忘假寐”。读罢,对友人赞叹道:“才思奇爽,一种超轶不羁之致,几空千古。”后来,他在《徐文长传》中,又对徐渭作了这样的论述:“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呜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呜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这段话把文人心态和诗文创作的关系,讲得非常透彻。但是,就徐渭而言,成就更大,对后世影响更为深远的,还是绘画。他同样以这段不可磨灭的奇郁之气,注之于绘画,就创造了一种磅礴、酣畅的大写意画风。
徐渭多画花卉,笔法奔放,水墨淋漓,个性张扬,不守法度。无论是荷花,是葡萄,是石榴,是梅菊,到了他的笔下,都有一种豪放野逸,纵横驰骋之气势。他自己在题画诗中说:“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不信试看千万树,东风吹着便成春。”“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拨皆吾五指栽。”这可说是他的绘画理论。徐渭的画风和理论,开启了一种浪漫的创新运动,他对于后代的影响,可以从那些名画家的景仰之辞中看出。同样傲岸不羁的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却刻了这样的印章:“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青藤门下牛马走”;海派大画家吴昌硕则自称“于画耆青藤、雪个”;衰年变法,极富创造性的齐白石,则在《庚申日记》里写道:“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求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他又有题画诗云:“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
齐白石的话,不但说出了他对徐渭等人的崇拜之情,而且还理出了徐渭所开创的这个画派的发展脉络:青藤(徐渭)——雪个(八大山人,即朱耷)——大涤子(石涛)——老缶(吴昌硕),而齐白石则自愿做他们的继承者。当然,这中间应该还有同样愿做青藤门下走狗的郑燮(板桥)。
八大和石涛都是明朝皇室后裔,明亡之后,亡国之痛自然比别人更加深切些,心中一股抑郁之气,悲愤之情,发为绘画,情感就显得更为突出。朱耷先是削发为僧,后来又做了道士,既画花鸟,又画山水。但他所画之鸟,傲岸倔强,蓄势待飞;所画之花,“叶叶向南吹”;所画山水,多取荒寒萧疏之景;他的署名,常将“八大”二字、“山人”二字联写,类似“哭之,笑之”。正如郑板桥在八大画的题诗中所说:“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八大山人以这种感情作画,当然不会去讲究章法的完整性了,他所追求的是气韵和寓意,突出的是主观情感。
石涛在明亡后也出家为僧,他原名朱若极,石涛、原济都是他的释号,又称大涤子、苦瓜和尚。他不但作品多,造诣高,而且还写有《苦瓜和尚画语录》,在理论上建树也很大,所以对后世的影响更为深远。石涛云游天下,历览名山大川,所画山水,独创一格。郑板桥评之曰:“石涛画法,千变万化,离奇苍古,而又能细秀妥贴,比之八大山人殆有过之,无不及处。”(俞剑华编著:《中国画论类编》第1177页)石涛反对“泥古不化”,认为那“是识拘之也”,又反对“缚人于法”,说那样“反为法障之也”,他尊重独创性,提出“借古以开今”的口号,并且说:“至人无法,非无法也,无法而法,乃为至法。”他反对摹古,反对“为某家役”,因为那样“非某家为我用也”,反而被束缚于某家,“纵逼似某家,亦食某家残羹矣,于我何有哉”;他强调发扬自我,以自我为核心,去吸取、去创造,从而画出自己的面目来:“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纵有时触著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为某家也。天然授之也,我于古何师而不化之有。”在心物的关系上,他一方面很看重天地造化的功能,同时又十分强调心灵的感受作用,他认为画家应该面向自然山川,但却不能为山川所役,他强调必须以心感物,容物入心,从而达到心物合一的境界:“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归之于大涤也。”(《苦瓜和尚画语录》)终归于大涤者,即是以我役物,而非为物所役也。
石涛在这里特别提出批评摹古主义,反对法障,其实并非泛论,而是有所实指的。这就是清代初期盛行于文坛画苑的遵法摹古风气。
满族以落后民族入主中原,为了镇压反抗,又大肆屠戮,对商品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起了破坏作用。对于士人,则一面大兴文字狱,一面又重振程朱理学,以钳制思想。鲁迅曾追述他在清朝末年时所经历的情况道:“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按:指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等);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清朝末年的情况尚且如此,统治力强盛的清朝初年,思想控制之严,更可想而知了。
在这种形势下,个性主义受到遏制,而复古思想重新抬头,也是必然之事。
在绘画界,作为复古思潮代表的,是“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翬、王原祁。“四王”与“四僧”的人生道路不同,如果说“四僧”走的是民间野逸的路子,那么“四王”则身居官职,面向朝廷。王翬奉诏参加《康熙南巡图》的制作,王原祁奉诏画《万寿图》,还做过康熙的书画谱馆总裁,受命主编《佩文斋书画谱》,他们其实都做了宫廷画师。处于这种地位,当然也就循规蹈矩,没有张扬个性的心思了。位居“四王”之首的王时敏,就抨击“近世攻画者”是“多追逐时好,鲜知古法”,他分析画坛形势道:“唐宋以后,画家正脉,自元季四大家、赵承旨外,吾吴沈、文、唐、仇,以暨董文敏,虽用笔各殊,皆刻意师古,实同鼻孔出气。迩来画道衰熸,古法渐湮,人多自出新意,谬种流传,遂至衺诡不可救挽。乃有石谷起而振之。”那么,这位振兴画坛的石谷(王翬),到底有什么长处呢?王时敏称赞他“皴擦勾斫渲染开阖之法,无一不得古人神髓。昔人谓昌黎文少陵诗,无一字无出处,今石谷之画亦然”(《西庐画跋》)。原来是师古有成。而王翬本人则说:“以元人笔墨,运宋人邱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清晖画跋》)“四王”的画,常常在题跋中就标出是摹仿某人的,如“仿大痴”、“仿云林”、“仿文敏”、“仿梅道人”、“仿赵大年”、“仿董巨”、“仿小米”等。由于“四王”在当时画坛上的地位,他们的主张,影响很大,仿古之风,不但流行一时,而且延及有清一代。
对于“四王”绘画的评价,随着历史形势的变化,曾经大起大落。有清一代,对于“四王”极为尊崇,奉为画坛正统,追随者极众;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许多人又将其看作画坛祸首,备加贬责,并声称要革他们的命。直到1992年“‘四王’绘画艺术国际研讨会”的召开,这才有个较为全面的说法。“四王”提倡摹古、仿古,这是事实,其消极作用也是客观存在,但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其艺术成就。盖因天下事往往并不那么简单,某些思潮的受害者大抵是追随其后的末流,至于倡导者,由于本身是大家,却常能超越其局限性,而别有一番成就。而且在历史上,人们之以复古相标榜者,也并非真是都要对古人亦步亦趋,却往往有着更为深层的意义。中国文化史上的这一现象,倒是被一位洋教授参透了。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艺术史教授高居翰说:“关于中国绘画的传统问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当某个中国画家宣称他师法古人时你不必太信以为真——这种宣称只是为了使他们的创作在观众眼里显得名正言顺而已。”(《中国画鉴赏(二)》)高居翰在这里当然不一定实指“四王”,但他对“四王”,特别对其中的王原祁,评价是很高的。他在另一篇文章中,特地举了王原祁的晚年名作《辋川图卷》为例,来进行分析。他认为,“王原祁的《辋川图卷》(1711)再好不过地展示了他的正统性和个人成就”。该图卷是摹仿王维同名图卷的摹本石刻而成,“但事实上,对王原祁来说,他主要关心的既不是王维画中的诗意,也不是其风光特点,这些在石刻拓本中荡然无存,尽管王原祁在题跋中说在他创作时参考了王维的诗。”“王原祁于是在重画王维的构图时,有意把千余年传统中……发生于两极间的所有内容都囊括其中。”“如同拓片上所见的那样,王原祁《辋川图卷》的卷首按王维构图一开始的样子,描绘了华子岗、孟城坳等旧城垣的遗迹。古拙的画法使八世纪的构图很程式化,几乎像地图,如明显倾斜的、不稳定的地平面与移动的水平面,画山岭,墙垣和树丛等成袋状空间的方法,都非常适合王原祁反自然主义的目的。这些方法使他能随心所欲地分割绘画平面,在远近的画面间构成有力的联系,并把空间作为又一种易于把握的抽象设计因素。另一方面王维或王维的摹仿者用来描绘岩石山岭的方法,王原祁觉得没用,而代之以用董其昌的笔法,从黄公望那里得到的程式。”(《王原祁与石涛:有法与无法的两极》)可见,王原祁用的是一种综合方法,而综合里面也就有了创造。旅美画家王己千也很赞赏王原祁,他认为王原祁的画容量大,把丰富的笔墨摆入一个很小的范围,比元四家还要复杂。“通常王原祁画中的一小部分就足够了,如果你把一小部分放大,你将看到他尤其注意结构和笔墨的多样化。至于里头的变化,我要说他比元代画家更进了一步,那就是为什么我特别喜爱并且仰慕王原祁的原因。我不以为他只在画画,相反的我认为他在用笔墨表现纯粹而抽象的美。”(徐小虎记:《画语录》(十一))
当然,作为一种思潮看,他们是顺应正统,而排斥个性主义的,对当时的复古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正如文学界在清初沉重的气氛中,仍有性灵派的延续一样,绘画上的个性主义革新派思潮,也在商品经济的滋养下,仍在民间发展。最有影响的,就是扬州画派。扬州画派兴盛于乾隆嘉庆年间,已经是清代中叶了。这时,清朝贵族的统治权力已经巩固,这个皇朝看来很是显赫,但国力却开始转衰了,正如《红楼梦》中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所说:“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具有叛逆之音的文学作品《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出现,就是这种形势的产物,则在绘画上出现非正统色调的扬州画派,也就并不奇怪了。
扬州画派以“扬州八怪”闻名。但八怪的名单却并不确定,各种画史上说法不一,加起来则超过八人,计有:郑燮、金农、高凤翰、李鱓、李方膺、黄慎、高翔、汪士慎、边寿民、华嵒、陈撰、闵贞、杨法等,大概“八”只是个约数,并非实指,似乎也可不必深究。但他们在绘画上的特色却是明显的。正如陈师曾所说:“如金农、罗聘、高凤翰、李鱓、黄慎、郑燮之流,或为布衣,或为卑官,不衫不履,落拓江湖,既非内廷供奉,不受院体之濡染,各肆其奇,别开生面。”(《清代花卉之派别》)这就是说,他们都富有生活阅历,境况不佳,接近民间,不受正统思想的约束,具有叛逆精神。这种精神反映在书画上,在正统文人看起来,就显得有点“怪”了。比如在书法上,当时的科举考试所要求的“馆阁体”,特点是“乌”、“光”、“方”,而金农却以秃笔重墨为之,像小刷子刷出来一样,有隶书之体势,含金石之气派,显然与众不同,号称金农漆书;而郑板桥则另创一种“六分半书”,也是别具一格,其实凡他所写之字,无论是何种书体,都表现出他的个性来,鲁迅曾评论他的篆字道:“因为有人谈起写篆字,我倒记起郑板桥有一块图章,刻着‘难得糊涂’。那四个篆字刻得叉手叉脚的,颇能表现一点名士的牢骚气。足见刻图章写篆字也还反映着一定的风格。”(《难得糊涂》)
扬州八怪的画,以郑板桥影响最大,他喜画兰竹,题材虽然不广,但却画得极有风致,而且寓意很深。那首有名的题画诗,就表明了他的寄托:“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正因为他把这种关心民间疾苦,痛恨官场黑暗的愤激之情,泻在这一枝一叶上,所以就越出常规,画出其桀骜的个性来。于是人们称其为“怪”。对于板桥及其他扬州画家的“怪”,人们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词曲家蒋士铨有题板桥画兰诗,是赞其怪的:“板桥作字如写兰,波磔奇古形翩翩。板桥写兰如作字,秀叶疏花见姿致。下笔别自成一体,书画不愿常人夸。颓唐偃仰各有态,常人尽笑板桥怪。”(《忠雅堂诗集》)编写《扬州画苑录》的汪鋆,则对这一画派大加抨击:“怪以八名,画非一体。似苏张之捭阖,偭徐黄之遣规。率汰三笔五笔,复酱嫌粗;胡诌五言七言,打油自喜。无非异趣,适赴歧路,示崭新于一时,只盛行乎百里。”但历史证明,汪鋆的判断错了。扬州八怪的画,岂止示新于一时,盛行乎百里,它不但流传甚广,而且愈来愈显示出其历史意义。
郑板桥虽然没有系统的画论,但在有些题画诗和画跋中,却表现出他对于绘画创作的精湛见解。比如,他有一则画竹题跋云:“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板桥题画兰竹》)这段话,把创作过程讲得很细致透彻。创作当然要面对现实,但客观对象却不能直接进入作品,它必须经过主观意识的感受和过滤,形成一种意象,即不同于“眼中之竹”的“胸中之竹”;但是,在落笔过程中,又会“倏作变相”,所以“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因此,他特别强调“意在笔先”、“趣在法外”。这一理论,并非宣扬艺术创作中的主观随意性,不是要求画家脱离实际,而是将“师法自然”的传统理论推进了一步,要求画家在面对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发挥主体的作用,达到主体与客体的有机结合。这种见解,是从他自身的创作经验中提炼出来的,显得特别的可贵。
“扬州八怪”的画风,虽然经过一些曲折的道路,但是到得晚清,又在海上画派中得以发展。
晚清的上海,是最早对外开放城市之一,资本主义势力发展得最快,新思想当然也就接受得最多。上海的文化,既具有强大的吸力,引人注目,又遭到传统文人的拒斥。“海派”二字,曾经被当做一个背离传统,华而不实的贬词来使用。20世纪30年代,生活在北京的作家沈从文就用这两个字来批评上海文人,引起了一场京海之争。鲁迅曾经撰文揭穿其底蕴道:“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京派”与“海派”》)这是就其社会背景而言,从艺术本身看,则海派艺术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富有创新精神,这是不可抹煞的长处。所以,海上画派与中晚明以来的革新派画风,有着天然的联系。
清末民初时期的海上画派出了许多名家:赵之谦、任伯年、虚谷、吴昌硕等等。他们的艺术感觉有殊,而标新立异之志相同,遂形成一股艺术革新的力量。其中,吴昌硕出道较晚,而影响最大。
吴昌硕早年专攻书法篆刻,不事绘画,自称五十岁以后始作画(实际上或者还要早些),但并无自信,曾求教于任伯年,任伯年叫他随意画几笔看看,觉得他用墨浑厚挺拔,不同凡响,于是大加鼓励,说是笔墨已胜过自己。这使吴昌硕信心大增,从此努力作画,终于成为大画家。由于有着上述的经历,吴昌硕发挥己之所长,以书法篆刻的手法入画,使自己的绘画具有篆籀笔意,金石韵味。他以大写意的花卉画为主,笔力苍劲,设色古艳,气势磅礴,在清末民初画坛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吴昌硕的画,重气不重形,即所谓“苦铁画气不画形”是也。正因为重气,所以也就着重运气的意念,即郑板桥之所谓“意在笔先”也。
但艺术之气毕竟是相通的,不能完全以地域为限。承续徐青滕——吴昌硕一派画意,并加以发扬光大的,却是定居在北京的齐白石。
齐白石出身于湖南农家,早年曾做过细木匠,二十七岁以后专门从事绘画。开始学的是工笔画,后来决心变法,对徐青滕一派甚为倾倒,大约在四十岁以后,改作写意画。齐白石虽云愿做青藤门下走狗,但极重个人的创造性,要“用我家笔墨写我家山水”,画出了自己的特色。齐白石的画,注意表现对象的要点,避免芜杂和零乱,讲究删繁就简,极重笔墨情趣,不追求形似,但又不脱离描写对象。他有一句画论,辩证地说明了其间的关系:“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齐白石出于农家的爱好,喜画花卉、瓜果、鸡虫、鱼虾等贴近生活的东西,但从不把它们当作简单的自然事物来描写,而都倾注了自己的情感,画得极其生动。正如王朝闻所说:“他靠他热爱生活的感情,观察的能力和敏锐,深知对象的美之所在,排除了流行的成见,敢于把自己深切的感受表现出来,其作品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境界。”(《再读齐白石的画》)
后来有些画家受了西方现代派绘画的影响,用中国画的笔墨来画抽象画,而张大千又大画其泼彩画,那应该另当别论了。
——发表于2001年《学术月刊》第十期,收入2003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