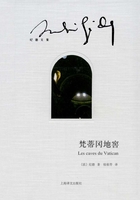我在蒙巴萨时住在阿里·本·萨利姆族长家,他是沿海地区的地方长官,一个好客、仗义的阿拉伯老绅士。
蒙巴萨有着儿童画里天堂的样子。深海环抱岛屿形成了天然良港,路面由白色的珊瑚礁筑成,种有广阔的绿色芒果树和奇妙而光秃的灰色猴面包树。蒙巴萨的海蓝得像矢车菊,在海港入口处,印度洋的狭长碎浪绘出一条轻描淡写的白色弧线,即使风平浪静时也发出低沉的雷声。蒙巴萨的窄巷城镇全是由珊瑚岩建造的,掩映在浅黄、玫红和赭色的美丽房屋阴凉下。城镇上方矗立着雄伟的古堡,有着厚墙和炮眼,三百年前葡萄牙人和阿拉伯人曾在这里对峙僵持。古堡比城镇的颜色更加暗沉,似乎在岁月的流逝中,它由于位置高高在上而独饮了更多暴风雨中的日落苦酒。
艳丽的红色金合欢在蒙巴萨的花园里盛放,颜色热烈得匪夷所思,叶子却又精致纤弱。太阳炙烤着蒙巴萨,这里的空气里有咸味,每天的微风都带来新鲜的东方湿气,连土壤都是咸的,所以寸草不生,地面就像舞池一样空。但古老的芒果树长着茂密的深绿色叶子,仁慈地洒下绿荫,它们投下一小块圆形的黑色阴凉。在我所知道的所有树种中,只有芒果树让人想起集会的场地,人类的社交中心,就像村庄的水井一样适于交际。大市场在芒果树下举行,树干周围的地面上摆满鸡笼,堆起西瓜。阿里·本·萨利姆在本岛上有一栋舒适的白色房子,就在大海的臂弯里,有一条长石路与大海相连。石路边有栋小客房,游廊背后主楼的大房间里藏有很多阿拉伯和英国的精美古玩:老象牙和铜器、拉穆运来的瓷器、天鹅绒扶手椅、老照片,还有一台大留声机。其中有一个绸缎内衬的小箱子里放了一整套四十年代讲究的英国瓷器茶具,这是年轻时期的英国女王和她的配偶送给桑给巴尔苏丹的儿子和波斯沙阿的女儿的结婚礼物。女王和亲王祝愿这对伉俪像他们一样幸福。
“他们后来幸福了吗?”当阿里族长一个个取出小杯子,把它们放在桌上向我展示时,我问他。
“唉,没有,”他说,“新娘不愿意放弃骑马。她让运嫁妆的单桅木船把她的马也一起运来了。但桑给巴尔人不允许女士骑马,所以这惹出很多麻烦。公主宁可放弃她丈夫也不愿放弃她的马,最后婚姻破裂了,沙阿的女儿回了波斯。”
蒙巴萨的港口停了一艘生锈的德国货船,准备返航。阿里·本·萨利姆的斯瓦西里桨手划着小艇载着我,我们往返岛屿时经过了这艘货船。甲板上立着一个很高的木箱,箱子边缘上沿露出两个长颈鹿的头。法拉去过船上,他告诉我两头长颈鹿来自葡属东非,正准备去汉堡参加一个巡回动物展览。
长颈鹿精巧的脑袋转来转去,好像受到了惊吓,很可能它们确实受到了惊吓。它们从没见过海。窄箱里的空间可能只够站立。世界突然间缩小了,在它们周围变化、逼近。
它们无法了解,也无法想象正在驶向的堕落。它们是骄傲天真的生灵,是伟大平原上温和的漫步者,它们一点也不了解囚禁、严寒、恶臭、烟味和兽疥藓,更不了解一个无所事事的世界里可怕的无趣。
穿着暗色脏臭衣服的人群会从街上的风雪里挤进来观看长颈鹿,来满足人类凌驾无声世界的优越感。他们会在优雅、耐心、黑眼线的脑袋伸出动物展览栅栏时指指点点,嘲笑它们细长的脖子,因为它们的脖子在栅栏里显得过长。孩子们要么在刚看到它们时害怕得大哭,要么会爱上长颈鹿,喂面包给它们吃。然后爸爸妈妈们会觉得长颈鹿是温和的野兽,相信它们会带来愉快的时光。
它们面前是漫漫无期的岁月,长颈鹿会不时梦见自己失落的家园吗?那些长草和荆棘树、河流、水塘和蓝色的山,现在都在哪里啊,它们去了哪里?平原上甜美高爽的空气撤去了。其他长颈鹿去了哪里?那些与它们并肩行走,一同慢跑过起伏的大地的长颈鹿呢?它们离开了,它们都走了,而且似乎不会再回来。
夜晚的满月呢?
长颈鹿在动物展览的大篷车里醒来,醒在闻起来像烂稻草和啤酒味道的逼仄箱子里。
再见了,再见了,我希望你们死在路上,双双死去。那么就不会有某个小小的高贵脑袋从箱子的边缘探出来,在蒙巴萨的蓝天下被吓到,不会被独自留下,待在无人知晓非洲的汉堡,脑袋转来转去。
至于我们人类,在没有遇到那个会严重侵犯我们的物种之前,是无法体面地请求长颈鹿原谅我们所做出的侵犯行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