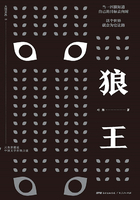有人说,茉莉又收到了很多来信,还有美国的贺卡呢!
贺卡算什么?因为同住一个家属院,我还知道那个人给茉莉寄来了美圆!
美圆,这是美圆!这上面是美国总统华盛顿!我们曾亲眼看见茉莉的母亲,在小院里跟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比划着,介绍手中的钱。
也正是这副场景彻底改变了茉莉母亲给我的印象。多年以来,这个口音很像外地人的女人,像她窝囊的男人一样很少跟外人讲话。可现在,她终于可以扬眉吐气。
茉莉给我们的压力好大。不知从哪天起,我们在小院里看见她,会很快低下头走掉,行同陌路。
后来,茉莉就去了唐大鲁的发廊。唐大鲁在我们小院里开店多年,从未收过女徒弟,他很紧张,我们都看出来了。
再以后,茉莉的变化就更令人惊讶。她的衣着和穿戴一天天斑斓起来,发型也变得成熟而又妩媚,像一条热带鱼。
这一切,都为她去见那个人做好了准备。
是的,那个人短暂回国,家住北京,一定要茉莉“飞”过去见面,机票都订好了!
可当时我正忙于高考,直到放暑假,母亲才把这一消息告诉我。我心里再一次酸酸的。
不过,仅过了几天,茉莉就回来了。茉莉依然在唐大鲁的发廊里忙碌着,她已经能剪出许多样式的发型了。
有一次我去理发,本来唐大鲁给我披好了发衣,可茉莉突然进来,把唐大鲁赶到一边去。剪刀喀喀,我们却始终没有说话。直到临别,茉莉忽然从背后叫住我,哎,考得怎么样?出于礼貌,我回过头来说,还行,你呢?啥时候去美国?
茉莉嘴角一翘,没有回答。我忽然从她眼睛里,发现了细碎的泪花!
那真是一个漫长的暑假。谁能料到比我的通知书先来的,竟会是茉莉的喜贴呢?茉莉在我们卑微的落寞的小院里结了婚!嫁给了矮倭瓜一样的鳏夫唐大鲁。
那些天,小院里到处都是碎盘子碎碗的吵嚷声。
父母没去参加茉莉的婚事,他们更害怕得罪茉莉的父母。他们和我一样,听着不远不近的吵骂,长久地陷入沉默。
来年大学暑假,我第一次带男朋友回家,在小院里看见茉莉母亲正怀抱一个胖娃娃跟我父母聊天。旁边,是高挑又丰满的茉莉。
我情不自禁跑起来,远远冲那边喊着,茉莉!
你究竟想什么心事
妻子进门的时候,张三正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抽烟。
妻子匆匆放下坤包,快步走上前来吻一下张三的脸,怎么啦亲爱的,想心事?
张三吐出一个优雅的烟圈笑笑。没,我能有什么心事?
鬼才信你!那你好好的发什么愣呀?妻子半蹲在张三面前耐心地研究张三的脸。
张三觉得好笑。——自己昨晚不是熬夜看球了嘛,今早睡到快十点钟才起床,肚子不饿,饭也没吃,就想抽支烟呢,妻子提前回家搞起“审问”来了。
你这么早回家干吗?有事你就忙,我抽支烟歇歇。张三懒散地说。
歇歇?妻子忍俊不禁。刚刚起床还没歇够?
妻子轻轻起身坐在了张三身侧,温柔地捏着张三的肩膀。说吧,究竟想什么呢?
张三惊讶地侧过脸来看着妻子。你这是怎么了?
妻子纤细的手指按上了张三的鼻头。好了,好了,跟我还玩什么深沉?我知道我最近只顾忙工作,对你关心不够,你在心里怪我了吧?
张三摇头否认。
难道你在猜疑我对你不忠?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张三愈发觉得好笑,“叭叭”地抽着烟,也不弹弹,烟灰都弯成了一条钩子。要我怎么说你才相信呢亲爱的?我真的没事,我就是坐着抽只烟!
没事?妻子神秘地笑着。那你干吗不吃我给你扣在桌上的早饭?干吗不打开电视看?你昨天新买的那套爱不释手的《藤泽秀行名局精选》又放在哪了呢?还想骗我,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可是你妻子。我才是全世界最最懂你的人!哼。
张三傻了。张三想解释自己不想吃早餐,不想开电视,不想看藤泽秀行,可“不想”能算哪门子理由呢?为什么会“不想”呢?——难道自己真有心事不成?可笑。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张三迟钝的脑子越发发懵了。
为了不冷落妻子关切的眼神,张三还是略带点烦躁地回答,老婆,我没事就是没事,没事不需要理由。你去忙你的好不好?
妻子竟开始怪怪地打量起张三来了,好象张三是个陌生的天外来客。
张三!你从前可不是这样的!你有话从不瞒我,我一直都以为我们之间无话不说没什么好隐瞒的呢。
张三烦了,求求你老婆,别闹了!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我不想再跟你说话了。
你还敢说自己没心事?妻子仿佛捉住了张三的什么把柄,声调徒然高了起来。你明明是有一肚子心事无从发泄还硬要瞒我!你究竟安的什么心哪?我真没想到你这人这么阴险!
阴险?张三将烟蒂狠狠地摁进烟灰缸里,抬了头猛盯妻子,眼神里充满了疑惑、失望、疲惫甚至恐惧。张三一字一句地问,你提前回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
妻子听了拼命地摇头。眼泪迸溅。
看来这个家是过不下去了!妻子话一出口,张三惊得险些从沙发上跌下来。这叫什么事儿啊?张三的倦意在这一刻彻底消失得无影无踪,可脑袋却像遭受了一记重拳被打晕了。
我早该猜到你另有心事的。妻子哭诉着。这些年来我有多么爱你,可你这样对我公平吗?我也是人!我也需要与人交流被人理解,有什么事不能坦然地摆到桌面上来谈呢?你从前就开过“离婚试试”的玩笑,难道你早有准备?
张三哭笑不得。他实在记不清自己何时何地开过这样一个玩笑。
说吧,对方是谁?我不是一个脆弱的女人,至少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脆弱。
张三伸手去摸烟盒,却被妻子抬脚踩住。张三只好哀求说,求求你别闹了,你还想让我说什么?
你究竟想什么心事?妻子斩钉截铁地问道。
没有。真的没有。我拿人格担保我真的没有心事行不行?张三一字一句肯定地回答。
好吧!妻子绝望地闭上了眼睛。谢谢你终于让我看清了你的真实面目,我终于明白我在你心目中是什么地位了!也请你以后别再随便作践自己的人格,我们该结束了!
于是妻子不顾张三强烈地阻挠,疾步跑出了门外。妻子消瘦颤抖的背影让张三悲痛欲绝……
屋内又恢复了平静。张三回到衣架前时无意中发现了妻子忘记带走的坤包。
打开,里面赫然放着一张已经签过妻子名字的离婚协议书!
迷路的女孩儿
吴建新识的女友汪梅,在一所乡镇中学教书。
汪梅每有晚自习,吴建都要骑摩托车去二十里外的学校接她回家。
接送虽然辛苦,可吴建喜欢汪梅轻轻揽住自己后腰、小鸟依人般的模样。再者乡下美丽的星空和清新的空气,也常让吴建感到心旷神怡。
饱受爱情滋润的吴建,爱上了这跑夜路的感觉!
可最近,他们俩遇到麻烦事儿了。
吴建的摩托车,总在半道儿上被莫名其妙地扎胎。
这很要命。摩托车夜路上被扎,前不靠村、后不着店,根本就没法儿修理。两个人摸着黑推车,一步步艰难前行。
那滋味,实在遭罪!
吴建就觉得这事儿蹊跷:为何车总在回来的路上、差不多同一地点被扎?而且扎进轮胎的锐器总是玻璃碴或图钉,显然不合常理……
吴建下定决心,非要查个水落石出!
于是,在一个汪梅没有夜辅导的晚上,吴建仍然骑车来到了那个经常“出事”的土坡附近,将车推入小树林,自己委身藏进草丛里。
适值初秋,花草葳蕤,百虫啾啾,月盘朝开阔的野地里散下大片银辉,不远处溪流在山坳里淙淙流淌。这一切都让吴建觉得陶醉。
但那个可恶的目标却很快出现了!
那是个个头不高、十五六岁模样的女孩儿,忽然就从野地里奔出来。距离较远,借助月光,吴建只能隐约看到她双手平端一张薄儿木板,鬼鬼祟祟向公路跑去!然后她警惕地四下张望,迅速抖动木板将一些杂物撒落在公路上!
谜底揭开了。吴建禁不住大吼一声:“哎,你站住!”随即像头跃起的猎豹,向着女孩儿方向飞扑过去。
女孩儿被平空的断喝吓得几将跳起来,丢下木板急忙撒腿就跑!吴建紧追不放。
女孩儿箭一样钻进玉米地里,跑不多远却忽然被盘根错节的枝蔓绊倒在地,吴建喘着粗气奔上前反剪住其双手,像提小鸡似的将她押了出来。
“说!为什么在路上搞破坏?”吴建气喘吁吁,怒声逼问。
女孩儿早就哭了,只是没有哭出声,淡薄的月光下,满脸湿亮。任凭吴建怎么晃她、问她,就是不回答。
“小小年纪就不学好!”吴建继续训斥:“知道半路上给车扎了胎,别人多难受吗?”
这时,女孩儿却开口了:“我就是要让他们难受!”一边眼泪,汹涌而出。
吴建越发气不打一处来:“看来你是故意的!走,我送你去派出所!”
女孩儿听了拼命地扯住草棵,像一小滩泥巴,怎么也拉不起来。
“好,只要说清你为什么这么做,我就放了你!”吴建有点心软了。
女孩儿一听,哭声忽然开始放大:“是你们杀死了我爸爸!你们赔我的爸爸!……你们都是凶手!我要给爸爸报仇!呜……”
吴建感觉讶异,这孩子该不会精神有问题吧?“不许撒谎!慢慢说……”
女孩儿继续哭喊着:“十天前的晚上,大约九点钟,我爸爸,呜……被一辆面包车轧伤了……我拼命喊人,拼命喊救命……就是没有一个人来理我!轧伤爸爸的汽车也逃走了……我喊了整整两个小时,都没有一辆车肯停下来帮我……”
“所以我每天晚上九点钟都来路上撒钉子……我要给我爸爸报仇!他死了,你们所有人都是凶手!……”女孩儿歇斯底里地怒吼着。
吴建当即愣住!他无论如何没想到,在这弱不禁风的女孩儿背后,竟有如此凄惨的经历。
“那你现在还上学吗?”吴建试着温和地说话。
女孩儿的哭声却再一次放大:“我想!可妈妈早就改嫁,我没有钱交学费了……”
吴建的泪水一下子冲出了眼眶。“给!”他慌忙从裤兜里掏出两百块钱来往女孩儿手里塞去。“先拿着!好妹妹,大哥刚才是逗你玩呢!别害怕。”
女孩儿仍旧抽泣着,坚决地摇头。
吴建忽生一计:“要不这样,好妹妹,你先拿着钱交学费,明晚大哥我也来和你一起撒玻璃、抓坏人怎么样?”
女孩儿用瘦弱的胳膊抹着眼泪,将信将疑接过钱,深深地望了吴建一眼,突然爬起身来跑掉了。
接下来的几天晚上,吴建和汪梅一早就来到那处土坡附近,等那女孩儿再次出现。可每次,他们的等待都落空了。
吴建直后悔没留下女孩儿的住址。
站在广阔的星空下,吴建想,但愿那女孩儿是迷路了吧,她再也找不到这个让她噩梦开始的地方了。
做一回别人的老公和老爸
半夜,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是个女人打来的。女人在电话里哭着问,是你吗?我好害怕!
我没听出是谁,连忙安慰她说,别怕,怎么了?
女人说,女儿现在正在手术室里,我好害怕!我怕失去她,你知道我有多么爱她吗?如果她出了事,我简直不想活了。
呀,她是打错电话了。
可我的同情心空前地膨胀起来。看看身边熟睡的妻子,我用尽量轻柔的话语劝告说,你坚强点,什么困难都会过去的,相信女儿不会有事!
女人呜咽说,谢谢你,这个世界上也许只有你还在乎我们,你知道女儿最近的成绩吗?她又考了全班第一名!可是她的病,她不让告诉任何人,她不想让老师和同学们来看她。
我说,女儿好样的。
女人听了,情绪似乎稍稍有了些放松。女人说,女儿现在不但学习刻苦,生活上也学会俭朴了呢,不再像以前一样喜欢乱买新衣服,还有,她还知道整理家务了,知道帮我做这做那,乖得像一只小猫,我现在真是一刻也离不开她啊!
我说,女儿真棒。
她十一岁了!女人口气变得自豪起来。在同龄的孩子中,她是最高的。像不像你?
我连忙说,不,我个子不高。
我以为这下女人该听出来了,可她仍深深地沉浸在叙述当中。其实,女儿能长一米六五就够高了,你说呢?
我不置可否。
女人的哭泣声小了下去,话语里充满了慈祥。女人说,可女儿再懂事也还是个孩子。前几天,邻居张叔叔给她抓了只鸟,她见了喜欢得不得了!每当我看到女儿和鸟玩耍的样子,我真感觉开心,感觉身上所有的疲劳统统都没有了。
你说,咱们女儿像不像一只美丽的小鸟?女人再次轻声地发问。
我该怎么回答呢?女人究竟把我当作了何人?是远在异地的丈夫?还是未能见面的情人?我开始为自己冒失地应答而感到尴尬。
再者,如此深夜,与一个陌生女人轻言细语,若被妻子醒来听到,岂不是一件很难解释的事?
于是,我选择了沉默。我不做声,是希望女人有所察觉。可事实上女人非但未察觉,反而话语仍像潺潺的溪水一样流淌个不止。
女人说,女儿最怕打针的,你还记得吗?她小时候一听到打针,嗓子都哭哑了。她7岁那年冬天,一天晚上磕破了头,去中医院缝疤,女儿的哭声搅得整座病房楼上的灯都亮了,身上棉袄都湿得透透的。
女人说,女儿在家里淘,可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乖,你记得吗,每一次我去幼儿园,去学校里,她都是老师嘴里的乖宝宝,学东西最快,最爱帮助别人,被男孩子欺负了也总是回家才掉泪,小小年纪就知道孝顺老人,爷爷在的时候,她从来都是他的开心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