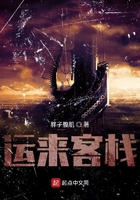答: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个问题与我在上面的评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在帮助我们认识何为自由秩序以及这种自由秩序为什么可欲的方面有着很大的意义;我想,我们无论如何强调这一点,都是不会过分的。当然,关于哈耶克的自由主义与非西方社会之间的关系,我在发表的论文中确实没有做过讨论,其间的主要原因是哈耶克本人不曾在这个方面做过任何系统的努力。而哈耶克之所以没有做这样的努力,实是因为哈耶克认为对不同文明进行比较研究乃是极具雄心的构想,非一般学者所能企及。他在赞誉研究不同文明的着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时就做过这样的解释。
不过,根据我对哈耶克论着的研读,我发现哈耶克在讨论其他问题的时候偶尔也论涉到了自由主义与非西方社会的关系问题。我想在这里具体阐发一下他的这些观点。尽管这些论述并不是系统论辩,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个人认为,哈耶克的有关论述并不会因此而减损它们对于我们的启示意义,相反,它们完全可以从另一个维度为我们提供反思我们自己在借鉴和学习西方文明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哈耶克曾在下述四个方面论涉到了这个问题:
第一,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指出,发展中国家应当从西方国家学习西方早先建构文明的方式和对自由的信奉,而不应当借鉴和采纳西方国家在成功发展以后所引发的各种替代性方案的梦想:一是因为正是对自由的信奉,才使得西方世界得以充分地利用那些能够导致文明之发展的社会力量,并使西方文明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迅速发展;二是因为各种替代性方案虽说会使发展中国家较快地模仿并获致西方的若干成就,但是它们亦将阻碍这些国家做出它们各自的独特贡献。
第二,哈耶克在《作为一种发现过程的竞争》一文中指出,作为一种发现探索过程的竞争,在那些高度发达的经济制度中极为重要,但是它之于低度发达的社会却有着更大的重要性,一是因为那种以为我们在一个低度发达国家(即首要问题乃是发现什么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可资使用的那种国家)中也能够事先确定其社会结构的观点,或者那种以为我们能够预测出我们采取的任何措施对这样一种国家所具有的特定影响的观点,纯属是异想天开;二是因为只有当少数乐意且有能力尝试新方法的人能够使众人感到有必要效仿他们并且同时又能够为众人指明方向的时候,风俗习惯才可能发生必要的变化;竞争不仅指出了人们如何方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具效率,而且还迫使那些依赖市场获取收入的人直面这样一种抉择:要么效仿更为成功的人士,要么失去部分或者全部的收入;正是依凭这样一种方式,竞争产生了一种非人力的强制:它迫使无数的个人必须以一种任何刻意的指令或命令都不可能促成的方式去调整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第三,哈耶克在《理性主义的种类》一文中专门讨论了日本思想家应当如何看待西方理性主义的问题,并且明确告诫日本思想家,那些把欧洲传统中看似最具特色的某种东西推至极限的学派,实际上与那些并不充分承认有意识理性之价值的人一样,都是极其错误的,只是这二者的错误方向不同而已:前者完全无视理性的限度,而后者则完全无视理性的作用。
因此,哈耶克希望日本思想家能够研究和认识西方社会中的与唯理主义相区别的“批判理性主义”传统,因为在哈耶克看来,它在创建现代欧洲文明的基础,尤其是在创建自由主义的政治秩序方面很可能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当然,哈耶克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对于非西方社会的中国思想家来讲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他在该文中指出,“颇为幸运的是,这种建构论唯理主义并不是欧洲传统可以贡献给人们的唯一的哲学……你们还可以发现另外一种较为低调且比较平实的传统:尽管它在建构宏大的哲学体系方面着力不多,但是它却很可能在创建现代欧洲文明的基础,尤其是在创建自由主义的政治秩序方面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这种传统并不是一种植根于欧洲思想发展某个特定阶段的片面的夸张之物,而是提出了一种真正研究人性的理论,所以它应当可以为你们的研究提供一个基础,而你们自身拥有的经验又能够使你们在发展和推进这种基础的方面做出重要的贡献。这种有关心智和社会的观点明确认为,传统和习惯在心智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第四,也是最为重要的,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三卷中极富洞见力地指出了非西方社会从西方国家移植民主制度的前提性问题,即非西方国家在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的时候必须关注支撑这一制度的很可能未形诸文字的相应传统和信念。
哈耶克明确指出,“正是这些传统和信念,在那些较为幸运的国家中始终构成了它们的宪法得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基础,尽管这些传统和信念并没有明确陈述出宪法所预设的全部内容,甚或还没有形诸于文字。
当然,新兴国家的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因为在这些国家中,甚至连一个与欧洲国家长期信奉的法治理想略具相似的传统都没有;据此我们可以说,这些新兴国家实际上只是从欧洲国家那里移植了民主制度而已,但是它们却没有这些民主制度所预设的信念和观念作为它们的坚实支撑。
……如果我们不想让移植民主制度的种种尝试归于失败,那么我们在建构这种新的民主制度的时候,就必须对大多数作为这些制度之基础的未形诸文字的传统和信念给出详尽的阐释,因为在成功的民主制度中,正是这些传统和信念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制约了人们对多数权力的滥用。当然,大多数移植民主制度的尝试已告失败的事实,并不能够证明民主这个基本观念不具有现实适用性,而只能够证明这样一个问题,即那些在西方国家曾一度运行大体良好的特定制度乃是以人们默会地接受某些其他原则这个预设为基础的——这就是说,在西方国家中,这些为人们以默会方式承认的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人们的遵循;因此,在那些尚未认识到这些原则的国度里,人们就必须把这些默会性原则作为宪法的一部分明确写进成文宪法之中,就像把其他的原则写进宪法一样。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做这样的追问,即西方代议制度以默会方式预设的那些观念,究竟如何才能够被明确地纳入到这类成文宪法之中呢?”我个人认为,哈耶克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辩,不仅涉及民主制度,而且也可以同样适用于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司法制度等,因此他的这一论辩对于一直在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与后来建构的现代制度间繁复关系的中国论者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如我们所知,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制度建设与传统文化之间的高度紧张始终困扰着中国论者,但是其间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在讨论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一般都是从孤立的角度来讨论制度变革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而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些问题:(1)西方现代的各种制度与支撑它们的默会知识和信念之间的紧密关系;(2)中国正在逐渐建构的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3)如何通过制度性安排来为正在建设的各种制度提供它们所必需的支撑性基础。
四、关于TheConstitutionofLiberty的翻译问题
问:在讨论了上面的问题以后,我想就哈耶克研究中的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请教于你。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耶克在1960年出版了他的重要着作TheConstitutionofLiberty。有的学者把这部着作的书名翻译成了《自由的宪章》
(台湾周德伟等人),刘锋在译霍伊《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一书时将其译作了《自由宪法》(三联书店1992年版),你将它译作了《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1997年版),而杨玉生等人在此后又把它翻译成了《自由宪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差异如此之大的译法,显然说明这已经不是一个翻译上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涉及理解的问题。因此,是否可以请你先就这个问题谈一谈你的看法?
答:我完全同意你的判断,这不是一个翻译上的技术问题,而是对哈耶克自由主义社会理论和知识观的理解问题。实际上,我在翻译哈耶克该书书名的时候颇费心思,学术界的好友也相当关心这个问题,尤其是许倬云先生和林毓生先生,他们在得知我正在翻译哈耶克这部着作以后,曾先后专门写信提醒我不要将书名译作《自由的宪章》并建议翻译成《自由的构成》。
但是,经由详尽考虑以后,我还是主张把它译作《自由秩序原理》,并且还专门就采用这个译名的理据写了一篇文章:《〈自由秩序原理〉抑或〈自由的宪章〉:哈耶克TheConstitutionofLiberty书名辨》(载拙着《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在这里,我只想征引哈耶克本人在《法律、立法与自由》“导论”中所提供的一个解释以及我本人对它的理解来说明这个问题。哈耶克在该书中指出:“如果我早在出版TheConstitution of Liberty 一书时就知道我会着手本书所试图进行的研究工作,那么我就会把那部着作的标题留下来,用在现在这部书上。我在当时采用constitution一词时,是在该词的广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其间我们亦用它来指称人的适宜的状态(thestate of fitness of aperson)。
只是在现在这部书中,我才致力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什么样的宪法性安排(constitutionalar rangements),即法律意义上的宪法性安排,才可能对维护个人自由有最大的助益。”
哈耶克这段晚出的关键文字,按照我个人的理解,至少向我们揭示了理解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这一书名的两个要点:首先,这个书名中的constitution乃是指一种适合于人的生活状态,即个人的自由状态或集合意义上的自由秩序;同时他通过这个书名所试图表达的乃是TheConstitution of Liberty这本书的研究对象,一如他在该书的第一章开篇所指出的,“本书乃是对一种人的状态的探究;在此状态中,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所施以的强制在社会中被减至最小可能之限度”。
当然,“自由秩序”这个研究对象不同于《法律、立法与自由》所确立的具体研究对象,因为后者的具体研究对象或试图回答的具体问题乃是什么样的宪法性安排才可能对维护个人自由有最大的助益。
其次,哈耶克的上述说明文字还表明,他乃是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处理前后两本书的具体研究对象的,即从重述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层面向主要是重构法律制度的层面的转换,后者乃是在文化进化规则系统限度下的论题。
20世纪50年代,哈耶克对自由遭受威胁的问题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在过去,“人们只是模糊地认识到了这一理想或者说不尽完善地实现了这一理想;因此,如果要使这一理想成为解决当下问题的指导,就必须对其做出进一步的厘定和阐明”。
正是这种判断,决定了哈耶克在阐释原则的层面上研究人的自由秩序的问题;当然他也对一些重大的政策进行了分析,然而这种分析充其量也只是“对这些原则的验证”。
到了六七十年代,哈耶克日益认识到,要对那些以制度作为基础的支配着当下西方人的种种信念做出重大的修正,仅诉诸于原则的阐释和寄希望于社会的道德是不充分的,这是因为那些信念所依凭的原本旨在保护个人自由的宪政制度已无法实现它们的目的,所以必须从原则阐述的层面转向变革这些制度的层面,而这就是哈耶克所谓的文化进化下的“制度性发明”(institutionalinvention)。
正是基于上述我对哈耶克说明的解读,我认为应当把哈耶克社会政治理论下的constitution理解成一种“秩序”,而把整个书名译作《自由秩序原理》:综而述之,采用这个译名,一是为我们理解作为一位纯粹经济学家的哈耶克转向研究社会政治哲学的学术旨趣留下了可能的空间;二是符合哈耶克社会政治理论的内在理路;三是完全符合哈耶克本人对这一书名的说明;最后也不含译者对哈耶克社会政治理论的任意限定。
五、对哈耶克“自生自发秩序”观念的讨论
问:在哈耶克的研究中,就像你所讲的那样,“自生自发关系”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念,而且还构成了他的社会理论的重要基础之一。但是,坦率地说,这个观念并没有得到人们很好地理解,因为人们一般都把哈耶克的这个观念与“自然形成”等而视之,甚至像汪晖这样严肃的学者也这样认为——他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哈耶克把社会领域视作是“自然的”或“个人主义的”领域,也即通过自然的交往行为而形成的自由的社会。既然你一再强调哈耶克“自生自发关系”观念的重要性,那么是否可以请你更加明确地澄清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