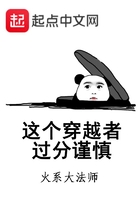1997.5.6 阴·晴
你说得不错,人各有路,各有不同的追寻或言梦想。几乎每个人都难免为他苦苦追寻的东西所累。或名利,或感情,此处是相等的。大多时候,也是对立的,所谓真正淡薄名利的,究竟能有几人?孟浩然可称是著名的田园诗人吧,而“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的谓叹正由他发出。不讳言者,我倒觉得诚实可爱。
人常言“最繁华时,也是最凄凉”。没有体会是想象不出那种孤独的。只是,没有最繁华,又如何会有最凄凉?绝对或者零,极富挑战性。“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
当年学《陈毅市长》时,我很深地记住了一句话“外面不发生政治变化,实验室如何进行化学变化”。他自是热情向上,满怀革命豪情。在我心中,却不由得转了一个角度,社会永远存在三六九等,不过时而模糊,时而清楚罢了。政治是操纵一切的翻云覆雨手。人生是无尽的挑战。即使到最后,也在为生命多一刻的呼吸而不懈奋斗。
今天收到信,一番感怀。
1997.6.6 阴·霾
现在,心情十分好。因为于不经意处,我见到了苦苦寻觅几年的《校园民谣》磁带,压抑住小鹿奔突一般的心跳,听着walkman中童稚甜蜜的歌曲,蹦跳地行在路上。偶尔驶过几辆车,几乎感觉不到“交通”或“喧嚣”的意味。归途上,我放慢了步子。歌页颤抖着握在手里,不晓得该如何描述它,不想说精致或美丽。看到它,油然而生的是狂喜和忧郁。听着这些歌,我的心、我的泪又变得透明。真的好难懂,刚才那么大的狂风,漫卷黄土。可是,你知道天是什么颜色吗?蓝的,很蓝,就像在拉卜楞寺曾陶醉的。而那白云,竟也似曾遇的凝若雪山,一切是那么明澈、干净、纯洁。西安——那刻我才第一次感到它的古老神秘。再多年的雨水也没能冲去它太厚的灰尘。可是,几番风沙,却“洗”出了它的动人容颜。
第二次,我觉得自己像个天使,就像两年前的一个下午,蓝天似乎与我亦步亦趋。身后,阴沉乌云,前方,乌云阴沉。美丽的,只是随着我的现在,我的身边,美丽似只为我存在。
快到家了,那线天中,又能纳入多少快乐和自由呢?
感动着、怀想着、惦念着、憧憬着、微笑着……轻易地、不觉地,一个下午已去。实在的事,却做了什么?
雨,总是不肯来。风,总要把云吹得四散。却,隐隐听到雷声……
1997.6.10
有个问题想问问你,因为似乎没有别人可以问。即使是你,我也不知如何能令它自然、随和些说出来。只是想问问,如果有一天,我想给自己一个了断,你会怎么看?若你得知,会不会想劝劝我?
人言,失败者才否定生命。我并不那么坚信。对比,不只是平衡,也往往是很深的悲哀。
其实,彼此明白,当说到时,往往不会做的。就像他讲给我听的,纵身一跳时,已什么都不想了。又记得他编的一个小相声,大概是说一个人不想活了,寻找各种方式结束,却没有勇气,始终搪塞各种借口……当时,大家笑得很开心。死亡——一个玩笑?
如此看世界时,有何能成恐惧?有何能成厌恶?有何能成绝望?
“最爱自己”成为理念时,人们却更加孤单了。
偶尔,我看自己,像秋风吹拂,晴阳微缀的青青林荫。压抑也好,释放也好,我不管。匆匆碌碌的世界,彼此能有一个小小的角落共泣同喜,能有一个相交的地方欢歌舞翩翩,能有一份遥远却绵延执著的心电感应,我就很满足很幸福了。
1997.6.18
当你微笑时,眼中黄色的纷纷落叶,也是翩飞、欢舞,笑声不绝的。
理解,其实并不难。难的,是许多事无法设身处地、无法身临其境。不能改变,只好听任。西方的文化核心是:人定胜天;东方却是:天人合一。理论上如此完美,思想上如此和平,可是行动呢,什么是真正的切实可行?
如今,因为现实而虚伪;未来,因为遥远而缥缈。没有一样是可知、可触、可感、可回味、可依恋的。
爸爸最主张我自立,却总在刻意地将他的人生经验作为我成熟的捷径。而往往未涉世时,会笑谈人生的虚空无常,却被一个小小的情感往事轻易湿润了眼睛。
现在的我,无论如何,也不会以为,寿比南山是幸福的。先知本该可以“avoid”(避免),可那些奇怪而难测的捉弄,使得很少有人能真正“escape”(逃脱)。
是否愿在身边留那么一个小小角落?那儿可休憩、可放纵;可微笑、可流泪;可欢喜、可悲泣……隐隐地,也会有感应。不为人知,只属于自己。而面对人群,只能也必会更坚强。浪漫似乎是奢侈的,现实一点比较安全。
1997.8.6小雨转中雨
非激烈,则冷漠,是我的性格。希望我能做到不卑不亢,真诚坦荡。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否算经历过?
单纯、天真、善良、温柔、善解人意——男人眼中的好女子应该是这样的,我觉得自己一样不沾。复杂、任性胡为、不可理喻、世故冷漠不时凸现。我虽不认为自己是个好女孩儿,倒也不觉得这样就是坏,是非、善恶、美丑原不是那样泾渭分明的。
如果有一天,有男人如M那般说,你是个完美的女孩儿——女孩该有的优点你都有,该有的缺点你也有。我想,那也是真正了解我、真正可称之为爱我的人。希望那时我能全心投入地爱对方。只要两情相悦,不要被感动。
自私、冷酷、残忍、贪婪,这是我对M现男友的评价。可没有办法,她爱的,正是此人种种世俗、世故与缺点。她完全想错了,我从不曾轻视、可怜她。我羡慕她,如她那样地羡慕我。我那么渴望全情投入,有所保留于我不是刻意的聪明,而是天性、宿命。这对我其实是一种折磨,我真的宁可遍体鳞伤。
报纸上那天读到一段话,“恋爱时是文学家,失恋时是哲学家,再恋爱是科学家”,M说我一直都是“科学家”。
1997.10.30
男人令女人感到不安全,是因为女人总想依赖男人;女人骂男人忘恩负义,是在计较付出与得到的比例。谁不迷恋青春美好呢?现在的世界,受伤男人为数也并不少。爱的悲剧性似乎是宿命的:两性间最原始的吸引,就是女人的美丽,男人的强悍。而婚姻更多意味着责任和道德。曾经太喜欢那句:“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是不是一个大骗子呢?从古骗至今,骗我们也骗他自己?爸爸会唱的歌不多,也往往只会两三句,最爱听他对妈妈唱:“美丽的姑娘千千万,只有你最可爱”。心中湿湿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