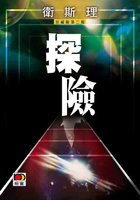走进森林,一丝凉意伴着陈腐的草木气息扑鼻而来,叫人道不出是香还是朽。这里象夜间,四处是蟋蟀的唧唧声。四处又的确是绿色的屏障,偶尔能看见从叶缝里筛下的太阳光柱。我没有忘记在拼命地走。扑,呼呼。一只野鸡拖着长长的花尾巴从离我不远的乱草蓬间慌慌飞走,抖落了几根花毛。我的娘我急忙拍了拍被这突如其来弄得差点要炸响的心,自我镇定。又迈开了脚步,结果一个念头涌上心来。听山里人说野鸡落窝的地方能寻到蛋,野鸡蛋营养丰富,蛋白多,街上买不着。如果,如果,我不想叙述一个家庭主妇,在这种景况下所产生的种种侥幸心理,仿佛看到一堆堆麻灰灰的鸡蛋,迫使我正为找不着偌大的布袋装走而犯难。于是,象有一股神气的力量在推我的身躯,我朝野鸡飞走的地方扑了过去,使劲分开一根根挡道的杂枝,极其认真地细致地寻找着,巴望眼前真的出现一堆堆热蛋。当我分开一蓬已近似枯竭的芦草时,一个模糊信息占有了我,果然那芦草中藏有一堆花斑斑的东西。还没等我兴奋的涌流从心脏扩展洒向周身,内心疾呼出终于出现了蛋时,我的眼睛已经又将另一个信息递进了大脑这个特殊机关,一条卷缩着的银环蛇,正用它那黑亮亮的眼与我对视,张着方形的口,伸出了箭舌,在吐。我发出一声连自己也弄不明白的疯喊,从布遍荆棘的山地,几步便跳到小路上,没命地向前跑去,直跑到一个山脊,才转过气来,瘫坐在一块路石头,心卡在喉眼上了,裤脚被撕破,脚肚被划开一道口,汩汩流出殷红的血,那蛇那景已经在我心中无法磨灭了,我只觉得四肢瘫软无力越想越恐怖起来。
我瑟瑟索索地站了起来,又继续向前攀登,路象条草绳,仍然向北缠绕,越走越窄小,林越来越深邃,不知走了多久,渐渐我出了这片森林,望得见那山头有一座石崖耸立,望得见头顶的蓝天丽日了。我有了几分欣慰,待我再望这被青草伏隐着的小路时,我发现它一直延长到那座高耸的石崖上,望不见尽头,一刹时,突然两眼发暗,对前路畏惧了。细看,前面的路满目石梯,顶天而去,一种不祥之兆从我潜在的意识中涌现出来,顿然感觉,我被那青年骗了,我坏过他那银色的梦啊,这被破灭过的梦里的路哪有尽头,世间的路哪有尽头?一股被愚弄的感觉从脚底升到脑顶,我确认被那小子活活报复了一回,终于,没有勇气继续走下去了。
等我再回到脚丫道,太阳已经从西山微笑了,这时一对情侣从西边道上谈笑着走来,他俩正饶有兴趣地谈论着麻姑仙洞。莫非他们今天去了仙洞,我鼓起勇气用尽最后一点力量向他们打听起来,原来他俩正打仙洞而来,只不过他俩是从西道进山的,远不过十几里路程,最难走的,是那百十级石梯,而那石梯顶上就是麻姑仙洞啊!
一阵懊悔的浪潮从心底涌来,事实证明,我从北绕道二十余里,在已经望得见仙洞的石梯路上,我败退了。
我回到了家里,丈夫摇着三轮车,走进我,两眼放着异常兴奋的光芒,他已经摇着车去大路上接过我三次了,见到他,我的双脚如同瘫痪一般,他期待着我给他带来美妙的故事啊。而为能给他讲述些什么呢?去讲我在快要领略到麻姑仙洞无限风光的时候退缩了么?
邙山遇“敌”
打我记事起,爸爸就杵着双拐走路。两根木棍,夹着一条半脚,一踮一迈地在地上挪动,谁都想象得出那该是何等痛苦,何等艰难,又是何等吃力。
爸爸为什么只有一条半腿呢?我背着花色书包上学了,心里常常这样思忖。有时候,悄悄问妈妈,妈妈总是垂下眼帘,摇头回答:你还小,说了你不懂。求我不要再追问爸爸的腿了。直到读小学三年级,一天老校长突然请我爸爸给同学们讲抗美援朝的战斗故事,我才知道,爸爸的那半只腿,是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国佬的重型炮弹炸掉的。回到家里,我哭了,我拽着妈妈的说,忿忿地说:我怎么不懂?爸爸的腿,是高鼻子,凸眼睛的美国佬炸的,是残酷无情的战争造成的。
从此,我幼小的心田里,深深埋下了一颗复仇的种子;决心长大去当兵,打到美国去,为爸爸报仇,为战殉的志愿军叔叔报仇。我等呀,等呀,等满了十八岁。我的愿望实现了,我穿上了绿军装,戴上了五星帽。为苦练杀敌本领,我画了一张又一张高鼻子,凸眼睛的美国佬,压在床铺下,放进挂包里。累了,渴了我就拿出来看一眼,看到它我就想起爸爸的腿,心里又充满敌意,连起来又忘记了疲倦,饥渴。三年过后,我练出了一拳嫩砸断五块砖的铁掌。一天能行走一百八十里路的飞毛腿。当上了侦查班长。我天天盼呀,我天天盼打仗,盼望打到美国华盛顿去。可是,我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美国不仅没有侵略,报纸上经常登出中美友好往来,中美互相协助的消息,好象再永远也不会发生战争,我永远也见不上高鼻子,凸眼睛的美国人。
做梦也不会梦到,初夏的这一天,我练攀登侦查,竟在中原风景区,群峦叠翠的邙山上,看见了美国人——一个落崖的美国人,他穿着一身黄色皮夹克,高鼻子、凸眼睛、黄头发,腰上吊着一只照相机,脸上正流着血。他在半崖的一棵古柏上晃悠着,挣扎着。这古柏离崖顶约有七米多高,底下却是百丈深渊。中国的一撮黄土,在外国人眼里都是珍珠。我马上猜想到,这位冒险家一定是看中了这崖中的古柏,为摄下这珍贵镜头不幸落身崖中的。果然,崖顶上有刚滑落的石头痕迹作证。好啊,狂妄的冒险家,要不是崖中古柏阻挡,你早就粉身碎骨。中国的山山水水,忘不了曾经遭受美国人的蹂躏。中国的每一块石头,历来都是打击侵略者的巨雷,这就是报应。我见到了这个美国人,高鼻子,凸眼睛就想起了爸爸的那半只腿,仿佛听见阴雨天爸爸的呻吟声,妈妈的愁叹声。这不就是我多年要寻找的敌人吗?想不到在这里相遇,我顿时热血涌流,怒气冲腾,身边正好又一大块多棱角的石头。
那位落崖的冒险家发现了我,鬼哭狼嚎地向我招手。我看清了他的面容,他很年轻,好象和我一般年龄。啊!忽然,我的心冷静了下来,犹豫起来。难道是他抛下炸弹炸坏我爸爸的腿吗?难道他就是当初战争的祸首吗?不!不会,在那硝烟滚滚的峥嵘岁月,我和他都还没来到人世间。那一定是他的爸爸炸的吧?啊,这有可能。那么,他的爸爸会不会也是一只半腿,或者只剩下半只腿呢?在电影镜头里美国佬从中国滚出去的标语前,我曾多次看到有无数头裹白纱,手杵竹杆,瘸瘸拐拐,龟爬鳌走,四处逃命的美国伤兵败将。我想那里面也许就有他的爷爷,他的爸爸。我不明白,那时候中美为什么不友好?为什么要象那样两败俱伤。这也许就是妈妈说我不懂的地方吧!我渐渐明白了,这是战争,爸爸的腿是残酷的战争造成的恶果,这罪过也不能全归于他的爸爸,他的爷爷,应归于残酷战争的制造者。
我终于熄灭了搬起石头复仇的念头。向那位正在绝望中挣扎的美国人,抛出了救命的绳索。他象猴一样精明,知道把绳索拴在身上,我一边用力向上拉;他一边扒着石缝往上爬。爬到大半腰,我已经大汗淋漓。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我扪心自问,我救的会不会是一条蛇?将来会不会恢复它的本性,再咬伤救过它的人?我国不是有农夫与蛇的传说吗?曾记否?我国不也有过农夫救蛇般的历史?只要我一丢手,他就会跌进百丈深渊。但是,人民渴望和平,人民需要安宁,我们正年轻,我们是世界的未来,我们要做安宁的维护人。当然,和平的同时,并不能麻痹,不能忘记过去,忘记战争的危险性一旦背信弃义,我们将用自己捕蛇的高超本领,捏住蛇的七寸(致命部位)。自卫还击战就是印证,让世人去公论。我忘不了我国素有舍己救人的传统美德,我终于没有丢手,忍受着内心的折磨,忍受着子不报父仇的疚痛,拼尽全力,将他救了上来。他感动得哭了,向我久久地鞠着躬。淌着热泪给我留下了一行中国字:我要把这件事告诉美国人,中美团结友好万岁。
啊!邙山,中原上瑰丽的山。邙山上我遇到了敌人。不,他不是敌人,他是致爸爸残废者的后代,是我的同龄人。不能把上辈的罪孽强加在他的头上,他是来中国游览的和平使者。但愿他真的把这个故事告诉美国人,告诉爸爸,妈妈,告诉美国青年朋友们;告诉我一个极普通、极普通的中国年轻战士,虚怀若谷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