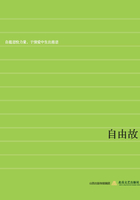等人们三三两两地聚拢了,天色已近黄昏,橘红色阳光在乔冬桂的眼镜片上晃来晃去。国字脸副主任站在一个石墩上,他首先纠正了小队长黄跃春关于开会的说法,他说其实并不是什么开会,而是根据他和乔主任所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并经他们研究之后,由他对一些问题作一个说明。他说:“为什么要作这个说明呢,因为最近有一些谣言,说某某某怎么样,跟谁又怎么样,可是你有证据吗?你抓到了人家什么?没有嘛是不是?这种事不是好玩的,没有根据就胡说八道是很不负责任的,是破坏人家的名誉。人家的男朋友是什么?是解放军战士!是保卫红色江山的钢铁长城!人家那是亲密战友,是很崇高的,崇高你们懂吗?咹?崇高就是不像你们似的,把那点骚事挂在嘴巴上。你说你没事七猜八猜干什么?有力气你不放到田里去,不抓生产,一天到晚记挂人家?你数数你肚子里有几粒油珠子吧!说得严重一点,你这是要毁我长城哪!是完全可以给你上纲上线的!当然啰,关于这一点,大家事前可能还不大了解,所以今天我特意在这里作一个说明。不过今后要注意了,不要再捕风捉影了!把一个影说成一个饼,还添油加醋,说是个芝麻葱油饼。说得的说不得的张口就说,到时候弄得自己吃不了兜着走。你兜得住还好,只怕你兜不住!你一双作田人的手,除了一手老茧,还有什么?你说你兜得住什么?”
国字脸副主任说话时,底下不时地响起笑声。副主任姓潘,叫潘瑞祥,家里住在金竹镇旁边的潘家堡,从小受父亲影响,喜欢读《三国演义》。性情温善,为人随和,听黄花萍说,如今他已经退休了,自家有几亩茶山,平常就在茶山上转悠,闲时还读读《三国演义》。
潘瑞祥这一番“说明”,既开脱了阎瘌痢,又给李玖妍的处女膜问题定了一个调子,这样一来,李玖妍的问题就简单多了,起码跟“破鞋”不沾边了,顶多也就是个“偷冷饭”的。当然,你都“偷”了,就不能太轻描淡写了,因此乔冬桂交代李玖妍,还是要有一个书面材料。要有认识,有态度,要斗私批修深挖思想根源。乔冬桂说,国字脸副主任也是这个意思,你就抓紧时间写吧。
国字脸副主任是吃了晚饭走的,陪他吃饭的有阎瘌痢和黄跃春,杨老八也来了,杨老八还把年轻的妇女主任也带来了,一顿饭吃得有说有笑,热热闹闹。知青办主任乔冬桂没走,她留下来准备开一个现场会,号召广大知青向徐小林学习,掀起一个科学种田的新高潮,同时也顺便抓一抓李玖妍的材料,把这件事情作一个了结。
那天黄花萍听了那个国字脸副主任对大家说的话,有点想不通,玖妍姐到底怎么回事呢?你们既然是亲密战友,为什么还要赖茅草蔸呢?李玖妍的情绪似乎比平常好一些,她说你一个小丫头,脑子里乱七八糟地想些什么?黄花萍说,我就是不懂你为什么要撒谎。李玖妍说跟你说不清。黄花萍说怎么说不清楚呢?你叫我撒谎,只点了那么几句话,我不就懂了?李玖妍说这是两码事,你一个小丫头,真不懂这些事的。
其实那时候黄花萍不是什么小丫头,她什么都懂了,她已经长大了,是个红润健壮的大姑娘了,并且已经定好了婆家,过了明年正月就要嫁到金竹镇去,给一个瘦瘦的很精干的年轻篾匠做老婆。所以李玖妍这么哄人黄花萍心里是不服的,不过黄花萍在跟我说这些时已经一点不计较了,她说也怪不得玖妍姐要哄我,她跟乔老师说的那些话确实挺难出口的,挺羞人的。我问黄花萍,李玖妍跟乔老师说了什么你怎么会知道呢?黄花萍唉一声,说,怎么不知道啊?又没过几天,不一句一句地都传出来了吗?
从这天开始,李玖妍晚上便不要值夜了,而是写材料。写了几次,乔冬桂都不满意,她说李玖妍,这件事你一定要认真对待,要详细,不要含糊,材料这种东西是不能有一点点含糊的。李玖妍只好再写。她趴在柴油灯下写材料时,会突然骂一声,龌龊!把黄花萍从梦中惊醒,问她骂谁龌龊?她说还有谁,乔冬桂!黄花萍眨巴着睡眼说,玖妍姐你怎么骂乔老师呢,乔老师怎么会龌龊呢?李玖妍说,你光看到她表面,不知道她心里有多龌龊,她心里装的全是些下三烂的东西!
李玖妍把时间、地点、人物、过程和细节都交代得详详细细清清楚楚,然后又挖了挖思想根源。思想根源好挖,在资产阶级那里的,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没那工夫,不像资产阶级那样腐朽堕落。但李玖妍却不忍心把自己往那里扯,她强调自己和詹少银只是不懂事,分别在即,一时头脑发热,没有控制住。乔冬桂对这份材料还是不大满意,说她写的不如她说的,她一写事情就变样了,怎么看怎么干巴,一点也不生动,完全没有了那种让人身临其境的感受。但她也提不出什么具体修改意见,说不细吗,已经够细了;说不清楚吗,究竟哪儿不清楚呢?只能说她文笔不好,勉强收下了。她用一个指头点点自己的脑子,语重心长地对李玖妍说:“还是要警惕啊。”
我曾经拼命想象,山野间遍布柴油灯会是一种什么情景?
夜色大概是脏污了,不干净了,谈不上风清露白了。夜色应该像一张被抹了油彩的脸,而且是一片混浊的、黄不黄紫不紫的油彩。蛾子见了灯火注定要变得很疯狂,它们弄不好会撞到值夜人的脸上去。值夜人肯定是头重脚轻的,就像一只没放稳的麻袋似的晃来晃去。蛾子撞过来了,李玖妍就打一个激灵,还没过半分钟,她又晃起来了。但阎瘌痢是肯定不晃的,他精神应该是好极了,他的眼睛一定是炯炯有神的。他其实也是一个残疾,—瘌痢瘌痢,一块光地;光地不光,杂毛黄黄。我们老鼠街的小孩很刻薄,看见瘌痢就这样唱。我们老鼠街还有一句俗话:十个瘌痢九个色。具体到阎瘌痢本人,他认不认为自己是个残疾呢?他一直想做李玖妍的工作,那么,他是怎么对李玖妍做工作的呢?他们在那样的夜晚,真的会什么也没做?东一盏灯西一盏灯,亮在那些坟堆似的土墩子上,天也静地也静,好像整个世界就剩下他们两个人。一男一女,或者再说得狠一点,孤男寡女。又因为静,便听见了许多东西在叫,比如青蛙在叫,虫子在叫。山也在叫。山上也有虫子,还有树蛙和岩蛙,还有飞禽走兽,还有草,有树。光是树叶发出的声音就宽阔无际,枫树叶、樟树叶、杉树叶、松树叶、茶树叶、桉树叶、栎树叶、榆树叶、柞树叶、槐树叶……几百种几千种树叶都在沙沙沙地叫着,几百种几千种大大小小的草也在叫着……阎瘌痢的身子里会不会也有什么在叫呢?不停地叫,拼命地叫,叫得他手足无措,他怎么办呢?起码,他会找一个草坡坐下来吧,然后拍拍旁边的草地,叫李玖妍也坐下来吧?草坡上的草一般都长得比较肥厚,草叶上已经开始牵上了露水,湿漉漉的,凉津津的,屁股坐上去很快就被湿透了。他会不会脱一件衣服给李玖妍垫一垫?他会不会说来吧,坐吧,我拿衣服给你垫好了?李玖妍坐下来之后,他会不会对李玖妍说,李玖妍同志,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你看看你这个情况,很不好办呢,你还想不想要我同意你说的那个什么茅草蔸呢?阎瘌痢是否真拿这件事跟我姐姐做过交易,—要我同意茅草蔸也行,但你也要同意我一件事,你就先让我做一回茅草蔸吧。假如他真这样不要脸,这样直通通地提出来,我姐姐会怎么办?她怎么权衡这件事?她应该很清楚自己的处境,照这样下去,她的名声只会越来越糟糕,不管她怎样努力,她都是没有希望的,前途一片黑暗,她就真要一辈子扎根在这个地方了。而这个人说,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我就帮你过这一关。过了这一关,就是柳暗花明了,天又是蓝的,太阳又升起来了,说不定从此就是一条康庄大道呢。她答不答应呢?这个人又进一步说,我是工作组组长,我说话是有用的,只要我帮你咬住它,那就是茅草蔸。茅草蔸算什么呢,它什么都不是,当柴烧都没人要它,嫌它带着土。这个主意好,真好啊。他也许还会像黄花萍那样,狠狠地夸她,说她聪明,主意想得很绝,把责任都推给一棵茅草蔸,自己什么事也没有,撇得一干二净。他这么夸她当然也是一种策略,也是为了说服她,让她的心思活泛起来,让她明白这实在是一件对人对己都有莫大好处的事情。
那么李玖妍明不明白这是一件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呢?柴油灯、蛾子、蛾子翅膀翻动时抖落下来的蛾粉(蛾粉像灰尘一样,很柔缓地弥漫着飘浮着,泛出细碎的雾一般的紫莹莹的光亮)、呛人的油烟子、被油烟子熏到山脚边边上的萤火虫(一点一点的,看上去似乎比芝麻粒还小)、山影、黑糊糊的天空和迷迷糊糊的星光、漫山遍野的似有似无的声音……还有被呛晕了的昏昏然坠地的蛾子(它们落下时的声音就像稀疏的雨点打在草尖上)、还有这个就坐在她身边的阎瘌痢、还有阎瘌痢的声音和气息—所有这一切都令人张皇和迷乱,晕晕乎乎浑浑噩噩,李玖妍会做出一个怎样的决定呢?从她对她的老师乔冬桂说的那些话,又老老实实地写交代材料来看,阎瘌痢好像并没有让她的心思活起来,一点也没有。她真是个死脑筋,油盐不进,属于那种遇事不会转弯的一根筋,不知道权衡利弊,不善于变通,为了让阎瘌痢无机可乘,或者为了撇清自己,再或者为了过眼前这一关,她居然断了自己的后路,放弃了“茅草蔸”,招出了詹少银。她为什么不肯跟阎瘌痢汤汤水水地搅到一起去呢,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我觉得她想错了,无论拿什么时代的眼光来看,她都是走了一步错棋。所谓棋错一着满盘皆输。要不然你就一根筋到底,死咬住“茅草蔸”也好呀。管你信不信,我就说是茅草蔸,见谁都说是茅草蔸,茅草蔸茅草蔸茅草蔸,咬碎了钢牙不松口,死活都由你。
兵法有云,置之死地而后生,可惜她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