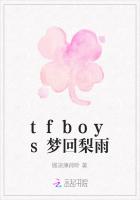这时,署长和戚朴民也来了,朱太太跟着他俩进了取暖房。署长一见钟心立笃悠悠的样子,不快地说:“钟探长,别空动脑筋了,如找不出凶手,就作为悬案吧,你先把证明写出来,交给朱太太!”
钟心立见署长来了,忙站起身,刚要答话,忽见从房梁上掉下一只蜘蛛,蜘蛛挂着一根丝,正好落在他面前,快要坠地时,那蜘蛛竟猛然一荡,又缘着那根细长丝飞一般地向上攀去,一眨眼,又回到了梁上。
钟心立望着蜘蛛,又低头看了一眼那张开的炉门,猛然省悟道:“我明白了……”戚朴民问道:“探长,你明白什么了?”
“朱先生是自杀的!”钟心立此言一出,满屋人都吃了一惊,朱太太顿时“嗷”的一声哭了起来:“老头子呀,你死得冤哪,被人杀死了,警察抓不到凶手,还说你是自杀的呀……”署长也不高兴地道:“钟探长,你说朱先生是自杀的,那他自杀用的那把枪呢,在哪儿?”
钟心立道:“如果我猜测得不错的话,那把自杀用的枪一定在取暖炉的排煤气管里!”说着,他拿起靠在一边的捅火铁条,伸进炉子的排气管,轻轻地捣着,一会儿,铁条似乎钩住了什么,钟心立慢慢往下拉,铁条尽头的弯钩上,果然钩着一把小巧的勃郎宁手枪,枪柄上还系着一根细细的橡皮筋。
看到手枪,朱太太忽然停止了嚎哭,脸色也变了。
原来,朱古力虽然家财万贯,但年近六旬,没有后嗣,原配夫人死后,他又娶了年轻貌美的太太。一年后,年轻太太竟为他生了个儿子。但儿子出生后不久,朱古力的企业却破产了,他只好携了太太和儿子回到老家石门县。朱太太原是看中了朱古力的百万家财才嫁给这个老头子的,如今老头子一破产,她哪里还过得惯这种清苦生活!后来,她得知朱古力曾在保险公司投保巨额人寿保险,如果朱古力一死,作为继承人的她就可以得到一笔保险金。于是,她几次威胁朱古力,说这日子没法过下去了,要带了儿子出走。朱古力老来得子,哪里舍得让她把儿子带走?而企业破产,他也确实心灰意冷,最后被逼无奈,便萌生了死的念头。因为自己一死,娇妻爱子就能得到那笔巨额保险赔偿金。但按照保险公司有关条例规定,如果投保人是自杀的,保险公司就不负责赔偿。于是他和朱太太几次谋划,挖空心思,终于想出一个“绝招”:留一个悬案给警察。他进取暖房后,先把门窗关紧上闩,再在取暖炉的排煤气管中装上一根橡皮筋,把橡皮筋的一头拉出炉子口,系在一把勃郎宁小手枪的把上,然后朱古力坐在藤椅上,用枪抵在自己的太阳穴上开了一枪,死的时候手一松,那根橡皮筋一缩,就把小手枪拉回到排气管里面去了。
真相大白,石门县城的居民纷纷指责朱太太心太毒。不久,朱太太卖掉朱家老宅,带了幼子出走,从此去向不明。
白鼠案
相传,清朝时候,在山东滕县、峄县和江苏铜山县搭界的那块地点,出了一桩没头案。现场是这样的:一个打草的小青年,两只手紧紧攥着打草的钐(割湖草用的大镰刀)杆跪在地上,他的头叫衫头砍掉,滚落在两步开外的草地上,尸身却跪在那里不倒。地保认出死的是他庄上李老汉的儿子,就赶紧跑回村告诉了李老汉,接着又到峄县县衙门报了案。峄县的县太爷觉得这地方属峄、滕、铜山三县交界的去处,就立即写下了文书,邀请铜山和滕县县太爷,请他们在同一天赶到出事地点,共同验尸。三位县太爷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带领仵作赶到现场,验看了一番,都认为死尸不倒,冤情一定很大,就联名分别呈报山东、江苏府台衙门。经府台指示,三县都在各自管辖的区域,仔细调查了解,一定要把这个凶杀案,弄个水落石出。他们查问了所有打湖草的农户,没问出丝毫线索;传问苦主李老汉,李老汉是个老实巴交的憨厚农民,只会出力干活,压根儿没跟别人打过架,闹过乱子,祖祖辈辈也没有为下过什么仇人。是谁杀害的呢?三县联合起来细查暗访了一个多月,也没搞出一丁点名堂,还是现场见到的一个钐头、一根钐杆、一具没头的死尸。这案子像个没把的葫芦,怎么能理出个头绪来呢?大伙都纳闷了。再说滕县县太爷的押印夫人,念过五经四书,还看过什么诸子百家的书,有一肚子好学问。人家都说她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大能人,出个谋,划个策,分析个事理,总是高出别人一头。听说她私下里帮县大老爷断过好多难断的案子哩。滕县县令为这码子事,吃不香,睡不甜,愁得难受。这天,他在内厅里正来回踱步,猛地想到了太太断案的才能,就找到夫人一五一十说了个仔细,要她帮着琢磨琢磨,拿出个好谋智来。其实,这位官太太对这个案子早有耳闻,眼下又听大老爷这么一叙说,心里更有数啦。当天,她让县大老爷带她到出事地点仔细观察了一番,无意间发现原来尸体跪着的地方,有个小洞口,这洞口有钐杆捅过的印。她想,小伙子为什么要捅这个小洞呢?这里边一定有文章。她暗自琢磨了好一阵子,才开口问县太爷:“老爷,您注意过这钐杆捅过的小洞吧?”“没有注意这个洞。”县令回答。“我觉着,这个小伙子是自己误杀,并不是他杀。”这位押印夫人像是很有把握,慢声细语地叙说着。“怎么见得?快说说看。”县令追问着。太太说:“莫急嘛,咱先从这个小洞往下挖,要是能发现个什么东西,就能证明我想得对头,那时再说给你听也不晚。”县太爷听了这番话,立时叫衙役们顺着洞口往下挖。果真等挖到二尺多深的时候,猛古丁地从洞里边窜出个小白鼠。可众人还是弄不明白,难道这只小白鼠能杀人吗?太太见大伙异样地慌,就说:“这个小伙子看见这只小白老鼠钻到洞里去,觉得怪稀罕,就跑过来跪在地上用钐杆使劲往下捅。兴许他用力过猛,震落了钐头,顺着钐杆正好滑落在小伙子的脖胫上,砍下头,丢了命。又因为他双手拄着钐杆,双膝跪在地上,有了这么个支撑,尸身才没有倒下。老爷,你说是也不是?”县太爷听了,打心眼里佩服。可这只是判断,有谁来证明他用钐杆捅这白鼠洞呢?太太见大老爷在疑虑这事,接下来说:“这湖涯荒滩,打湖草的不会只是一个人。我看,找那些常跟他一块打草的人问一问,兴许能证实这个小伙子被砍掉头的原委哩。”县令按照太太的意见,把平时和他一块打湖草的人全传了来,一个一个地询问,要他们不要害怕,不要顾虑,照实回话。要是不说,等查明白谁知情,可要从重处罚哩!经县太爷这么一开导,还真管事,在询问一个中年农民时,他说:“回大老爷,那天,我和他一块到这湖边荒滩上打草,太阳平西的时候,俺俩把打下的草堆好,就扛起钐回家。半路上,碰到一只小白鼠,从他脚下窜过去,他就在后边追。我累得要命,哪有闲工夫陪他去挖白鼠,就先回了家。当时我走出老远,回头见他正蹲在那里看什么。谁知第二天就听说他叫人杀害啦。倒底是谁杀害的,我可不知道啦。”“为什么早先不禀报这些事?”县令在追问。“这是人命关天的事,俺怕受牵连,谁还敢提这些?”中年农民照实回答。县令听了点点头。把传来的农民,全都打发回了家。滕县县太爷在夫人的协助下,终于弄清了这桩没头案的实情,认为可以结案了,便会同峄县、铜山县的县令,把案情的来龙去脉,呈报给山东、江苏府台衙门,奉批给了了这桩公案。滕县县令破了这个案,立了一大功。后经山东、江苏府台衙门议定,把峄县、铜山县靠滕县的地盘,共划出三个社,归属滕县管辖。这就是老百姓都知道的滕县的“南三社”。
潦草的遗书
有位老人十分喜欢小鸟,所以他在杂木林深处建了一幢别墅,并在别墅里挂了许多鸟笼,里面养着各种各样的鸟。
一天,他的一位多年未见的朋友前来拜访他时,发现他死在家中,便立即报告了警局。刑警来到现场,发现一张字迹潦草的遗书,说他是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而自杀身亡的。但是,当刑警环顾四周时发现,室内有很多鸟笼,笼内的小鸟还在欢快地啼叫着。他的朋友向刑警介绍说,死者三年前当了爱鸟协会会长。
听了这话,刑警果断地下了结论:“如果是那样的话,是他杀,遗书是伪造的。”警察是根据什么说出这番话的?原来,刑警看到小鸟还在笼子里便断定是他杀的,因为既然死者是爱鸟协会的会长,在自杀之前应该会将小鸟放飞,给它们自由。爱鸟家对小鸟的爱要超出常人一倍,而把它们关在笼子里自杀是不可思议的。血字诅咒星期五傍晚,正在进行重建工作的市博物馆冷冷清清。馆里的工作人员都提前下班了,只有老刘一人负责检票和看门。离下班还有半个小时,一个身穿黑风衣的年轻女孩要进馆参观,老刘提醒她就要关门了,女孩笑笑说:“没事,我一会儿就出来。”
到了闭馆时间,女孩仍然没有出来,老刘在门口叫了几声也没人回答,于是他走了进去。旧馆正在重建,这个临时馆区很小,呈圆形,站在入口处一眼就可以看遍整个馆区。馆区没有人,但有的展柜前感应灯是亮着的,说明不久前有人在那里呆过。馆区内没有窗,也没有别的出口,只有一条狭窄的横向走廊,左侧是紧紧关闭的表演厅,右侧通向二楼的铁门,二楼也有部分展品,但由于跟馆内办公室在一起,铁门在工作人员离开时已经锁上,女孩上不了二楼。
老刘有些奇怪,女孩哪里去了?在女孩进去后这段时间,他只上了一趟卫生间,难道女孩就是那时候出去的?他摇了摇头,关上大门。
周期六上午,进馆参观的游客多了起来,再加上正好有一个外国旅行团来参观,于是一楼的表演厅准时开始演奏古乐。正当游客们陶醉在美妙的音乐声中时,外面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坐在最外面的一对外国游客急忙跑出演奏厅,站在走廊上四处张望。临时馆区内没有人,感应灯却大亮。只见在一座玻璃罩内展出的古代木棺,棺盖突然被掀开,砸到了玻璃上,但令人恐怖的是,有一把剑,正慢慢没入棺内,最后猛然一顿,只露出一个剑柄,稳稳竖在那里。“我的天啊!”随后跑出来的一些游客看到这个情景,纷纷大叫起来。老刘听到声响,也马上赶了过来。
他走近木棺,隔着玻璃就能看到棺内的情形。一个身穿黑风衣的年轻女孩静静躺在棺内,胸口插着一把剑,鲜血正慢慢渗出。老刘惊骇地退后一步,却又看到掀开的棺盖内侧有一个奇怪的红色符号,仿佛是用女孩的鲜血写成,鲜血淋漓。老刘忍不住大叫起来:“死人了!快报警啊!”
接到报案,市刑侦队队长张津亲自赶往案发现场。由于大家惊吓过度,谁也没有想过要打开玻璃罩看看,所以现场保护得很完整。
玻璃门上的锁并没有被撬开的痕迹,钥匙只有老刘才有。虽然案发时,老刘最接近玻璃门,但在场的人都证明,老刘没有碰过玻璃门,那死者是怎么进入封闭的玻璃罩内呢?
“警官,这女孩我认识。”老刘嗫嚅着把昨天傍晚这女孩进入馆内却离奇失踪的事儿说了出来。
张津皱了皱眉,问:“你当时没有检查木棺吗?”老刘摇摇头,说:“棺盖平时都是盖着的,而且玻璃门又上了锁,女孩怎么会钻进去?真是怪事!”
张津没有答话,等调查人员在锁边取完指纹,他戴上手套,拿钥匙打开锁,钻了进去。
玻璃罩是特制的,很宽敞,除了那一具木棺,再站上四五个人都绰绰有余。张津趴在棺沿上往里看。死者表情平静,没有任何挣扎过的痕迹,她身上的黑风衣散开,露出里面的白色低领毛衣,剑就插在胸口处,鲜血溢出,但被毛衣吸收,并没有到处飞溅,还有一个小皮包放在脚下。
张津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凶器,然后把老刘叫进来询问:“这是把青铜剑吧?好像有些年代了,会不会是你们的馆藏?”老刘仔细看了看,不太确定地说:“大概是吧,我不太确定,不如让王馆员或是馆长来看看,他们都是考古方面的专家。”
那个王馆员走了进来,仔细看了看插在死者胸前的剑,断定道:“这是我们馆内的藏品,应该在二楼的第十八号位置上,是一把清朝的仿春秋青铜剑,剑身很长,没什么太大价值。”王馆员抬起头,正好看到棺盖上面那个用血写的奇怪符号,便好奇地凑过去,突然,他像想起了什么似的惊叫起来:“馆长,诅咒,这是汉王墓里的那个诅咒!”他似乎受了极大的惊吓,跌跌撞撞跑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