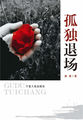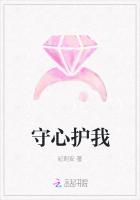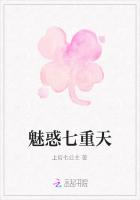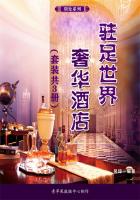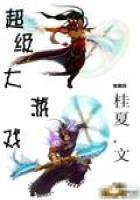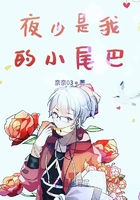王佐红
一直有一个印象:朱世忠先生的文学创作一直都在坚持,但一直不是很集中的“出炉”,很慢很执著。
直到拿到了杂文集《朝着空气射击》,才醒悟到翻过《秋天开花的梨树》时的感觉仍很靠近。于是生出敬佩,朱先生的行政工作很忙,这两年里竟然连续出了两本书,而在我的感觉里这两年是一个很快的过程,没有来得及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时间就过去了。
对先生的文章读得比较多,有其中原因:我在上中专的时候,先生是我们学校的大才子,副校长,口才和文才都是我们学生仰慕并喜欢的,我们自然比较关注,比较引以为豪。他的文章以散文杂文居多,幽默风趣、朴素亲切、睿智通达。往往取材很小,立意却很大,有能力把很小很小的一点素材能写到很大很重要的命题上,并且将其意味写完写尽,别人无法再出其外。先生以前的创作似乎很“乱”,就是什么文章都写,小说、散文、评论、杂文等,都有光彩闪现,但似乎“光束”不够集中。直到看到《朝着空气射击》,才发现先生已经在杂文散文方面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绩。
曾经认为先生的散文是最上乘的,现在发现,先生绝对是写杂文的一把高手。
我认为写文章最重要的是写两种东西,一是思想,二是写法。杂文写作首先面临的是思想认识,先生的杂文的思想一直都在敏锐、清晰、积极的状态上,不必细谈。他的杂文尤放光彩的是他的写法,很幽默、很风趣、但是很犀利,出手很“重”,让认真的读者读了之后很有些受不了。我有一个见解,即真正的读者往往是“怕”作家笔下故事中的“意外”的,这种“怕”又会是读者期盼的。朱先生的文章就有这种效果,讽刺一种现象,他往往从另外的小事情说开,风趣幽默不断,让你不自由地笑,在你不提防处提出“意外”的现实问题又不得不让你深入思考,有时候很痛心,这时候我们就为我们读文开始的笑意而惭愧,从而内心更加认识到现实问题的严峻,杂文的意义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全部实现了。
《3·15:我不敢上街》是非常典型的一篇,作者从戏说自己开始,“我”全身上下有许多假的地方,假得绝对让你读着想笑,可是“我”只怕3·15这一天,只要3·15这一天我不上街就什么事都没有,“我”很聪明,不会在3·15这天上街的。批评社会打假风气的虚伪和表面,最终让读者在发笑中感到了社会打假环境的悲哀。这是一种植入灵魂的悲哀,打假,我们往往只是做做样子,当我们在作家的幽默语言中藏着笑体验这份悲哀的时候,这种悲哀就更加悲哀了。
《轰动中国的民间收藏品》是一篇非常有意味的文章,作者采用了一种非常新的表现手法,以电视节目的呈现方式表现“夹带”这样一个曾经的作弊的工具,结果令人发笑,令人叫绝,实现对考试制度的绝佳抨击和批评。而他最初的入文却是一副一本正经的态度,电视节目《鉴宝》的形式很正式很完整,过程很紧凑,把读者的悬疑吊得高高的,在一步一步的推动中,你不由得发笑,但结局让我们笑得很后悔不已,文章揭示的批评的事实让我们无法不痛心,曾经作弊的工具“夹带”竟然价值连城,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教育特征。这就是杂文幽默风格的力量,比于表达方式一般的文章,它给读者心灵的撞击更重,对智识的开启更重要。
朱先生的杂文,总是先让读者发笑,然后再发自内心的后悔,这是杂文作家在思想境界成功之后艺术性上取得的成功。这一类的文章我认为是先生文章中最好最不可被复制的部分,《我冤枉我申诉》《芙蓉姐姐是有贡献的人》《“范跑跑”名副其实》等等都让人接受深深的警醒。
先生是一个很用心的作家,他写着杂文,关心着天下大事,追求着文学梦想,对文学有着准确的认识和体验,我很感同身受,以下是写在《朝着空气射击》勒口上的一句话:“写作是个人化和私密色彩相当明显的行为。我并不高尚,没有拯救别人灵魂的能力,没有用文字给世界增添光彩的天分,更没有荡涤污泥浊水,激浊扬清的境界。因此,写文章的出发点很简单,就是要把过去的不堪,拿出来让太阳暴晒,清理灵魂的垃圾,不让往事在心里荒芜发霉,不要被垃圾拖累。写杂文,是想把生活中有些见不得人的东西,让眼睛检阅。如果写作时守不住这个底线,我连回家卖红薯的资格都不具备。写作并不是宗教,并不像有些人标榜的那样,只有天天烧香叩头,才能悟得真谛,然后普度众生。”在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感觉我内心很长时间没有被激发出来的共鸣感响应了,作为一个比较认真的文学读者,找到最高的共鸣当然是最幸福的了,可是许多时间了,我都被一些假的空的哄骗人的所谓理论罩着,害得我心理的健康指数也不高,在读这段文字的时候,我终于有一种被别人疗救了一把的感觉,非常舒服。作家这样的坦白让读者感觉到作家是真诚的,是认真的,是远离虚伪和造作的。
杂文、甚至文学,于当下的时代,是一个边缘的状态,其实它本身就应该处在边缘的状态,只有在边缘的状态,它才会以自己的面目存在,当下有些作家把文学弄得很虚很假,很装很造作,并借以实现其丑陋的目的,把读者当傻子欺骗,那样,最后伤害的不光是文学,还有自己。
作家朱世忠的智识很是让我认同,杂文和文学观当然更是。他的杂文让人笑,更让人笑过之后痛而后悔,他在杂文中绝对不会让你轻松地“一笑而过”。因为这个品质,他的杂文,是好杂文。
(载于《银川晚报》2009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