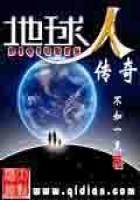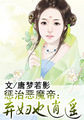荆竹
超群之才华刚刚得到全面展示的时候,死神硬是残酷地将他拖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他留给人们的只是惋惜、悲痛与辛酸。这对他来说,是多么的遗憾多么的不公平。记得,他刚离世之时,与他同在一个单位共事的我的儿子,在第一时间将噩耗告诉了我。我一时愣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又在第一时间告诉了宁夏作协常务副主席余光慧女士,以便安排有关事宜。
朱世忠走后,许多朋友都说:“他就是这个命。他虽然有才华,可命不好。好在他总能用读书写文章来排遣劳累,还有我们这些好朋友,他失去的灵魂还是能得到一些安慰的。”真是知友莫如友。对他之了解,我虽然不如其他朋友那么深细,但我却明白地知道这些年来他的忙碌,他的超负荷工作,他的辛勤创作……翻读朱世忠的这两本文存和以前的著述,会想他这些年所走过的路,他那些人生经历,他那出众之才华,他对社会之付出与所得到之回报,我似乎理解了朋友话的含义。
朱世忠在社会上和文学界皆是颇有影响的人物。他毕业于固原师专中文系,并取得宁夏大学本科学历,还获得香港公开大学教育领导与管理学科硕士学位。在他辞世的前几个月还曾对我说:“到现在,我一共在3个单位工作过,固原民族师范学校、共产党人杂志社、新闻出版局。固原这个地方虽然比银川小,甚至有点土,但是我对固原很有感情。固原有个最大特点,就是不仅出土特产而且出人才、出文学。”他的这番话,更加让我感到他可亲可敬。当时我暗自想,他在固原工作30多年,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对固原乃至宁夏的文学事业所作的奉献,所取得的成就与形成之影响,是无人能替代的。他虽然离开西海固多年,但对故乡仍然是一往情深。
我与朱世忠之交往,始于新世纪之初。那时,他还在固原工作,前来参加宁夏作协召开的第一辑“金骆驼丛书”作品研讨会,会期一天。在下午研讨会结束时,我作了研讨会总结。会散人走时,朱世忠突然来到我面前,“吹捧”了几句我的小结发言后并自我介绍。从此我们就有书信往返,他还向我索要过书。再后来,开会经常见面。我的印象是,他热情好客,侠骨衷肠,有一种特殊的生命情调。给我的感觉是,他在生活上没有什么事情似乎可以在意,所在意的就是文学。朱世忠的热情,在文学上表现得超乎寻常之突出。更为可贵的是,他这种热情是受着清醒的理性驱使的。有一次他对我说:“已经弄了这么多年文学了,在文学方面我还是没什么大出息,今后就写点杂七杂八的吧,也可以为别人的文章助威呐喊,敲敲边鼓。”朱世忠很谦虚,为人也很低调。其实他早已经出版过散文随笔集与杂文集,对文学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与见解。比如,他说牛撇捺的杂文是“心理流程和文字表述水平惊人的一致”,读他的杂文,“我们会在杂文家强烈的忧患意识冲击下,感悟杂文家的灵性和智慧”;说朱正安的散文随笔集《反哺集》,是将“衣食住行、草木山水、花鸟鱼虫、锅碗瓢盆汇聚笔端,挥洒成独到的思想感悟,在形式上是靠近传统散文的那一类文章,用质朴本色而又诚挚真切的语言,讲述了摇撼过情感与灵魂世界、珍藏在作者心底的人和事”;他说何强的小说《零度研究》,是“陌生化的小说叙述”,是“以极富个性的‘另类’叙事,挖掘异域资源,以重体验、敏感性、达性灵的独特写法,形成异质特色”;他评价高嵩的散文《“共荣圈”里》,“是表露个人独特感受和体验的佳作。我敢肯定,他对人性残忍、卑微、阴暗、高尚的揭示产生的震撼力,会使人永生难忘;我们叹服他的选材精当,思想之深刻”;他说贾长厚的散文《鱼趣》,“则要表现人类和赖以生存的生物间的隔阂和依偎,且想用人类的观照去解决生物界的纷争而不能达到目的的无奈”;对吴善珍的散文《宁夏的味道》,他则说是“入情入理地使宁夏发出迷人的气味,表现了她对第二故乡的挚爱”;说葛林的散文《银湖岸边那一头牛》,是“对没有生命的雕塑牛展开想象,写尽人间沧桑和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反差”;他还说“石舒清是只会写不想说的那一类厉害人。他已经站在小说的象牙塔上迎风远眺,能饱览山水之外的风景,倾听来自山上的声音……石舒清藏在海原的四合院里用刀子一样的笔书写清纯如水的生活”(见朱世忠散文随笔集《秋天开花的梨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等等。他的这些看法,堪称是有见地而又闪烁着灵性的文学评论。这是朱世忠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也是他的文艺思想和卓越才华的记录。
他写文学评论文章,一般在三个方面“助威呐喊”较多。一是为有潜力的文学新人呐喊,对那些在文学上有才华与艺术上有创新的作者总是投以特殊的热情。在这方面,他很有眼力,喊声也很高。比如《黄河文学》2002年第一期发表了何强的短篇小说《零度研究》,他就感到这是宁夏一位颇有潜力的青年作者,将来会有大发展,他立即就写了一篇《零度情感:陌生化的小说叙述》的文章,为其助威呐喊。二是为反映当下生活,闪烁思想火花的作品呐喊。三是为有创新突破的作品呐喊。他曾在《多元整合的审美态势》一文中说:新世纪伊始,宁夏的文学以立体作战、集团冲锋的趋向,引起文坛的广泛注意……银川是西夏古都,宁夏是文学富矿;贺兰山下,黄河两岸应当有游记、历史散文和文化散文驰骋的广阔空间。遗憾的是这方面的散文游记太少(见《秋天开花的梨树》一书)。可见,无论是对作家个体来说,还是就整个宁夏文学之格局来看,他皆渴望有创新与突破。每次作协开会,他总是与那些拔尖的青年作家们搞得热火朝天,同他们大都是谈文论艺,往往在走廊里就能听到他那仍带固原腔之高谈阔论,有时甚至是大声争论。
朱世忠还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我们常说,幽默首先是一种心态。不仅文学之生动有趣需要幽默,即使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同样也需要幽默。平时与朱世忠在一起相聚,人们总爱聆听他讲一些幽默笑话。他讲的笑话幽默,往往有起承转合,甚至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很像是篇微型小说,听完后让人笑得前仰后合。是啊,谁一辈子还不会说几句笑话、逗逗乐呢?在日常人际伦理中幽默是润滑剂。每当僵持、对立剑拔弩张时,一方突然来点幽默,哈哈一笑,干戈化为玉帛,气氛立即缓和。朱世忠之幽默即是如此,能调动人之情绪,能点燃人之心灵,能提升人之兴趣。这恐怕也是朱世忠生前朋友多之缘由。
最后,再说说《朱世忠文存》及其他作品。我在阅读朱世忠作品的时候,有一个十分突出的印象,就是他的作品大都体积很小,但容量很大。仅《文存》所收文章就达170多篇,庶几是由短简碎章而构成。我喜欢短简碎章式的小东西。这让我想起中外艺术史上许多现象。人在艺术上往往有偏见,有癖好,我的癖好就是小东西比大东西好。我在巴黎卢浮宫看到久仰的鲁本斯那些皇皇大作,就不甚喜欢,倒是他那些小画,特别是一些小草图,皆为率意之作,我反而特别喜欢,竟至舍不得移步。读文学作品也一样,如果以我的兴趣,我更偏爱小作品。以俄罗斯作家来说,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让我心向往之,但如果一定要让我选择出最喜欢的小说,我可能会选普希金的《拜尔金小说集》,集中的《暴风雪》《驿站长》诸篇,是几颗温润晶莹之珍珠,收在了所谓“西方文化”的潘多拉盒子里,那真是美极了。就说中国的东西,如果不是真山真水,只论画中林木丘壑,我偏爱宋人册页;至于唐诗,我酷爱绝句,读词则往往舍长调而只取小词。我想,朱世忠的作品之所以我认为很好,盖除文内有巨大之信息量与思想内容外,可能与自己这种倾心小东西的偏爱有关系。我在展读《文存》时,不时就有一种温暖之感动在心里油然而生;文气贯通,言简情痴;一读之下,不但被深深地吸引,而且有一种特殊之感觉,觉得这些文字非常熟识,那就是我的老朋友朱世忠——在这些清晰明亮之文字里,我又见到了他的身影,还有他那温和之微笑,虽然模模糊糊,可是绝不会认错。《文存》之阅读让我非常高兴,因为在今天的文学写作里,文学的小品传统仍然还活着,不仅活着,而且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文学园地,一派生机。
(载于《宁夏文艺家》2011年2月5日,《黄河文学》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