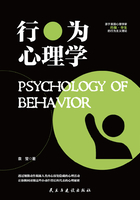“既然如此,”福尔摩斯说道,“我建议保持作案现场,把这个房门封起来。我们与这位夫人一块到她住的屋子里去。等到了那里,我们说清楚一切以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计划。”
三十分钟以后,我们四个人已在卢卡夫人的小房间中坐了下来,听她叙说那些离奇的事情。事情的结局,我们在偶然中已亲眼所见了。她的英语不是十分标准,但是说得非常快且流利。为了更加明白一些,我只有作必要的语法修改。
“我出生在坡西利坡,也就是那不勒斯附近,”她说,“首席法官奥古斯托·巴雷里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曾是当地的议员。根纳罗是我父亲的手下。我喜欢他。其他的女人也同样喜欢他。他既无金钱也无权势,他几乎一无所有,仅有漂亮的面孔,大的力气和年轻的活力——因此我爸爸不同意我们的婚事。我和他一同逃跑,在巴里结婚。将首饰都变卖,我们能到达美国就是这笔钱的作用。这已是四年前的事,在那之后,我们没有离开过纽约。
“起初,我们挺走运的,一位意大利男士被根纳罗帮助过——那位男士在一个名叫鲍厄里的地方遭到暴徒的袭击,他救了他,从此他就与这个有势力的人成了朋友。这位先生名叫梯托·卡斯塔洛蒂。卡斯塔洛蒂——赞姆巴大公司的主要创办人就是他。纽约的主要水果进口商就是这家公司。当时,赞姆巴先生生了病,我们新结交的朋友卡斯塔洛蒂掌握了公司的大权。有三百多人在这家公司工作。他让我的丈夫在他的公司里上班,并且把一个门市部交给我丈夫,在各个方面他都非常照顾我丈夫。卡斯塔洛蒂先生没有太太,我敢说,他把根纳罗当作了他的儿子,我和我的丈夫都非常尊敬他,几乎也把他当作了我们的爸爸。我们买了一所小住宅,在布鲁克林,我们的命运似乎不会再有什么风雨。可就在这时,乌云一下子出现在我们的上空,并瞬间将我们的天空布满。
“在一天夜间,下班归来的根纳罗,领回一个名叫乔吉阿诺的同乡,他也居住在坡西利坡下。此人身材魁梧,你们已经见过,他的尸体刚才就在你们眼前。他不仅身体大得出奇,而且一切都非常奇怪,让人感到恐怖。他说话的声音像雷鸣一般在我们的小房子中回荡。说话时,他摆动庞大的手臂,在我家的房子中都无法伸展。他一切都是热烈且古怪的——思想,情绪等等。他说话时,非常有力,就像在嚎叫,别人也只能呆呆地听他不停歇地演说。他的双眼始终盯着你,他完全将你控制住了。他是一个恐怖的怪人。谢天谢地,他已经命丧九泉啦!
“他经常到我家来。但是我明白,根纳罗同样讨厌他。我丈夫呆呆地坐在那里,样子十分无奈,脸上没有一点颜色,听我们的客人说话时,没有一点精神。他说的全是胡言乱语,什么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没完没了地演说。根纳罗没有说一句话,我呢,是非常明白他的。我从他脸上看出了一种以前从未见过的表情。开始时,我想是厌恶。一段时间之后,我渐渐清楚,不光是厌恶,还有恐惧,一种深沉的、隐藏的、胆怯的恐惧。那天夜里,也就是我发现他害怕的那天夜里,我搂着他,恳求他看在我们相爱的情份上对我叙说一切,为何这个大块头把他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他终于对我说了。我刚听完,心便像冰一样凉。我可怜的丈夫啊,在那倒霉的日子中,全世界都与他作对,他差不多被这不公平的生活给逼疯了。就在那段时间中,他加入了那不勒斯一个名叫红圈会的团体。是老烧炭党的同盟。这个团体有着非常恐怖的誓约和机密,只要加入其中就别想再退出。我们躲到美国时,我丈夫还想着与他们再不会有牵连。有一天夜间,他在大街上遇见了一个人——就是在那不勒斯介绍他加盟那个团体的大个子——乔吉阿诺。在意大利南部,别人都称他为‘死亡’,因为他杀的人不可计数,真算得上是一个刽子手!他为了逃避意大利的警方,才来到纽约。在他新的住所,他成立了这个可怕组织的分部。这些事都是根纳罗告诉我的,而且将他在那日得到的一张纸条给我看。纸条上也被一个红圈圈着。纸条上说要他在某日集合,他必须前去。
“真是太倒霉了。可是后边还有更倒霉的。我曾观察了一段时间,乔吉阿诺经常在夜间到我们家来,而且总是与我谈话。虽然他有时也和我丈夫谈话,但他两只野兽一样恐怖的双眼却总是注视着我。在一天夜间,我明白了一切。他所谓的‘爱情’——野兽和病人的爱情——我已非常清楚。他来我家时,根纳罗还未回来。他闯进房子里,我被他那双熊掌似的手紧紧地搂住,他将我拥在他熊一样的怀中,在我的脸上疯狂地吻着,甚至请求我与他一起走。当我拼命地挣扎呼救的时候,我丈夫回来了,朝他扑过去。他把我丈夫打昏,夺门而出,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来过我们家。也就是从那天晚上起,我们成了死对头。
“几天之后,我丈夫开会归来,从他的神情,我便可以明白有可怕的事要发生。但这一切比我们想象的更可怕。红圈会是靠敲诈有钱的意大利人来维持生活,假如别人不给钱,他们就用武力相逼。看情形,灾难已降临到我们的好朋友和恩人——卡斯塔洛蒂身上了。他拒绝一切淫威,而且报了警。红圈会打算杀鸡吓猴——用我们的朋友做标本,以消灭其他反抗者的这种心理。会中商定,将我们的朋友的屋子及他本人一块用炸药摧毁。由谁去做,将抽签决定。当我丈夫将手伸入袋中抽签时,他发现了我们的敌人那幅冷酷的面孔正朝他冷笑。毫无疑问,他们早就计划好了一切,那个杀人的标志就是签上那个让人望而生畏的红色圆圈,明显被我丈夫抽到。他只有两条路:一是杀死自己的恩人,二是我和他将遭到他们那帮人的毒害。只要是对他们不利的人,他们憎恨的人,他们决不轻易放过,不仅要报复这些人自己,另外还将报复这些人的朋友。这就是他们魔鬼一样的规矩中的一部分。这种恐惧降临到了我可怜的丈夫身上,压得他焦虑万分,差不多就要神经失常。
“我们每个晚上都依偎在一块,一起防备着随时可能到来的灾难。行动的日子定在第二天的夜间。中午左右,我和我丈夫到达了伦敦,但是没有时间通知我们的朋友他有灾难;也未向警察报告这一切,为了使他将来的生命没有危险。
“先生们,其他的一切,你们都清楚。我们明白,我们的仇人像影子一样紧随在我们周围,乔吉阿诺对我们的报复,纯属他的个人原因,但是无论如何,他是怎样的残忍、奸险、固执,我们都清楚。他那恐怖的势力在意大利和美国到处流传。我藏身的地方,是我亲爱的丈夫在我们离开之后仅有的几天内安排好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可以保证我绝对安全。关于他自己,也想早点远离他们,也好与美国和意大利的警方取得联系。我本人也不清楚他住在什么地方,如何生活。我只能从报纸中的寻人广告栏里得到他的消息。有一回我向窗子外边看去,发现这所屋子被两个意大利人监视着。我明白,我们最终被乔吉阿诺找到了。后来,我丈夫通过报纸告诉我,他将从一扇窗口中给我发信号。但是发出的信号,唯有警告,没有其他什么,而且又忽然中断。现在我知道,他发现他被乔吉阿诺盯住了。谢天谢地!当这个可恶的人出现时,他早准备好了。先生们,我现在想请教你们,从法律观点上讲,我们有必要害怕什么吗?我丈夫的所作所为,这个世界上的哪个法官可以判他的罪吗?”
“哦,葛莱森先生,”那位美国人边扫视着警官边说道,“我不清楚你们英国有什么样的看法,可是我认为,在纽约,所有的人们都会感激这位夫人的丈夫!”
“我把她带去见局长,”葛莱森先生说,“假如她所讲的都是真实情况,我想她和她的丈夫都是没有任何罪可言的。可是,我不明白,福尔摩斯你为何也牵扯到这桩案子中来了呢?”
“教育,葛莱森先生,教育,我还打算从这所老大学中学点知识。得啦,华生,你的记录本中又多了一份凄惨且奇怪的资料。对啦,还未到八点钟吧,今天晚上瓦格纳的歌剧在考汶花园上演呢!如果我们立刻就去,或许可以看上第二幕。”
3布鲁斯-帕廷顿计划
这日,伦敦到处烟雾缭绕,久久不能散去。
从礼拜一到以后的好几日之中,我确实怀疑我是否可以从我们的窗口看到外边的景物,是否可以看清不远处屋子的形状。
第一天,我的朋友在给他那本非常厚的参考书编索引。
第二天和第三天,福尔摩斯一直在听中世纪的音乐。
可直到第四天,雾仍是那样浓,丝毫没有散去的迹像。我的伙伴那样好的忍耐性也受不了啦,这样枯燥的日子,太没意思。
所以福尔摩斯开始在我们的房间中来回走动着,并且不断找事做,磨磨牙齿,摸一摸我们的家具什么的,对于这样没有丝毫活力的日子他非常生气。
“华生,报纸上有什么好新闻吗?”
我非常清楚,他所说的报纸上的好新闻,是那些关于罪犯的离奇故事的揭晓。报上登的有关政府方面的新闻、经济方面的新闻、政治方面的新闻等等非常多,可是我的朋友对于这些统统都不感兴趣。
他抓起报纸再次浏览了一遍,都是一些乏味的东西,所以放下报纸仍然走过去走过来。
“伦敦的罪犯全是一群蠢猪。”他边走边牢骚着,就像一个找不到对手的挑战者,“华生,你瞧外边那些稠密的烟雾,人都在朦朦胧胧之中,隐隐约约。这为作案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对吧?”
“处在这样好的天气中,凶手和小偷可以大摇大摆地穿梭在人群中间,并且作案以后别人还不容易发现,浓雾成了保护他们的帷幕。好像野兽藏在丛林之中,谁也没发现它,可是它可以随时扑向它的猎物。”
“但是,如此一来,唯有受害人本身可以看得非常明白。”他说。
“不是还有许多扒手吗?”我说。
福尔摩斯从鼻孔中轻轻地哼了一声。
“这个烟雾缭绕的天气并非专为那些小偷小摸的事而有的。”他说,“幸好我不是社会中的罪犯,这确实是万幸。”
“确实如此,非常好!幸好你不是!”
“假如我是布鲁斯或者伍奇德,或者是那些有十足把握可以杀死我的五十名凶手之一,若是那样,由我本人去侦破它。我可以活多长时间?”
“仅需用一张传票,一回假的约会,就能搞定吗?”
“幸好那些经常发生暗杀的国家没有这种天气,不然——哈哈,总算到了!我们终于能不再无聊!”
佣人递过来一份电报。
我的伙伴看了那份电报,仰着脑袋哈哈大笑着。
“太妙啦,太妙啦,我的哥哥迈克罗夫特马上就到!”
“得啦,这有何大惊小怪的?”
“这里有非常值得惊奇的缘由,比如说吧,犹如在一条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上,迎面驶来一辆公共马车。迈克罗夫特有属于他的生活圈子,他必须在那些圈子中穿梭。
“他的生活范围差不多是三点一线式的,倍尔美街的住所,欧尼根俱乐部,白厅,一共也就这几个地方。我这里他仅来过一次,并且仅一次。这一回绝对是发生了重大的事情,不然他不可能到我这里来!”
“他没告诉你是因为何事吗?”
他将电报递给我:
因卡多甘·伟斯特之事见你。即到。
迈克罗夫特
即日
“卡多甘·伟斯特,这个名字我听说过。”
“我不怎么记得这个名字。但是我感到奇怪的是,迈克罗夫特亲自前来找我。由此可见,公共马车也可能开到弯曲的乡间小道上,是吗?你清楚他是做什么的吗?”
“我仅模糊地记得一点点。”
“好像是在英国政府中干什么?”
福尔摩斯听完,大声地笑了。
“那个时候,我们结识不久,还不怎么了解。关于那些国家的事情,说起时,都非常小心谨慎。”
“你说他在英国政府中工作,这没有错。假如从某种意义上看,说他就是英国政府,那也没错。”
“这究竟是怎么搞的?”
“我早就知道你会非常吃惊。我哥哥迈克罗夫特一年的收入只有四百五十英镑,仅算一个小职员,他不曾有任何坏的企图和任何野心,他视功名利禄如粪土,可是我们英国少了他就不行!”
“我越听越不明白。”
“你耐心地听我说,他有非常独特的地位,而且是用他的聪明才智换来这样的地位,不曾有任何的投机取巧可言。这样的事情没有前人引路,也没有后人来继承,惟有他自己。他的思维独特,思路明朗,并且记忆力超人,过目不忘。他的能力超过所有的人。我和他的才华一样。只是我们所走的路不一样,我的才能用来侦察案子,他的才能则用作某种特殊的事情,我们英国政府各个部门的大小事情都必须经过他的手才行,他是一个聚集站,一个大容器。从他那儿可以找到任何信息,而且给以平衡。假如别人都是专家、权威,他的特长是各方面都懂。假如有一位总管要得到印度、美国、海军和钱物等方面的问题,除了他没有一个人能详细知道,仔细地说与你听,另外还会告诉你这其中哪些因素有影响。因此,他成为了一位不可缺少的人物。起初,他的同事仅仅是为了方便和快捷才去求助于他。到后来,便渐渐地发现,在他的脑袋中,无论什么样的事情都包括。当需要的时候能随时取出来使用。因此,那一个又一个的难题都是由他发表的那些见解决定的。他就在那中间生活着,平时,他从不出门,只有当我由于一两件小事情去求他,他才会适当地放松几分钟。今天,为何不请自来呢?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卡多甘·伟斯特到底是什么人物?他们有何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