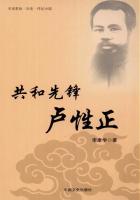正议论着,王道士提来了一桶热气腾腾的面片儿汤,又端来一碗黑糊糊的什么咸菜。他说今日还就是忘了准备吃的东西。山上条件甚差,万岁凑合着吃点儿不知可否?
此话一说,大家倍增凄惶酸楚。建文帝端过那碗面片儿汤时,他倒未觉出有什么,可周围的大臣们都已泣不成声了。天啊!皇宫近在咫尺,却成了天涯沦落人了!
吃过了夜膳,大家继续议论。遂决定左右不离建文者三人:叶希贤、杨应能都已剃发,自然是“比丘”,程济算是打杂儿的“道人”。又确定往来道路上时常提供衣食的六人,都起了绰号:“衣葛翁”、“雪巷”、“槎主”、“南山樵夫”、“太湖渔翁”和“补锅匠”。
在确定建文帝旅程目的地时候,有人建议远赴云南,依西平侯沐晟。史彬却说,西平侯能靠得住否,怕不好说。又有人提了几个去处;可仔细斟酌,亦觉不敢保险。议来议去,眼看夜半,还是徐王府纪善史彬说:“此地不可久留。我看,不如先去我家暂避数日,再作计较。”
史彬的家是苏州府吴江县黄溪,濒临太湖和南运河,交通比较方便,且史家家赀也厚,足够饮食。而其他人的家乡,最近的也是襄阳,三天两日也到达不了。所以众人也都提不出反对意见。
说声要走,渡船就是最急的。当即就有几个人下山筹备。按说玄武湖上该是有船的,因那年头儿此湖封闭,户部在湖心岛上造“黄册”(即赋役登记册),闲人莫入,官吏们上下班交通工具不是马和车轿,而是舟楫。只不知现今乱哄哄的,还有船未有。到湖边一看,还真是巧!真有一只舴艋舟在那儿荡悠,想是因了风势从南边飘游过来的。
这几位大臣赶紧将船拢到岸边,又急火火到观里禀报建文。建文大喜。却又愁无有舟子。史彬说我会驶船,只是多年未弄了。王钺说我也凑合。众人说,好好好,撑船的便是你二位了。
这工夫儿天就要微明了。因怕道士们回来,弄不好横生事端,所以必须马上离开。于是大家相拥相抱,哭作一团。最后不知谁说了句:“天下无有不散的筵席”,又有人更正说是“后会有期”,就在玄武湖畔洒泪分手。
建文(现在是应文和尚)、叶希贤(应贤)、杨应能(应能)、史彬(太湖渔翁)、王钺(补锅匠)便上了船。在许多双泪眼的注视下,这“载不动许多愁”的舴艋舟,便贴着玄武湖的东北岸,寻找长江去了……
现在,在黄溪的这所谓“清远轩”里,几个人已吃罢饭,餐具懒得收拾,先听“太湖渔翁”史彬讲他所搜集到的来自京师的消息。
建文早已得知马皇后自缢而薨,且被“补锅匠”王钺抱到了乾清宫火堆里。他也知道,马皇后以他的名义享受了“天子葬礼”,被埋在了钟山上。为此他将他的马皇后,与太祖的马皇后还暗暗作过对比,觉得这两代马皇后的命运真是有天壤之别!不过这都无所谓了。死了的无须再让他惦记了。他现在惦记着的是活人,比如他的母亲吕太后(现在降为懿文太子妃)。由他的小弟徐王(已降为敷惠王)陪伴着,迁往懿文太子陵园。
他的另外两个弟弟,吴王被降封为广泽王,远徙濠州;衡王降为怀恩王,迁往建昌。他的少子即二岁的文圭据说没逃出宫去,连同其乳母被燕军一起抓住,如今被押回凤阳去了。至于太子文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究竟去了哪里呢?……
太湖渔翁即史彬说,他家私学的教习王先生刚从应天回来。王教习得到的消息是,广泽王和怀恩王尚未到达濠州和建昌,就又被废为庶人,一起禁锢在凤阳了。刚说到这里,建文就连连点头叹气说:“唉,我料定会如此的,料定会如此的。还有别的消息没有?”
史彬说:“都御使景大人又被杀了……”
建文一愣:“景清?他不是降了新朝了吗?”
“唉!那是假降。景清是要为陛……为师父您报仇。他是想杀了燕逆,以图匡复建文朝廷的呢!”
于是史彬便复述了景清刺杀永乐且被“剥皮实草”,悬挂于长安门上的经过。引得建文以及叶希贤、程济等好一阵嗟叹。不过他们都未流泪——他们听到此类血淋淋捐躯的故事太多太多了!
来到黄溪之后,每听到这类的故事(比如暴昭被寸磔),他们便会由某人写一篇诗文,然后由“渔夫”和“补锅匠”撑了船,他们到太湖里哭一场,然后将诗文撕碎,葬人湖中。他们只能以此来寄托哀思。但是这样搞的多了,也容易引起乡人怀疑。所以再后来,写了诗文便就地火化,埋进地里。这样也就无法放声大哭了,只能使悲痛化作石头沉甸甸压在心里了。
然而史彬后来讲述的故事使他们得到了一点快慰。史彬说,景清的“人皮草人儿”挂在了长安门之后,说也怪,每到夜晚之间通体发亮。人们称其为“忠臣精英之光”也。有一天,永乐帝车驾经过长安门,忽起一阵飓风,刮断系了景清的绳索,景清的“人皮草人儿”恰恰掉落到永乐的车辇前头。恰恰又是立着,扑向辇门做张牙舞爪状。结果吓得永乐夜夜做恶梦,梦见景清仗剑追杀这个篡位贼王!……
“好!”众人听罢,情不自禁拊掌欢呼。而且,应贤和尚和“补锅匠”,很顺理成章地便联想到,永乐没准儿会被吓出病来,没准儿活不过今年去呢!
然而,这种少有的愉悦未能持续两刻钟。接下去史彬通报的情况,又使他们陷入了惶恐之渊里。
史彬说,溥洽被逮捕了。下了诏狱。
“溥洽?……”程济惊叫一声——他是极少惊惶过的,可这会儿面如土色。应贤、应能和“补锅匠”随之也惶惶不安地站起来,在这不大的茅屋里踱着步。只有史彬和建文好像尚未觉出事态有多么严重。他两个瞅瞅程济,又瞅瞅叶希贤和王钺,极困惑地问:“怎么了?究竟怎么了?”为何锦衣卫逮捕暴昭,逮捕铁铉等人,程济都没有这么惊惶过呢!……
程济怔了片刻,然后招招手,让大家都凑近些,围拢到建文身边来。他压低声对建文说:“显而易见,溥洽下狱,证明永乐对陛下之死起了疑心。臣可以断定,自此而后,朝廷必会在各地严加搜捕!……”“溥洽与我有何关系呢?”建文困惑不解。
叶希贤倒是能理解程济的意思,可他提出这么一个问题:“难道永乐会在各地张贴榜文,画影图形捉拿陛下?这不可能的吧!程大人是否有点过虑了呢?”
“不不不”,程济说,“永乐绝不会如此愚笨。永乐即便知道陛下尚活在世上,他也不会承认的。他只承认乾清宫的焦尸。惟其如此,他的皇位才能坐下去。”
“唔!……”叶希贤若有所悟,“那便是说,永乐捉拿陛下,不是明的,却是暗的?”
“唉!这就是朱棣!”程济极佩服似地点着头,喊出了永乐的名讳。随后又对建文说:
“陛下,恕臣说句无礼的话——永乐这个人,他就是把陛下杀了,他也不会承认杀的是陛下您呀!……”
建文只觉得一股凉气从胸腔升起,缠绕在了脖颈上。他下意识地摸摸脖颈。他瘫坐在了木椅上。
程济慢慢踱到窗下,倾听着外面的萧萧竹声。间或有狗吠幽幽传来。甚至还有荒鸡莫名其妙地咯哒哒蹄了一阵。少顷,程济说:“陛下,‘梁园’虽好,非久居之所。
此地离京师甚近,人多而眼杂,而我等又不能老呆在这‘清远轩’里。依臣之见,还是远走高飞,萍踪江湖,东西南北,皆吾家也!”
建文说:“卿言甚是。那就走吧。可先去哪里呢?”
程济闷了半晌,说道:“陛下,先去云南如何?”
“好……吧!”建文沉吟道,“去云南,该是经过襄阳的吧?我记得廖平的家是在襄阳,且到他家里住一住。”
第二天,建文帝就离开了太湖之滨。行前应史彬之请,建文将他“驻跸”过的“清远轩”改题为“水月庵”。
史彬没有随同建文继续漫游。他也未再出仕。这年深秋,树叶儿要落光的时候,永乐帝令将建文时在任诸臣自行离职者四百六十三人全部削籍,礼部行文各州县,追缴革除诰敕,苏州府遣吴江县丞巩德来到史彬家追讨诰敕,见自号“太湖渔翁”的史彬,戴了竹笠、披了蓑衣,正垂钓于竹溪。巩县丞将嘴巴俯在渔翁的耳朵上说:
“听说建文皇帝在先生家里?”
渔翁微微一哂道:“哪儿的话呀!你看,你这话把快上钩的鱼给吓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