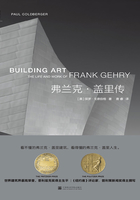朱能迷迷糊糊觉得身上受到了重压。他以军人的警觉,马上翻身而起。一刹间这才知道压他的是个女人。这女人又爬上来,用肥肥的奶子使劲在他胸上摩擦,且将甜腻腻的嘴巴猛吻他的唇,而两只手也在他身上乱抓乱挠……朱能明白了:这定是脱儿火察的女儿蒲察。这工夫儿他浑身燥热,腹下尤其难受;但听听两边就有雷似的鼾声,只好将双腿努力地夹住。心里话:蒲察也忒大胆,忒狂放!如何守着自己的父亲,就能跟个陌生人来这种事儿呢!他惶惶地悄声对蒲察说“不行不行”!而蒲察却说“就行就行”!当然,只要朱能铁了心肠,蒲察也是无可奈何的。最后,她只能狠狠地在朱能肩膀上咬了一口,又在他屁股上拧了一把,再一跳一跳地越过了张玉、火真和她父亲的身躯。白白的身子闪了两闪,溶人了月色……
翌日清晨,脱儿火察向三位客人各献一碗凉奶。张玉一饮而尽。火真一饮而尽。朱能端起奶碗时,脱儿火察却是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盯他。待他也一饮而尽后,脱儿火察赞叹:“好,大丈夫也!”——后来,据火真介绍,脱儿火察的奶碗里没准儿掺了什么玩意儿。如果夜间他们睡了女人的话,这碗凉奶便极可能使人阳痿,甚或断肠而亡。不过这也是猜测,未必真会有那么严重。不过这倒真使朱能吓一大跳,确有点儿后怕呢!
早饭过后,大家的头脑都清醒着,主客的会谈正式开始。脱儿火察的智商其实不低,脑瓜亦不笨,他就料定张玉等三人有要事上门。他说:
“你们汉人常说‘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兀良哈人没什么窗子,毡房外面便是朗朗青天。三位朋友有什么话,尽管说吧!”
“好,有大哥这话就好办了!”于是张玉道明来意。他希望脱儿火察能“良禽择木而栖”,带领朵颜三卫归属于燕王麾下。随燕王杀到应天去,夺取天下。等燕王当了皇帝,决不会亏待朵颜人的。
脱儿火察嘿嘿冷笑着,并不急于答话。说实话朱棣或者朱权再或者其他什么人当皇帝,对他和朵颜人乃至兀良哈族人来说。皆是无所谓的。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他这个部族的前途,他必须要权衡的是他这个部族的利害关系。张玉明白他的心态,于是便代表燕王向他承诺:一旦夺取了天下,将给予朵颜人以更大的自主权。一句话:“尽割大宁地界三卫,以偿其功”。
脱儿火察听说将来要把大宁的地界整个儿割给他,眼睛和那道伤疤同时“唰”地亮了。他手里一直转来转去玩着一把刀子的;此时停止了把玩,将刀子很熟练地在铺地的羊毛毡上弯弯曲曲划了一圈儿。然后拿手一揭,揭出了毡片片儿,是他想像中的大宁地界的图形。他扯住这毡片片儿在张玉眼前亮了亮说:
“这便是大宁地界儿,全归我了?”
“全归你了!”张玉说。
脱儿火察高兴极了,便把那代表“大宁”的毡片片儿贴到了胸膛上。眯眼向上咕哝了几句他那个民族的语言,像是祷告什么。然后再睁开眼,一边恋恋不舍似地把毡片片儿填铺回去,一边问张玉:
“朋友,这事情可是太重大了。可我怎么能轻易相信你呢?”
“这个好办。”张玉说,“我们可与部长大人签约——签订‘大宁之约’!”
“你,和我?”脱儿火察笑着摇摇头。
张玉连忙更正说:“自然不是我,是我们燕王殿下。”
“燕王殿下?他在哪儿?”脱儿火察问。
张玉笑道:“部长大人若不信的话,请看这是什么……”说着,从怀中掏出个黄缎包袱。打开来,恰是金质龟纽的“燕王之宝”。他双手捧着宝,放于毯上。然后他和朱能、火真便肃然起敬地改变坐姿,双膝跪于宝前。闹得脱儿火察也随着他们跪了。
脱儿火察下意识地将手在袍上揩了揩,去摸那金宝。他粗糙的手指接触到包裹金宝的黄缎时,黄缎神奇地蹭出火星儿,将他烫了一下。他皱裂的皮肤也挑起了几根黄色的纤维。但那金宝他是抓牢了,也看准了。确是刻着“燕王之宝”四个篆字——他也是识得汉字的呢。
于是,脱儿火察慎重地表示,他和他的朵颜卫,乃至朵颜部落的父老们,可以考虑与燕王签约,但是福余卫和泰宁卫,还须与安出和忽刺班胡商议。
张玉说,很好,我们可以一起去拜会安出、忽刺班胡二位部长。不过事不宜迟,迟则容易透露风声儿。我们签的是“密约”,是不能令外人知道的呢。
话说到这地步儿,彼此亦无须客气了。脱儿火察很坦然地收受了张玉等带来的厚礼。而张玉也便不再提什么过“百岁儿”的事。脱儿火察甚至忘记了应该让夫人将小公子抱出来,请客人们欣赏一下、夸赞几句。看起来他的心情比张玉他们还急。他吩咐一声:“拉马过来!”当即跨上马,带着张玉三人走出朵颜老营。
走出寨栅时,朱能听到后面有一女子叽哩咕噜唱了几句什么歌儿。歌词听不清,但猜测那定是蒲察唱的。他扭头一望,见果然是蒲察,向她摇着一条火红披巾,那脸膛也被披巾映得红彤彤的。
于是脱儿火察很惊讶似地上下打量了朱能一眼说:“咦,我女儿昨天夜里爱上你了吗?”羞得朱能抱住了头脸,差点从马上栽下来。惹得张玉和火真哈哈大笑……
以后的几天里,张玉、朱能、火真三人由脱儿火察引领、陪同,分别会晤了福余的头领安出和泰宁的头领忽刺班胡。少不得也是送上厚礼,直言不讳地提出要求。安出与胡刺班胡同脱儿火察一样,欣然同意。于是便由张玉、朱能、火真代表燕王,而由脱儿火察、安出、忽刺班胡代表朵颜、福余、泰宁三卫,在共同草拟的一份秘密盟约上签字、盖印。
盟约文本的文字如何写的,甚至有没有这么一份盟约,后人不得而知。但不管怎么说,朵颜三卫为燕王打天下确实立下汗马功劳,也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燕王——日后的永乐皇帝——对朵颜三卫甚是感激,另眼相看,赏赍甚厚,更不消说,将大宁辽阔的地域尽割三卫以自治,称之为“内藩”。其在历史上的功过,不知该如何评说。
而在朵颜三卫悄悄归附燕王之后,燕军的将士们又由脱儿火察等人牵线,化妆潜入大宁城里,秘密接触守城的将领、军校直至戍卒。尤其收买了松亭关守将陈亨的家奴,令其赶赴松亭关,说服陈亨降燕,伺机行动。与此同时,燕军还分头抚恤那些驻防松亭关的将士家属,给这些家庭悄悄送去了布帛、粮薪以至金银钞币。虽只有六七天的时间,但大宁已成为了熟透的果子,不须采撷,便会掉入燕王的怀抱呢!
五
燕王在大宁度过了六个难忘的昼夜。
他和宁王相处得甚是欢洽。二人或品茗,或行酒,或弈棋,或赋诗。说实在的大宁比不得北平,没多少风光胜景游览。宁王本想邀燕王一道打围狩猎的,无奈朱鉴、石撰等坚决反对,也只好作罢。他有心请燕王去“鸣翠楼”上消遣一番,又觉得不太合适。后来,还是将那位叫做青萍的妓女接到府里,让她操琴唱曲儿侑酒行乐。好歹也算是尽了做小弟的一片心意了。
至于燕王拜托宁王的那件所谓大事,日前也已办妥。宁王代燕王草拟了一份上报皇帝的“谢罪表”,请燕王看过,非常满意,便交待长史石撰誊抄,然后送发。
这时候燕王在大宁导演并主演的这出戏剧已渐入佳境,接近高潮。殊不知宁王也自觉地进入了角色,且演得相当成功。
当宁王再问燕王“还有些什么事儿需小弟办”时,燕王拂着长髯笑道:“无什么事儿了。我明日就该回去了。”宁王便说:“唉,真不愿四哥走啊!”燕王说:“我也真不想走呢。”忽然他想起了那只受伤的大雁,便问随侍的狗儿:“那只雁呢?它伤病可是痊愈了吗?”狗儿灰着脸垂着头嗫嚅道:“它一直不吃食儿,不喝水儿,昨儿已死去了。”燕王便大怒:“该杀的奴才!你如何竟让他死了呢?”狗儿忙跪下叩头请罪。宁王就为狗儿开脱,说那也不是他的过失,是雁自己绝食而亡,属于自杀呢。燕王又是重重一声长叹:“唉,雁啊雁啊,你何必如此呢?你为何不养好了伤,重新飞上天去呢?……”又是泪汪汪的。
宁王陪着燕王叹了几声,心里却在暗笑。笑燕王有点儿矫揉造作。
这天上午巳时,张玉通过朵颜三卫的守城兵校,将一张纸条儿辗转递到燕王手上。纸条上说:“诸事皆谐。似可按原计划行动。”那时候燕王正与宁王玩儿一种叫作“叶子”的纸牌。打这种纸牌须四人,另两位是朱鉴和石撰。燕王在端茶碗时,发现碗底下沾了一个小的纸团。他便趁着大家都集中精力看牌的工夫儿,将纸团取下,用自己的牌挡着,悄悄地展开读了。然后笑吟吟地说道:“这把牌儿,无疑我是要赢的了!”而宁王也说:“唔,我的牌也不错。柳暗花明,不会输的!”看来,输的只能是朱鉴和石撰了。
离别的前夕,这两位王爷并首躺在炕上,说了一会儿话,互相道个“晚安”,很快便都发出了鼾声。鼾声此起彼伏,时弱时强,时疾时徐,甚有韵味儿。这可以说是绝妙的琴与瑟的合奏,是鼓筒与鼓皮的共鸣。
但是在黑暗中,两双眼睛都是亮灼灼的。他们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呢。
燕王在前天(即十一日)接到了世子朱高炽的信函,得知李景隆军已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他心里急得要命,但又不能在宁王等人面前表现出来。他知道火候儿未到,不能揭开锅盖,否则便会吃夹生饭的,而现在好了,可以揭锅了。待明日“长亭送别”时,便会有好戏儿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