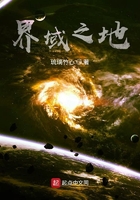席金玉定晴看去,只见陶丘山盔甲耀目,雁翅锐长八尺有余,非等闲之辈。便呼啸一声,先发制人,指东打西,元宝铁锐横扫千钧,不想刹那间又来了招大鹏展翅,击向陶丘山的脖颈。若在一般人,不死也伤,陶丘山却识破了他的诡计,雁翅锐陡举,挡住了席金玉的元宝铁锐。二人你刚我强,走马灯似地打得难分难解。大战二十回合后,陶丘山冷汗阵阵,虽竭力一拼,终未逃脱死亡的命运,被席金玉打中头部,脑浆崩裂。
铜管山见状,怒不可遏,欲要与陶丘山报仇雪恨,被李世民止住。李世民点将道:
“骁骑将军董理出马。本帅看得明白,此人有勇有谋,功夫卓绝,不可小视。但他已露出破绽,你当寻机击他背部。出马吧!”
董理虽然年过半百,勇武却不减当年。难得的是他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实战经验丰富。他也发现席金玉的背部往往露出空档,若不击其弱点,很难取胜。于是,打马出了阵门,直逼席金玉前胸,意在引诱席金玉将注意力集中在前面,加大后面的空档。
席金玉面不改色,洋洋得意,看董理的生铁棍如一条黑龙,在自己面部、胸部飞动,不免暗自高兴,元宝镜时而怪蟒翻身,时而力劈华山,耍得有板有眼,阴风四起,宛如凶猛的狂潮,横荡四溢,势不可挡。
董理亦非无能之辈,生铁棍指上打下,匡庐独秀,阴冷袭人,壮阔雄豪。胯下马似有灵性,与他配合得恰到好处。
二人大战三十回合,董理看若继续打斗下去,非吃亏不可,生铁棍突然在席金玉心窝处一戳,待席金玉阻挡之时,陡地抽回铁棍,打向席金玉背部。席金玉眼疾手快,回锐来挡,却为时已晚,背部中棍,口吐鲜血,坠地而死。
先锋独孤盛气冲宵汉,向宇文成都请缨出战,宇文成都大声制止,杀将出来,叫道:“李世民,你敢与爷爷大战三百回合吗?有种就出来与爷较量一番,无种就献城投降!”
“宇文成都,杀鸡焉用宰牛刀,何用本帅赔你玩耍,本帅的三弟李元霸早已按捺不住,就让他来夺你性命吧!”李世民在李元霸耳边窃语几句,接着道:“元霸,就看你的了,务要拿下宇文成都的脑袋。出马吧,我亲自给你擂鼓助阵。”
“二哥,你就看热闹吧。”李元霸在白龙驹的屁股上拍了几巴掌,白龙驹四蹄腾起,厮叫着冲人阵中,指着宇文成都道:“什么无敌将军,原来是个毛贼。”
宇文成都大惑不解,暗道:“李世民怎的令一个孩子出阵与我较量,这不是开玩笑吗?”想到这里,说出一番话来:“李元霸,快回家吃奶去吧,我堂堂威震华夏的无敌将军,与一个乳口小儿过不去,恐被天下人耻笑!”
李元霸闻言大骂:“放你娘的驴驹子屁,小爷前来拿你狗命是看得起你!”
“元帅,对付这个不懂事的黄嘴角子,何用你亲自动手,以防辱了威名,让末将将他挑于马下也罢!”
宇文成都顺声望去,原来是中郎将严如铁打马而来,便道:“严将军,就由你来销了他吧,省得脏了本帅的手。下家伙吧,本帅在这一边观战。”
严如铁不过二十多岁,英武不群,气宇不俗,胯下一匹黑花马,使一杆长七尺的劈水亮银錾。不知是他轻敌,还是技不如人,只战一合,劈水亮银枪便被李元霸的双锤夹住,怎么拔也拔不出来,这才意识到对手是个厉害主儿。
李元霸的臂力无人能及,双锤左一扭右一扭,竟将严如铁的劈水亮银錾的錾尖弄成了油炸果儿。严如铁惊惶失措,弃了劈水亮银錾,拨马就走。李元霸手起锤落,打发他上了西天。然后用锤指着宇文成都道:
“宇文成都,你打算怎么个死法?快快道来!”
宇文成都被激怒到了极点,方天画戟忽地一抡:“本帅包藏宇宙,吞吐天地,威震八裔,岂容你黄口乳子指名道姓地羞辱于我。今天不把你碎尸万段,难解心头之恨!来吧,看本帅在两合之内打你个血飞肉溅!”
“先别自吹自擂,较量一番后再下定论!”
李元霸求胜心切,冲向前去,抡锤便打,宇文成都举方天画戟迎住。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一个似下山猛虎,一个如出水蛟龙,直杀得走石飞沙,地颠天颤,太阳无光,两军将士膛目结舌,大战三十回合难分高下。若论功夫,宇文成都在李元霸之上,要论臂力,李元霸比宇文成都高出一筹,每当李元霸的双锤碰到宇文成都的方天画戟,宇文成都便觉双臂发麻。面对宇文成都出神入化的方天画戟,李元霸不得不时时小心。二人杀至四十回合,因长途跋涉,房事过度,体力已经减弱的宇文成都,经这番苦战,体力渐渐不支。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李元霸却积聚了大量的能量,此时才刚刚用去了一半,越战越勇。又战三个回合,他左手锤弄虚,右手锤击实,一锤下去,击碎了宇文成都座骑的头颅。座骑扑通倒地,将宇文成都摔在地上。他大笑着来了招蛟龙深海,锤打宇文成都头部。宇文成都就地十八滚,躲过了死神,然后一跃而起,抓起方天画戟刺向李元霸的大腿。李元霸哪会让他得逞,左手锤骤挡,宇文成都的手腕被震得生痛,不由倒退了数步。李元霸得势不让人,大喊数声,双锤奔宇文成都的太阳穴而来。在宇文成都九死一生之际,先锋独孤盛与数员战将打马前来救主,宇文成都方才逃得性命。
主帅败北,官兵不敢恋战,无不颤颤惊惊,做着逃命的准备。李世民见状,令旗一指,率十余万人马杀了过去。官兵如同退潮的海水,掉头就逃。义军士气大振,排山倒海般地掩杀过去,官兵死伤惨重。李元霸一马当先,双锤如流星,遇者死,挡者亡,一口气将数十个官兵送上了西天。
义军追出三里许,正杀得起劲,忽听城门处收兵的锣声响起,李世民只好下令停止追杀,收兵回城。
回到城中,李世民问李渊道:“我军杀得正酣,父亲为何下令收兵?若再杀他一个时辰,官兵伤亡就会十之有三,如此以来,官兵不过伤亡万人左右,遗憾哟!”
“父亲,你太善良了,咱与宇文成都势不两立,该乘机斩尽杀绝才是。”李元霸抹着脸上的血迹,愤愤不平地道:“我这力气才用了不到一半,再杀他个千儿八百的不在话下,杀死宇文成都王八蛋也不无可能。追杀时我一直在寻他,怎么也没见到他的影儿。都怪我,那只锤打到他脑袋上就好了,却击中了他的战马。下次要是再遇到他,就打他个稀巴烂!”
李建成、公孙顺德、刘弘基、李神通、柴绍等将领也都认为不该这么早就收兵,无不提出质疑。
李渊回答:“诸位的心情可以理解,三军服威,将士用命也非坏事。不过,穷寇莫追,这已是被许多战例证明了的。莫说敌众我寡,就是我众敌寡,一旦他们走投无路时,必奋起迎击,以图生存。兔子被追急了还咬人呢,何况人?凡善战者,无不先保护好了自己,后击打敌人。若离城太远失去依托,后果可想而知。就让他们多活些时日吧,欲速而不达。今我已效法杨广,让百姓坚壁清野,宇文成都无了粮源,必从关中运送给养,我再效法刘邦,切断敌之粮道,看他还能在这关中活多少时日!”
李世民与众将领以为有理,便不再议论此事,惟有李元霸耿耿于怀,牢骚满腹,嘴里不干不净,经李世民与李渊训教一顿,方才有所收敛。李世民道:
“元霸,你将宇文成都打落马下,又打杀了许多官兵,振奋了军威,本应给你记大功,因你在大将军与本都督面前无礼,这大功就免了。”
李渊帮助李元霸脱着盔甲:“你元霸是立了点功,但这点小功算什么?也值得自觉了不起吗?真正的英雄好汉有傲骨而无傲气。”
“我有傲气行不?”李元霸委屈地噘着嘴:“你俩的话我听了,错我也认了,以后再打这样的仗可要派我出马,最好给我个先锋做做。”
李世民哑然失笑:“先锋官除了能冲锋陷阵,还要服从军令,你这么任性,能做先锋官?天大的笑话。”
“这也不行那也不中,我不干了还不行嘛!”李元霸一时性起,转身就走。
李世民不去理他,嘴里却道:“天下这么大,比你有本事者多的是,少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
“元霸,你以为离了你这仗就打不胜了?走就走吧,没人会理你的。”李渊向李世民递个眼色,小声道:“别再理他,他还会回来的。”
果然,李元霸还未出郡衙的大门,便折了回来,先摇摇哥哥的胳膊,再傻笑着给为陶丘山写悼词的李渊磨墨。李渊与李世民如同没有看见他似的,谁也不搭理他。但二人都暗暗地在心里说:孩子,元霸毕竟还是个孩子,若调教得好,会成为一员良将的。宇文成都号称天下第一,却败在了元霸的手下,元霸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了,难怪他那么骄傲。
李渊写完悼词,一连看了数遍,然后向李世民道:“陶将军心底无私,勇猛刚烈,虽死犹生。为了张扬他的事迹,振奋士气,提高战斗力,应当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这葬礼由你主持,我来致悼词。”
“如此甚好。宇文成都吃了大亏,决不会就此罢手,肯定会进行疯狂的报复,明日不来,后天准来。这丧礼就在今天下午举行吧。我这就令刘弘基安排去。”李世民说做就做,即派亲兵前去传唤刘弘基。
李渊踱到院子中,围着那棵翠柏转着圈儿,思考着下一步的对策。接着一语不发地回到室内,向亦在苦苦思索的李世民道:“世民,这一仗打得爽快、利落,这与你的‘没有进攻的防御不是真正的防御’的战略思想有关,下一步还要进攻吗?”
“当然要进攻,是说以后,非指现在。眼下就照父亲保护好自己,才能打击敌人的说教办理,先打几仗防御战,待官兵大量减员,体力不支,厌战情绪饱和之时再进攻不迟。”李世民不无忧虑地道:“只是箭矢不足用,滚木擂石也不太多,若官兵连续攻城三天,就能告罄。”
“犒赏三军之事安排了吗?”
“安排下去了。杀羊一万只,宰牛五百头。只是酒不太多,仅储存了两万坛,若是尽饮尽用,所剩无几。”
“不要为给养犯愁,太原、弘化、龙门等郡县有大量的库存,会源源不断地运来的。到时官兵会尝到断粮的苦头。小麦已经收打完毕,秋作物还未成熟,再断他粮道,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施展了。以此为据,我敢断定,宇文成都还会行速战速决的战略。
“何时发兵断他粮道?”
“需在保此城万无一失的情况下发断粮道之兵。可以肯定,战事会相当激烈,很难在短时间内发兵断其粮道。”
“若是刘司马此时借来兵马就好了,可惜至今……唉!”
“兵马会借来的,突厥既重情谊又重财物。我与蒙古可汗吐凡利有八拜之交。吐凡利又与突厥首领始毕可汗感情甚笃,刘司马还带了那么多贵重礼品,他不会不借的。之所以用这么长的时间,一是突厥已归属隋朝,其首领很难决断,二是突厥地广人稀,一下子借十万兵马,非招新兵不可。若刘司马能在十日内借来兵马,敌之粮道便无切断的必要,合兵一处,转守为攻也就行了。”
李世民对突厥不甚了解,便问:“父亲,给我讲讲突厥的事情好吗?若刘司马借来兵马,与其打交道就会多起来,不知其详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