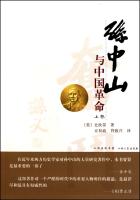时光犹如滔滔东逝的长江之水,在眼前一闪而过。不知不觉中,晋王杨广来到广陵在扬州总管任上度过了近十年的光景。
十年里,他走过了自己的青年时期,三十岁了,开始步入人生中的而立之年。十年里,他由一个血气方刚、勇武敢闯的藩王,成为一位更有心智、更加练达、更具声威的朝廷重臣。随着岁月的流逝,杨广觉得,从并州到扬州,不仅仅是父皇委以重任的结果,也是命运历程的必然。自己并不适宜生活在粗犷冷峻的黄土高原,而更应该融入脚下这片有川流、有泽水,既清秀纤细,又和煦温柔的土地。他喜欢这里,是因为这里的山川原野、人情风物迎合了他的性格,也最能体现他的性格,两者之间几乎不存在谁适应谁的问题,而是直接相融在一起的。再说萧妃原本就是南国淑女,能来扬州生活更是欢天喜地、求之不得的事。还有那个柳娣,是打胎不几天便随他一起赴任扬州的,一路上颠簸劳顿,到广陵时身体已虚弱得不行。然而没过几天,就养得面若桃花,楚楚动人,比在并州时更漂亮了。这些年,柳娣名义上依然是晋王府上的婢女,实际上却是杨广的小妾。柳娣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主见,无论萧妃怎样劝说,也绝不要那个名符其实的王姬身份。萧妃从未因为柳娣与晋王的那些事情对她忌妒怨恨丝毫,表面上当然是主仆,私下里却胜似姐妹。这使得杨广更加高兴畅快,他觉得只有南国女子才能如此宽宏怀柔。他认为这也是南国水土给自己的恩惠,他越加感激和留恋这片水乡泽国。若是父皇允许,他真要在这里住上一辈子。
就在这时候,杨广听到了最近在皇宫发生的几件事,确切地说是有关皇太子的几件事,让他在一瞬间就打消了久居南国的念头,他看到自己的宏图大业当然是在北方,在长安,在森严而辉煌的皇城里面。
这些关于皇太子的消息是扬州总管掾张衡由京城里带回来的。
在总管府的众多属官里,杨广惟对张衡甚为信任。张衡幼怀志向,才思敏捷。他十五岁入太学受业,其研精覃思一直为同辈推崇。开皇初年,被文帝拜为司门侍郎。杨广出藩并州时,张衡即拜为并州总管掾,后来又随杨广来到广陵,成了扬州总管掾。许多年来一直跟随着杨广,既是晋王的属官,更是他的密友。
杨广在调任扬州总管的时候,父皇文帝曾有旨意,允许他每年只回京朝见一次。这样一来可以让他专心做好扬州任上的事情,二来又免去了有事必朝的千里迢迢的劳顿之苦。杨广对父皇的用心和关爱甚为感激。但做为崇尚仁孝的晋王,每逢重要节令和岁末年终,他都要派官员带上许多南国的丝绸珍宝及名贵特产,进京去问候一下父皇母后和文武重臣。而每每担此重任的官员就是总管掾张衡。
眼下是开皇十八年的年末,张衡又一次为晋王完成了进京朝贡皇上皇后和文武重臣的使命,回到了广陵。
以往张衡自京城回到扬州总管府上复命时,总是与晋王先说一些皇上皇后的身体起居以及文武大臣收到礼物后对晋王感谢赞扬之类的事。而这一回见到晋王,行礼问安之后,张衡却选了一个新话题,他说:
“大王,依下官之见,大王应尽快准备,去京师朝见皇上、皇后。”
“哦?”杨广心下诧异。他没想到张衡会开门见山地说到朝见一事,因为他每年进京朝见都是在五六月间的暮春初夏时节。那时候北方的严冬已经过去,而炎夏的酷暑和秋天的大风尚在遥远,是最适宜北上的时候。这已成惯例,张衡更该知道。杨广问道:“总管掾此次进京,莫不是听到了什么于本王不利的消息?”
张衡微微一笑:“正好相反。大王,这次下官进京,所听到的都是对您有利的消息。”
“噢,真的吗?总管掾都听到了些什么事情?”
张衡收敛了笑意,压低了声音说:“朝中文武都纷纷传言,皇帝陛下对皇太了已经失去了宠信。甚至有人猜测陛下正在思谋着另立……”
杨广摆摆手,止住了张衡后面的话,说:“事关传承大隋基业,你我都不可胡猜乱说。”
张衡自知言语有失,低头称是。
“不过,”杨广又说,“凡事无风不起浪,你听到的那些纷纷扬扬的传言,一定是由什么事情引起的吧?”
“正是,”张衡答道。接着,他向杨广讲述了这么一件事。
一年之中,冬至也算是个大节令。按惯例,每逢冬至,朝中百官都要入宫朝见皇上,进献贺礼。今年的冬至,文武百官朝贺之后,又结队去了太子宫。皇太子杨勇身着礼服,大陈乐队,在东宫外热热闹闹地迎接百官,仪式非常隆重。
这事传到文帝那里,龙颜大为不悦。第二天早朝,文帝面对群臣正色问道:
“昨日冬至节,朕听说百官相率朝见东宫,不知道这是遵循的哪朝规制礼仪?”
殿下一时无人应答。少顷,尚书左仆射高颎出列奏道:“陛下,百官去东宫应为祝贺,不该用朝见一词。”
“是吗?”文帝冷冷地反问,心中不免有些反感。他认为殿下群臣之中无论是谁出来替杨勇说话都情有可原,而惟有你高颎不该出头。因为高颎的儿子已娶了太子的女儿,两人成了亲家。看来高颞是自恃功高权重,连这些嫌疑都不顾忌了。文帝想,既然你无所顾忌,朕也就不给你留面子了。就说:
“既然是节日祝贺,按常理应该是三人五人,至多十个八个地相随同行,而且是你来我走,随便哪个时辰都可以的。为什么百官同时集合起来作队同去?是有人征召,还是巧合?为什么太子还身穿礼服,鼓乐喧天地迎接百官?这又是哪朝哪国的礼制?”
皇上一连串地发问,殿下群臣鸦雀无声。
文帝故意停顿了一会儿,观察了一下殿内群臣面色,一个个都诚惶诚恐的模样,高炅页也耷拉下了眼皮。于是,他提高了嗓音,大声说道:
“自古以来,朝纲礼制等级森严,上下内外有别,君王臣属才不至混淆。太子勇虽然终将继承大位,而眼下仍是朕的臣子。正冬节令,文武百官另行朝贺东宫,不合朝廷典章制度,应当立即停断。此后若有违者,一律按谋反问罪。那时候,朕就不管他与太子有何关系了。”
群臣听的明白,这最后一句显然是在敲打高颎。接着,文帝又说:“当然,擅以礼乐迎迓百官是太子之过,朕自然不免追问教训的。”……
听了张衡的讲述,杨广沉吟了一阵,心中暗暗思忖:依父皇的脾气来看,对太子已不是有些不信任,而是心中早有猜忌了。他自思自叹着说:“唉,单就这件事而论,太子做得是有点过分了,也会对他人不利,比如高颏……”
“大王说得极是。”张衡接过话头,“礼乐受贺一事过了没几天,陛下传旨挑选宗卫侍官充实皇宫禁卫,一下子从东宫宿卫中选走了一批精悍校尉。高颎页马上奏称:若皇宫尽选取强者,恐怕会使东宫宿卫力量太弱了。陛下一听很是恼火,说:朕随时行动,宿卫必须雄毅。太子毓德东宫,左右何须强武?几句话便把尚书左仆射呛得额头冒汗,垂头丧气地退了出去。大王你想,这怎能不让人猜疑是太子与高颎大人串通一气呢?”
杨广一拍大腿,说:“嗨,这个高颎,怎么这样不看眼色。他果真以为功高可以镇主吗?哎,总管掾,刚才说的这些事,与你先前提到的要本王进京朝见又有什么关系?”
张衡呵呵地笑了,说:“大王一世聪颖,不会想不到吧。还非得由下官之口说出来不可?”
杨广似懂非懂地摇了摇头。
“大王,以下官之见,若皇帝陛下真在思谋废立之事,那最最有望立为太子的就是——”张衡说着,伸出右手的食指来指了指杨广。
杨广慌忙伸手将他的手指按下,说:“太子废立是国家大事,只有父皇可以言说,你我不可猜测。”
张衡说:“这些道理下官都明白。不过,大王,人一生之中要成就几件大事,就要有成大事的时机。时机到了眼前,即刻伸手抓住,事就成了。若稍有疏忽犹豫,时机错过了,就会一去不复返。下官觉得,眼下正是该大王伸手去抓一抓、试一试的时候。”
杨广觉得,张衡说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好像火镰敲击火石进发出的一簇簇火星直射自己心胸。心胸里好似藏有一堆干柴,哪怕有一颗火星溅上去,定会燃起一蓬烈火。杨广知道,这烈火一旦熊熊燃起,是会烧塌苍穹的。所以他一直在躲闪着,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躲闪,或许这是人的一种本能。
他对张衡说:“今天咱们两个说的话,你绝不要再跟任何人提起!”
张衡点点头,说:“大王尽管放心。下官跟随大王多年,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自己心里有数。”
张衡心中的确有数,因为他看到,晋王已经动心了。
这一夜,杨广辗转反侧,大睁着两眼没有丝毫睡意,心中似有一股激流在奔腾汹涌。他分明地感觉到,那堆干柴已经被点燃了。
反正睡不着,杨广索性坐了起来,拉过一条锦被围在身上。
萧妃也睁开了眼。其实她一直没有睡着,听着杨广翻来覆去地折腾,她感到了反常,此时见他干脆坐了起来,自己也不想再装睡.忍不住问道:
“你今天是怎么了,有什么心事吗?”
“没事,就是睡不着。”黑暗中,杨广淡淡地回答。
萧妃掀开被子,披衣下床,摸索着点燃了一盏灯,又回到床上陪杨广坐着。暗暗的灯光里,她看到了丈夫脸上有一种自己几乎没有见过的表情:凝重、痴醉,还夹杂着激动。她又试探着问道:
“要不,我去叫柳娣过来……”
“唁!看你又想到哪里去了!”杨广打断萧妃的话,说:“在你们女人眼里,男人到了夜晚除去寻幸床笫之事就再没有什么可想了,是吗?”
萧妃摇摇头,说:“大王可真是冤枉妾妃了。我是见大王满腹心事,又不想对妾妃讲,所以……唉!”
杨广笑了:“爱妃的眼力没错。我不是不想对你讲,是怕把心里想的事讲出来,惊得爱妃更无法入睡了!”
萧妃抬头朝杨广浅浅地一笑,说:
“妾妃随大王这么多年,虽没见过什么排山倒海的阵势,眼见耳闻的事情也不算少了。能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至于惊倒妾妃么?”
杨广没有立刻回答,只是用两眼直盯着萧妃,良久,他突然问道:
“爱妃,你想不想做皇后?”
萧妃就像被人兜头浇了一瓢凉水,浑身猛地一颤,脸色都灰青了,张口结舌地说:“大、大王,你……”
杨广见她这副模样高兴地大笑起来,又展开披在身上的锦被,将她裹进来,说:“刚才还说没有吓倒你的事。看,只有一句话就把你惊得这副样子!”
萧妃难为情地说:“真没想到大王会拿这样的话跟妾妃开玩笑。”
“不是跟你开玩笑,”杨广压低声音,一本正经地说,“这一夜我都在想,怎样才能让你做皇后。”
萧妃一下子从杨广的怀里挣脱出来:“那、那么,大王是想……”
“不错,我想做皇帝,继承父皇的大业!”
“那皇太子……”
“当然,我得先立为太子,才能继承皇位。”
“不,不是。我是说,父皇陛下早已立杨勇为皇太子多年了!”
“凡事都不是不可以变的,所以,今晚我一直在想——”
杨广对萧妃讲了张衡在京城里听到的事情,以及要他进京朝见父皇的想法。
“我觉得张衡说的有道理,应该去京城里看看。”杨广继续说,“当然,事关天下安危,父皇即使有些什么想法,时机不到也是不会轻易表露的。不过,我觉得总可以从母后那里或多或少地听到些消息,探得点风声。父皇母后号称宫中二圣,有什么大事总是一起商议,拿出决断。再说,父皇能对朝中群臣严责太子的过失,极有可能还是受了母后的感染。”
萧妃听了这番话,情绪稍稍有了点稳定,她轻轻地说:“妾妃虽然也生在帝王之家,却自幼生长在乡野民间,见识短浅,更无城府,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妇道人家。幸得天降洪福跟随了大王,长了许多见识,享受起了荣华富贵,夫妻之间也恩爱甜美。妾妃原想,此生能得到这般境遇就非常满足了。大王,这些年来,你做过的事情,无论是对是错,妾妃从未阻拦干预过。今天这事我也不想多说,只想提醒大王,此事非同小可,稍有不慎定会招来杀身大祸,所以,一定要小心行事,万万不可轻易将自己的心思流露出来。”
杨广心中很是感动,拉过萧妃的手抚摸着说:“凡要做大事,都得冒风险的。我也仔细想过,依我晋王才干威望和对国家建立的功勋,都不在皇太子之下,按说继承帝位的应该是我,朝中文武也不会有异议。可为什么我只是晋王而不是太子呢?就因为我是父皇的次子而不是长子。这多么不公平啊!这种因袭了多少年的,不看才干功业而传立宗室的陈章旧制,难道就不可以改一改吗?”
说着,杨广又激动起来,手都有些颤抖。但他马上意识到了,这样更会增加萧妃心中的不安,于是他又笑了笑,说:“不过爱妃尽管放心,我要做就会做到成功。眼下还不到冒险去做的时候。此次进京,我只是先试探一下父皇母后对太子的态度面已。”
萧妃喃喃地问道:“不去试探,行吗?”
杨广坚定地摇了摇头。
“唉!妾妃真的弄不明白,天下人为什么都喜欢那个王位,都想得到那个王位呢?”
“因为,得了王位,天下就是自己的了。有了自己的天下,才能去做一切自己想做的事!”
对丈夫的回答,萧妃似懂非懂,只是在心里想:除了做皇帝,你现在还有什么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