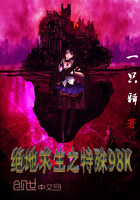太阳刚刚爬过对面楼房的顶上,弟弟便开始忙活了,穿上那件浅灰色的长风衣,背着那把破吉它出门,去广场上上班了。
家门附近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广场,平时闲人多过路的人也多,弟弟踩着一地的阳光,慢慢踱向那个花坛,坐在花坛的边沿上,开始工作。只是他所谓的工作,和周围那些面前摆着破碗或者竖着写满悲惨经历的人性质一样,只有他称那是工作,而且是很认真地说。
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笑着对他说:“你周围的那些人,不会让你抢他们的生意的!”他神秘地笑,说:“山人自有妙计!”只是那天中午回来,弟弟的长风衣上布满了脚印,他连饭也没吃,回到自己的房间,一会儿工夫便传出了呻吟声。到了午后,他居然起来了,而且把风衣上的灰掸得很干净,背上琴又要出去。我叫住他:“换身行头吧,你穿成这样去,不挨打才怪!”他留给我一个倔强的背影,迈着微瘸的腿,看来被教训得不轻。
晚上弟弟下班,回来后神采飞扬,衣服也干干净净,看来不但没挨打,生意好像也不错。我打开他的琴盒,却是一个硬币也没倒出来。于是嘲笑说:“你连一毛钱都没挣到,还乐得像捡了金条一样!”他故作高深地一耸肩:“太俗,张口闭口都是钱!我这高雅的艺术岂是金钱能衡量的?再说,大哥,我挣的钱并不比你少啊!你别像地主婆一样剥削我!”这孩子,真是神经了!
夜里,弟弟房里传来劈哩啪啦的打字声,我无聊地玩儿了一会儿,竟伏在电脑前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屏保的图案在眼前变幻,已经过了零点,弟弟的房间里已没有了声音。我继续上网,到一个网站上看小说,看弟弟的长篇玄幻,他同时开了两本书,都已经签约上架,也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的第一部,现在书摊上四处都是盗版。但是却看得我着急,我常批评他:“大白天的时间再家写书多好,你知道那些无聊的读者多么期待?你对得起他们吗?”那样的时候,他会斜我一眼:“读你书的人就不无聊?而且,我知道,你也在看我的书,你这个正统的作家怎么也无聊起来了?”我悻悻:“我只是想看你怎么成为太监的!看你想象力那么放得开,最后怎么往回收!”他回以我的依然是背着琴盒有些酷酷的背影。
弟弟一个秋天都在往广场上跑,就像有瘾似的,依然是一分钱也没拿回来。有一天,我对他说:“你先给我弹唱一首,我看是不是你把那些人都吓得不敢从广场经过了,我觉得最近咱们这儿行人特少!”他倒是没拒绝,坐在那儿给我弹唱了一首Beyond的《再见理想》,唱得倒是有那么几分味道。唱毕,他说:“看你层次可能高些,才唱的这首,我在外面唱的,都是大众喜欢的。你弟弟我的嗓子可不是盖的!”我回以颜色:“别看你唱歌不上税,吹牛可是要上税的!”
我知道弟弟有段时间在恋爱,而且十有八九去广场上唱歌是为这事。那个秋天,每一天他的情绪都在微妙地变化,或幸福甜蜜,或伤感多思,或黯然,或兴奋,而且,他的玄幻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和他的心境契合着。只是有一天晚上我看他的更新,男主人公和那个心爱的女人竟然分手了,让我震惊不已,回想当天,弟弟并没有反常的情绪,没有那种失恋的痛苦和忧伤,反而有种平静中透着的安静与满足,真是奇怪的孩子!
快冬天了,弟弟还是那身装束,我曾对他说:“你得多买几件风衣了,总穿一件,观众们会有视觉疲劳!”他却说:“没多长时间了,冬天就不出来了,太冷,旁边的那些人冬天也很少出来!”这家伙,居然跟那些乞丐对比上了。他却一本正经地说:“那些人并不是像你想象中那样骗钱的!”我不理他:“好了伤疤忘了疼,忘了第一天他们联手揍你了?”
一天天地寒冷起来,我平时足不出户,这天却突发奇想,想去看看弟弟。正是下午下班的时间,广场上人来人往,弟弟被包围在一小簇人群里,看不见人,却听见吉它声歌声传出,这小子,一首流行歌曲倒是唱得也满动人的。我挤进去,看见他面前的琴盒里已经装了不少钱。我躲在一边,一会儿,人都散了,弟弟艰难地站起来,把琴盒里的钱散发给周围的乞丐们,还说:“这回你们冬天不用出来了!今年冬天更冷!”终于明白,这小子挣的钱居然这样消费出去了,整个一个秋天,他等于替那些曾经打过他的人讨钱!
我先跑回家,站在一楼的窗口,看着弟弟慢悠悠地走回来,凉凉的风吹动他长长风衣的下摆,脸上依然是满足的神情。一进门,他立刻换了一副神情,急急地甩了风衣,脱下裤子,把左腿的义肢摘下来,疼得呲牙裂嘴,腿根的断处,已经磨得不堪入目。我忙为他抹药,再把他抱回房间。
那个夜里,我在弟弟更新的小说中,看到他借主人公的口说出的几句:“原以为最幸福的事,是和心爱的人相伴偕老,现在才发现,最幸福的事其实给别人以帮助;原以为最痛苦的事,是恋人陌路,可是经历了才知道,在那份帮助别人而得到的幸福面前,这种痛苦微不足道。”
第一次,在深深的夜里,听着隔壁弟弟熟睡的声音,在电脑前,我没有伏案而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