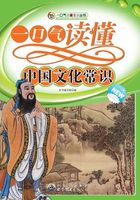市电视台新推出一档娱乐节目,叫“舞林争霸赛”。我是科班出身,领导让我负责参赛选手的选拔工作。这天傍晚,一走出电视台大楼,我便隐隐觉出有点不对劲:有人在躲躲闪闪地跟踪我,而且是个女子!
说实话,这段日子,我没少和跟踪客打交道。因为这个节目的赞助商有实力,奖金设置格外丰厚,单月冠军就有近万元奖励。当然,相当多的选手,特别是女孩子压根不是冲着钱来的——若能嘁哩喀喳地杀入年度决赛,赞助商会进行包装宣传,没准儿就能红得一塌糊涂。
走到街角,余光一扫,只见那个女子拐了弯。刚要松口气,一个看上去约摸有40岁的中年男子冷不丁地立在了我面前,赔着笑怯怯地问:“您是夏老师吧?”
我姓夏,叫夏松。不等我点完头,中年男子忙掏出一沓资料,恭恭敬敬递来:“我叫宋大川,想报名参赛——”
“你多大了?”我没有接,笑着打断了他。
这次赛事,对选手的年龄做了明确规定:16岁以上,30岁以下。从节目开播到现在,我已查出多个谎报年龄的选手,甚至有些家长也跟着添乱,在户口本上做手脚。眼下,不用看资料,只看长相,我就能断定这个叫宋大川的男子明显超龄。
许是瞅到我笑得别有意味,宋大川猛地拍了下脑门,从资料里抽出张照片:“夏老师,我说走嘴了,我是给女儿报名的。你看,这是我女儿宋春天,上个月刚过完16岁生日。”
原来是给女儿报名的。照片上的女孩身材不错,也很可爱,正嘟着小嘴在扮鬼脸。
看过照片,为了避嫌,我仍没接报名资料,说:“宋先生,咱按正常程序走,你明天送到栏目组。只要选手符合条件,就能参加预选赛。”
“真的?你是说我女儿也能上舞台了?”宋大川眼前一亮,变魔术般从墙角拎出一只布袋:“太谢谢你了夏老师。这是我自家养殖的黑木耳、蘑菇,你一定得收下——”
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这个道理,我懂。可宋大川硬往我的怀里一塞,转身跑远。看他那几步跑,似乎还有点踮脚。没办法,我只好拿回家,准备明天再还回去。不料,第二天早晨下楼锻炼,我一眼就看到宋大川缩在街角,屁股下垫着张纸壳,脑袋枕着膝盖呼呼哈哈睡得正香。
莫非,他在这儿蹲了一宿?我满心纳闷地走上前,叫醒了他:“宋先生,你……没走?”“没,没,哦,我没事。”宋大川揉揉睡眼,慌忙站起:“夏老师,我还有件事想问问你,舞伴有……有说法吗?”
这个没具体要求。如果选手找不到合适的舞伴,栏目组还会帮忙搭配。解释完,我问:“你女儿怎么没和你一起来?她都会跳什么舞?”
宋大川嘎巴嘎巴嘴,一脸的难为情:“不瞒夏老师,我是林甸镇的,家里条件不好。不说这些,还是说说我女儿吧。春天打小就喜欢跳舞,转圈舞跳得可棒了。真的,邻居们都说,春天一定能跳出大名堂——”
转圈舞?知道拉丁、伦巴,也知道肚皮舞、街舞,至于这个转圈舞,我还真没听说过。见宋大川眉飞色舞说个没完没了,样子像极了他的女儿已经技压群芳夺了魁,我不觉有些烦。林甸镇我去过,穷山恶水,十年九旱,百姓的日子过得不富裕,可再穷也不能拿孩子当摇钱树啊。心下想着,我拦住了宋大川的话茬:“这样吧,资料我收下,下周一你带女儿到电视台填表。要没问题,当天就参加第一轮预选。”
宋大川又是一通道谢,乐颠颠地走了。
转眼到了周一早晨,刚到电视台还没进门,我就听到有人喊我。循声找去,是宋大川。宋大川一手提着个大包裹,一手牵着照片上的女孩,跑得气喘吁吁。更让我始料不及、大跌眼镜的是,他的女儿宋春天走路摇摇摆摆,嘟着小嘴也非扮鬼脸,而是就那样:非常典型的脑瘫儿!
“喂,你开什么玩笑?病人是不能参加比赛的!”我顿觉受了愚弄,没好气地质问。没想到,宋大川也瞪了眼,嗓门比我还高:“夏老师,春天没病。你好好瞅瞅,她没病!”
00她没病,那就是你有病!我懒得和他纠缠,抬腿要走,宋大川却拽着我走到一旁,低声苦求:“夏老师,对不住了。没人的时候你打我骂我都成,可当着春天的面,我求你别说她有病,行吗?”
瞅着宋大川可怜巴巴的眼神,我的心倏地疼了一下,耐着性子说:“比赛有规定,参赛选手必须身体健康——”
“夏老师,春天她很健康,爱说爱笑,还能帮我干家务,真的。”宋大川像抓住救命稻草般死死握着我的手不放,沙哑着嗓音道出了参赛的原委:春天一生下来就是个脑瘫儿,街坊邻居们都劝他扔了算了,他没听。为了给春天治病,家里的积蓄花光了,还欠下一大笔外债。妻子受不了苦,狠心走了,是他一个人将春天拉扯大的。他发现,春天站不稳,可特别喜欢跳舞。于是,他买来舞曲光盘,让春天跟着学。这一学就是十多年,一天都没耽误过。
听到这儿,我问:“宋先生,你能告诉我,为什么非要带春天来参赛吗?”
当下,很多节目都靠煽情提高收视率。对这种揭伤疤赚眼球的做法,我一点儿都不感冒。如果宋大川也想用女儿的不幸赚取同情,对不起,请便。孰料,宋大川嘎嘣溜脆地回道:“我要让春天知道,她不光长得漂亮,舞跳得也好。”
没错,跳得不好,哪能上舞台?和同事商量一番,我决定破把例,让春天参加选拔赛。可一做出这个决定,麻烦又来了——整个节目组居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舞伴。原因非常简单,根本没人会跳什么转圈舞!
实在没辙,我只好征求宋大川的意见,打算让宋春天来一支独舞。宋大川一听,脑袋当即摇成了拨浪鼓:“夏老师,还是我来吧。在家里,春天每次跳舞都是我陪着她。”
你?我惊讶得叫出了声:“你能行吗?”
话一出口,才知多余。难怪那天宋大川会问舞伴有没有要求,看得出,别人给春天做舞伴,他还一百个不放心。春天腿脚发软,一不留神就会栽倒。舞伴要笑话她,定会伤了她的自尊。而父亲不会,父亲永远都不会笑话自己的女儿。
好,就你了。我冲灯光师、音响师和摄像师发出了指令:全心投入,有请宋春天登场!
随着轻柔的音乐响起,宋大川扶着女儿慢慢走上舞台,冲着我和同事腼腆地鞠了个躬后,开始转圈,不停地转圈,动作几乎没有任何亮点。尽管只是重复地旋转,可宋大川每转一圈都非常小心,生怕踩着女儿的脚。灯光师将灯柱打到宋大川的脸上,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人都看得真真切切,他的眼圈里亮亮的。那是一个父亲的骄傲,一个父亲的幸福。
“哎哟——”
突然,意外发生了,许是舞台太滑,满脸陶醉的宋春天冷不丁地脚下一歪,身子瞬间失去重心,趔趔趄趄地就要摔倒。宋大川也慌了神,赶忙去扶。一时没站稳,“啪叽”摔了个腚墩。不过在跌倒的同时,他紧紧地抱住了春天。
“夏老师,都是我不小心,是我没用,不关春天的事。你们都看到了,春天跳得很棒。求你们了,让我们再来一遍,好吗?”宋大川半坐在舞台上,急得脑门直冒汗。
如此简单的请求,我没有理由不答应。很快,宋大川吃力地站起,牵着女儿继续转。转着转着,春天一头扎进宋大川的怀里,泪光莹莹:“爸,谢谢你带我来跳舞。我知道,我能行,一定能行……”
预选赛结束,宋春天的比赛之路也到此结束。目送他们相互搀扶着走出电视台大楼,我灵光一现,冲刻录师喊:“快,马上做一套宋春天的比赛光盘。标签上要表明:宋春天的春天之舞。”
十几分钟后,我扬着光盘追了出去:“宋先生,宋春天,请等一下——”
宋大川听到了,踮着脚跑来。由于跑得太急,在踏上台阶时又摔了个跟头。谁能相信,他的左腿竟然脱了节,横飞出去——
那是一条劣质的假肢!插柳村的爱情
一
当天色黑下来时,听到枪炮声渐渐远去,乔榛才哆哆嗦嗦钻出了隐藏在墙角的菜窖。
门板砸了,柴垛烧了,鸡鸭也一只没剩。望着被折腾得七零八落的院子发了阵呆,乔榛禁不住浑身一激灵,猛地扑向散发着焦煳气味的东厢房:“先生,先生——”
乔榛哭喊的先生,是昨天刚娶了她的男人赵永志。东厢房是他们的新房。就在今早,插柳村外突然枪声大作。不等村民们想明白怎么回事,凶神恶煞般的鬼子来了。透过门缝看到鬼子无恶不作,乔榛当场吓得双腿发软不听使唤。好在赵永志反应快,一把将她推进菜窖封盖了个严严实实。后来,她隐约听见院子里鸡飞狗跳,乱作一团。
满地狼藉的新房里,没人。乔榛抬腿正要去街上找,一个敦实的车轴汉子冷不丁地出现在面前。
“黑牛,瞧你鬼头鬼脑的,想吓死我啊?”乔榛吓了一大跳,很快认出车轴汉子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黑牛。黑牛拦住乔榛,瓮声瓮气地说:“不准你出门!”
乔榛不由一怔:“为啥?鬼子不是走了吗?我要去找我先生。”
“赵先生他……他——”
“你说啊,我先生他怎么了?你让开啊!”见黑牛吞吞吐吐,乔榛的心一下子提溜到嗓子眼里,用力搡开黑牛跑出了院。刚出门,脚下就绊上柴捆摔了个跟头。
不是柴捆,是死人。满街都是死人!乔榛“啊”的一声惊叫,慌张奔回院子扎进了黑牛的怀里:“黑……黑牛,死人……”
“乔榛,插柳村没人了。要不,你也走吧。”黑牛抱着乔榛不停颤抖的身子,说。乔榛一听,急忙挣开:“我不走。我先生让我在家等他,他不会扔下我不管的。”
沉默半晌,黑牛指指东厢房,示意乔榛回屋,接着挡住院门,掉头走了。第二天一早,乔榛强按着怦怦心跳上了街。四下望去,街面已被收拾得干干净净,淌过血的地方也撒上了一层新土。尽管如此,整条街静得还是让人骨子里发毛。想到黑牛昨晚说的话,乔榛小心地推开了隔壁宋婶的院门。
颤声招呼了两遍,没人应声。乔榛没敢进,又走向下一家。一直走到村口,却只瞄见一个人:黑牛。黑牛正光着膀子,在野地里闷头挖坑。
“黑牛,你没走?”乔榛凑了过去。看得出,黑牛整夜都在忙,眼睛里满是血丝,手掌也磨出了血。听到询问,黑牛顿时像个孩子似的呜呜大哭:“我是他们养大的。我要走了,谁来照顾他们啊?”
顺着黑牛的手指看去,乔榛惊呆了——庄稼地里,一夜之间堆出了大大小小几十个新坟!
“黑牛,看没看到我先生?”乔榛跌跌撞撞地冲向坟包,挨个查看。
“乔榛,别找了,这里面没赵先生。”黑牛欲言又止:“他,他……”
乔榛急了,扯着嗓门催问:“他在哪儿?你快告诉我啊!”
“他,他跟古家二小姐跑了——”
古家二小姐叫古梅,和赵永志同在村学堂教书。黑牛说,鬼子杀进村时,藏在柴草垛里的他瞅见赵永志翻出院墙,拉着古梅跑向村外。听到这儿,乔榛沿着两人跑走的方向找出了足有十多里地,却连半丝人影都没找到……
二
插柳村本就不大,老老少少全算上也不过百余口人。鬼子一走一过,没来得及逃的全遭了毒手。等黑牛埋完最后一个遇害乡亲,插柳村平添了七十多座新坟,整个村子也只剩下乔榛和黑牛两个人。乔榛每天都去村口等,眼巴巴地盼着赵永志回来;黑牛则握着根手腕粗的铁棍,不远不近地跟着。
这天,乔榛又走向村外。黑牛赶忙跟上,吭吭哧哧:“乔榛,别去了。赵先生他不会回来了——”
“我不信,他会回来的。就算等一辈子我也要等!”乔榛硬邦邦地打断了黑牛。在嫁给赵永志前,村里曾有人传闲话,说古梅经常找赵永志,关着门一嘀咕就是好半天。乔榛没念过书,和赵永志也只在宋婶的介绍下见过一面,但她相信自己的眼光:先生不是那种不正经的男人。不然,她也不会嫁给无父无母、借住在人家东厢房里的他。
黑牛再不多言,将铁棍别进后腰,三下两下爬上长在路口的那棵大柳树,把风。转眼又过了大半年,赵永志仍旧毫无音讯,乔榛却显了怀,走路也变得格外吃力。更糟糕的是,一天傍晚,乔榛挺着大肚子刚要去村口,就见黑牛大步噔噔地闯进了院。
“黑牛,是不是我先生回来了?”乔榛急忙迎上。
黑牛顾不上喘匀气,弯腰抱起乔榛直奔墙角的菜窖:“我看见鬼子了。你快藏好,别出声,我去把他们引开!”
掩好窖口,黑牛爬上了院墙。眨眼工夫,院子里便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乔榛心惊肉跳地从窖盖的缝隙望出去,只见三五个鬼子端着枪,到处乱戳。眼瞅要搜到菜窖跟前,黑牛忽又从墙外探出头,边骂娘边朝鬼子撇瓦块。鬼子叽里呱啦一通喊叫,紧跟着追去。
黑牛,你快点跑,别让这帮畜生追上你。乔榛在心里喊。恰恰这时,几声沉闷的枪响撞入了耳鼓。
黑牛,求你千万别出事。啊——
许是受惊动了胎气,乔榛顿觉腹疼难忍叫出了声。不好,孩子要出生了!乔榛一咬牙,撕下块布条塞住了嘴巴……
约摸半个时辰后,窖盖被揭开。是黑牛!乔榛指指身下,气息奄奄地喊:“快,快,快拍孩子的脚心——”
喊声未落,“咕咚”,黑牛一头扎进菜窖,昏死过去。乔榛看得真真切切,黑牛的腿上血污一片……
三
乔榛生下的是个男孩,胖乎乎的,很可爱。为了引开鬼子,黑牛右腿被子弹击穿,成了瘸子。转过年,插柳村陆陆续续回来了几个人,其中有古梅的父母和弟弟。还和往常一样,乔榛抱着儿子守在村口,见人就问:你见过我先生吗?他叫赵永志。你们看,这是他儿子,念志。
念志。这名字叫着顺口,好听。黑牛一瘸一拐地跟在乔榛身后,翻来覆去地咂么乔榛给孩子起的名:念志,想念的自然是赵永志。世上的事还真架不住念叨,在念志满两周岁那天,好消息终于传了来:有个逃难的乡亲在克山城碰上了赵永志。赵永志托他给乔榛捎来了话,等世道太平了,他就回插柳村看她。
“黑牛,你听见了吧?我先生他好好的,很快就回来了。”乔榛惊喜地眼泪直流:“你领念志玩,我这就收拾屋子去。”
“唔。”黑牛应了,蹲身驮起念志去了村外,怔怔地瞅着那座座坟冢出神。念志稚声问:“黑牛叔,他们都是谁呀?”
“他们都是黑牛叔的亲人。有爷爷奶奶,大伯大婶,还有兄弟姐妹——”
正说着,乔榛匆匆跑来,红着脸颊说:“黑牛,我想和你商量件事。我先生是教书先生,礼数多——”
“我知道,我一会儿就搬。”黑牛虽长得粗实,憨厚,可也明白乔榛的心思。自打鬼子屠村后,黑牛就搬进了隔壁宋婶的空房。那些日子,村里死寂得瘆人,黑牛就敲墙:乔榛,咱插柳村都是好人,别怕。赶上刮风下雨,乔榛吓得睡不着,黑牛索性守在院门口,一站就是一整夜。如今,赵永志要回来了,为了避嫌,他得搬走。当晚,黑牛在村外离那一座座坟冢没多远的地方搭了间窝棚。乔榛有些过意不去,帮着铺了炕,问:“黑牛,你为啥不走,为啥对我这么好?”
黑牛看了眼坟冢,没吱声。那年,7岁的他逃荒逃到插柳村时病倒在路边的柴垛里。要不是乔榛发现了他,喊来乡亲把他背回村,喂药喂饭,他早冻死饿死了。做人不能忘本,他要日夜守着乡亲们,逢年过节为他们烧点纸,添几锹土。
“黑牛,等遇到好人家的姑娘,我给你做媒。”乔榛接着说。黑牛脸红了,支支吾吾:“你……真信赵先生能回来?”
“嗯,我信他。”乔榛说得很坚决。果不其然,这年初秋,鬼子一投降,赵永志就回到了插柳村。可让乔榛做梦都没想到,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古家二小姐古梅。古梅挺着个大肚子,一进门就跪倒在地,哭求乔榛原谅。一时间,乔榛犹如五雷轰顶,懵了。
“乔榛,对不起,我,我——”
“你走,你们走啊!我再不想看到你们!”乔榛没听赵永志的解释,发疯般将两人轰出了院。等她哭够了,哭哑了嗓子打开门时,门外只戳着黑牛。黑牛嘎巴嘎巴嘴,说:“他俩走了——”
“你也走!我谁也不想见!”乔榛抱着念志,泪花扑簌簌地流满了脸……
四
和赵永志成婚那年,乔榛才17岁。一夜洞房,有了念志,生离死别多年,谁想苦等苦盼来的却是这样一个结果。黑牛想说,他几次见过赵永志和古梅手拉手,可话到嘴边又改了口:“乔榛,日子还长着呢,你打算咋办?”
还能咋办?一天天过呗。有念志,就有奔头。说完,乔榛扛起锄头,牵着念志下了地。仿佛只是一晃,两年过去。这天半夜,一个人影鬼鬼祟祟摸进插柳村,悄悄攀上了乔榛家的墙头。抬腿正要跳,忽觉脑后生风。
是黑牛。黑牛挥起木棍,砸向黑影的后脑勺。黑影躲闪不及,骨骨碌碌摔进了院内。乔榛被惊醒了,抱紧念志惶惶地问:“谁?”
“一个贼。”门外,传来黑牛的动静。不料,黑影低声喊:“是乔榛嫂子吧?我找你有要紧事。”
的确是要紧事。进了屋,来人揉揉后脑勺,道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原来,赵永志是共产党,在插柳村以教书先生的身份做掩护,暗中搜集情报。出身地主家庭的古梅也是他们的同志,赵永志搞到的情报都由她电传组织。鬼子屠村的第二天,两人又接到新任务,以夫妻的名义在克山城潜伏下来。抗日胜利后,因古梅的大哥在国民党内任要职,组织又让两人借这层关系加入国民党,继续做情报工作。那次回插柳村,古梅假扮怀孕,是做给她父亲看的。正是她父亲写给她大哥的一封信,省去了不少麻烦。
听到这儿,乔榛急急插话:“你是说,他们是……是假夫妻?”
“以前是。后来,后来不是了。”来人迟疑地说:“我这次来,是想请你帮忙照顾他们的孩子。”
什么?赵永志抛弃了我,却让我照顾他们的孩子!乔榛紧咬嘴唇,沉默不语。
“不久前,他们俩身份暴露,全被逮捕,组织上正在想办法营救。赵永志同志被捕前说过,你是个好女人,好母亲,他对不起你。如果他和古梅同志出了事,就把孩子送回插柳村——”
在那样险恶的环境里工作,朝夕相处,难免生情。不管赵永志做的是对是错,可孩子是无辜的。乔榛擦擦眼泪,抬起了头:“别说了,孩子呢?”
“我把他藏在村口了。是个女孩,叫念榛——”
念榛?乔榛一听,泪水流得更欢:“黑牛,你快去找孩子,找念榛!”
收养了念榛没多久,黑牛去了趟克山城,带回一个不幸的消息:在集体越狱时,古梅替赵永志挡了子弹,英勇牺牲,赵永志也受了重伤,下落不明。
我先生不会有事的,他一定会回来的。就算不为我,为了念志念榛他也会回来的!乔榛拉住黑牛的手,一再央求:“黑牛,求你多往克山城跑着点。碰到我先生,就把他拽回家看看孩子,看看念榛念志……”
五
转眼6年过去,听说大半个中国都解放了,赵永志始终杳无音讯。又苦捱了8年,依旧没等到赵永志的乔榛一病不起。弥留之际,她让念榛念志出了屋,只留下了黑牛。
乔榛有好多的话要对黑牛说:鬼子杀来那天,黑牛不准她出门,是怕满街的尸首吓着她;隔壁住着,黑牛从没在夜里睡过觉;为了引开鬼子,他故意跑得慢,腿上才挨了枪;家里有了两个孩子,黑牛宁肯吃糠咽菜也要节省粮食……她懂黑牛的心思,可时间已经不多,来不及说了。乔榛满眼感激地看着黑牛,抬手想摸摸他的脸,伸到半空却又垂了下去:“黑牛,下辈子……”
插柳村外的野地里,又多了一座新坟。
后来,念榛念志长大成人,先后离开插柳村在城里安家落户。这年清明,两兄妹回村给母亲扫墓,打算把母亲的坟起走。黑牛瘸瘸拐拐地走出窝棚,拦下了他们:“不行。你娘说过,这辈子,她要在插柳村等你爹回来。”
“我们也一直在找爹。听人说,我爹越狱时好像头部中枪,可能想不起插柳村了。”念志说:“黑叔,那你跟我们走吧,我们会好好照顾你。”
“我不走,我要陪着他们。他们都是我的亲人。”腰身日渐佝偻的黑牛摇摇头,眯眼望着一座座由他修起的坟冢,目光最后落在了乔榛的墓碑上,幸福的笑意瞬间溢满了脸,像是在自言自语:“我也在等,等下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