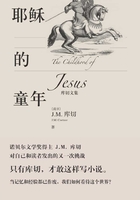某夜,睡得正香,忽被一阵婴儿的啼哭声,惊醒。我们这栋楼,没年轻夫妇啊,哪来的婴儿的哭声?寂静的夜晚,孩子的哭声特别响亮,细辨,似乎是从三楼飘下来的。第二天,三楼的大婶果然端着一盆红鸡蛋,挨家挨户散发。原来是大婶早年嫁出去的女儿,前不久终于生了个宝宝,回娘家休养来了。大婶一边派喜蛋,一边漾着笑脸,请邻居们多担待,孩子闹夜,吵着大家了。我们都真心地祝贺三楼大婶,荣升外婆了。此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们都是在婴儿的啼哭声中,入睡,做梦,醒来,下厨,吃饭,洗衣,出门上班。孩子嘹亮的啼哭声,成了我们这幢老式居民楼的原声伴奏。不隔音的墙壁,使孩子的哭声仿佛近在自己家。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么真切地听过婴儿的啼哭声了,一个新生命,在用哭声向这个世界宣告他的存在。我们都慢慢习惯了他的哭声,以致几个月后,当孩子和他的妈妈突然搬回自己的家,夜晚再也没有了孩子的啼哭声的时候,我的心骤然失落落的。筒子楼,忽然寂寞了。
几年之后,我终于搬离了筒子楼,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居,新居的墙壁很厚实,窗玻璃都是双层的,隔音效果特别好,关起门窗,几乎听不见室外的声音,自己家的声音,也不会传出去。我很快适应了这种安静的生活。偶尔,我会想起住过的筒子楼,以及从不同的邻居家传来的嘈杂声,那是一种让人心烦意乱,也让人无法忘却的声音。那是生活的原声。有时,我还会怀念这种声音,特别是当天突然落雨的时候,从不同楼层的阳台上,传来的呼喊邻居们收衣收被的声音。温暖的喊声如在眼前,提醒我们,不要被雨淋湿。
留给你一个明朗的空间
终于将自己的东西收拾整理好了,四五只纸盒子,塞得满满当当。它们安静地躺在墙角,等待着搬运工过来,将它们从这个办公室,搬到我的新办公室去。昨天还整洁有序的办公室,现在变得肮脏,混乱,惨不忍睹,跟电影里的逃亡镜头似的,到处散乱着纸片,文件袋,坏掉的笔,用过的本子,灰尘,烟蒂,甚至还有一双臭鞋。乱糟糟的垃圾里,混杂着我的气息。
这几天,办公楼乱成了一锅粥,因为各部室人员进行了大调整,大家都在忙着挪窝,从一个办公室,挪到另一个办公室。
这也是我第N次换办公室,我的新办公室换到了楼上。我拎着脸盆、扫把和抹布,准备先去新办公室看看,有没有腾空,再好好收拾打扫一下。每次搬办公室,最累的活就是收拾新办公室,将一个又脏又乱,堆满垃圾的办公室整理干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刚刚腾空的办公室,永远堆满垃圾,乱七八糟。
找到了我的新办公室。门开着。
奇怪,怎么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片垃圾,地面还拖过,湿漉漉的。显然有人刚刚收拾过。难道我走错了,这不是我的新办公室?回头又看了看门牌号,没错,正是我即将搬入的新办公室啊。
正纳闷着,有人拎着拖把进来了。我认得他,是工会的老章,去年刚从另一家报社调过来的。这间办公室,以前就是他的。
我看着他,问:“你搬好了吧?”
老章点点头,“是的,我的东西都已经搬到新办公室了。”说着,弯腰拖起地来。
“那你,这是……?”我疑惑地看着他,都搬走了,还拖地干什么?
他直起腰,说:“你是要搬到这间办公室吧?我这就收拾好了,等地面干了,你就可以直接搬进来了。”
原来是这样啊。这太出乎我的意外了,搬了这么多次办公室,还是第一次有人在腾空办公室后,将即将属于别人的办公室,收拾干净的。
我连声道谢。
老章摆摆手,“都是同事嘛,举手之劳,应该的。”老章把我拉过去,告诉我,办公桌应该怎么放,才能照到阳光,又不刺眼;电话搁哪儿,接起来方便;哪个插座能用,哪个是坏的……都一一交代清楚。
我用力点着头。冬日下午的阳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落在我和老章之间,那是温暖的橙色。
告别老章,我拎着脸盆、扫把和抹布,又回到了我原来的办公室。望着满地的垃圾,我卷起衣袖,打扫起来。
有人拎着脸盆、扫把和抹布,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他是这个办公室的新主人。看到我在忙碌,他诧异地看着我,我笑着对他说,回去吧,打扫干净你现在的办公室。
走廊里,都是忙碌的身影。
每次搬办公室,我们都是忙着打扫别人用过的办公室,替别人清扫垃圾。这一次,我们和老章一样,把办公室打扫干净,留一个干净、整洁、明朗的空间,给别人,也把自己美好的一面,留给他人。而我们要搬进的新办公室,则是别人留个我们的,一个同样干净、整洁、明朗的空间。
只是顺序稍稍变一下,感觉就完全不同了。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我们完成了一次温暖的传递。
门口的鞋子
妻子打电话说,下午就能到家了。
妻子出差半个多月,又赶上连续阴雨了一个多星期,没人收拾的家里,又脏又乱。不能让她看到,她不在家的日子,我的生活是多么糟糕。对,找个钟点工,来帮我突击收拾一下,这样,她一跨进家门,就能看见一个整洁温馨的家了。
外面的雨,哗哗下着,一点没有停下的意思。我打了把伞,出门。
我家附近就有一个小中介所。
天气好的时候,中介所总是很热闹,很多人挤在这里,找事情做。今天却没几个人。我向店老板说明来意,找一个钟点工,临时打扫收拾一下家。店老板指了指坐在门口的一个人,就她吧,行吗?我看看,是个中年妇女,面熟,想起来了,这不是经常在我们小区门口摆摊擦鞋的大姐吗?她不好意思地笑笑,说,连续下了这么多天雨,也没人擦鞋,闲得慌,而且,坐吃山空也吃不消啊,于是,就来找点活干。
原来是这样。我问她,帮我收拾下家,50元,可以吗?她的双手交错在一起,连连点着头,“好啊,好啊,真谢谢你了,大兄弟。”
带她回家。进门的时候,正犹豫给她哪双拖鞋换,她从口袋里掏出两只鞋套,弯腰套在了鞋上。我看看她,有点尴尬地笑笑,告诉她,主要是搞搞卫生,特别是厨房和卫生间,脏得不成样子了。
她利索地卷起了袖子。
交代完要干的活,我就坐到书桌前,打开电脑,继续我的写作。
屋外,不时传来水池里哗啦啦的水声,钟点工轻轻而快捷的脚步声……
窗外的雨,还在断断续续地下着。连续的阴雨天,让人的心情都变得灰蒙蒙湿漉漉的。
突然,手机响了起来。是妻子,她告诉我,火车快进站了,让我开车去接她一下。
走出书房,看见钟点工正跪在客厅的茶几旁,擦地板。
她还没有收拾好,怎么办?我犹疑了一下,对她说,我要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我故意将“马上”说得重一点。虽然我家里并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但说实话,我还是有点不放心,让她一个人呆在我家。
她直起腰,“那你早点回啊,我快好了。”
顺利地接到了妻子。本来想给她一个惊喜,现在只能实话告诉她了:家里很脏乱,我请了个钟点工,把家收拾一下,估计我们回家,她该收拾好了。
妻子惊愕地瞪着我,你让钟点工一个人留在咱们家里了?
我明白妻子的意思。我解释说,钟点工就是我们小区门口擦鞋的那个妇女,应该没关系的。
那也不安全啊,赶紧回家!妻子把行李往车上一扔,快!
我不禁也有点担心起来。
飞快地开车回家。到了家门口,听听,房里没有任何动静。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有点哆嗦地打开门。她正蹲在门口的玄关处。
她抬起头,手里拿着一只皮鞋。她说,家已经收拾好了,看见门口这几双鞋,都有点脏了,就帮着擦一下。
玄关的地毯上,一溜摆着几双擦得锃亮的皮鞋,有我的,也有妻子的。
我和妻子面面相觑。
送钟点工走的时候,我递给她60元钱,另外10元,算是擦鞋的钱。她执意退回了10元,说,今天我是做钟点工,所以,我只能收你一份钱。
雨还在下。我的心情,像门口干净的鞋子一样,亮堂。
瞄准
他躬着腰,低着头,蹑手蹑脚,向芦苇深处走去。
风从江边吹来,干枯的芦苇沙沙作响。虽然已是隆冬了,但是阳光还是将大地烘得暖融融的。气候变暖了,连南迁的候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飞到这儿也停下了,不再往南飞。而以前,这里只是他们迁徙过程中的一个休息站。现在,这片湿地,成了众多从北方飞来的鸟儿的越冬地。
除了轻微的风声,空气中四处都是翅膀的振动声,他熟悉这些声音,清脆,干净,温暖,像丝绸从指间划过的声音。他是这一带有名的猎手,空中的鸟儿,即使飞得再高,也难逃他锐利的眼睛,以及百发百中的猎枪。子弹呼啸而出,天空中旋即有一只黑影,孤独地应声而落。从无意外。
他找到一块稍高一点的干地,蹲伏下来。
望过去,不远处就是江涂,鸟儿们此刻都在那儿戏水,觅食,打盹,或者互相梳理羽毛。午后的阳光,将江涂之上的鸟儿们,晒得暖洋洋。
他的目光,在鸟堆里梭巡。
最多的是野鸭,好看的绿头鸭,调皮的翘鼻麻鸭,贪吃的斑嘴鸭,还有叫声响亮的瑟嘴鸭,他认得他们,就像熟悉的邻居。此外,还有几只大雁,悠闲地踱着方步,甚至还有几只色彩斑斓的黄鹂鸟。他的目光从他们身上掠过。这些,都不是他今天的目标。
他继续在江涂上搜寻。它们应该就在这儿啊。
突然,他的眼睛一亮。在一撮芦苇边,他看到了几个细细高高的身影,没错,就是它们。热血一下子涌了上来。
他揉揉眼睛,确认就是它们。一二三,四,对,果然是四只,他们告诉他,总共四只。它们埋头在江涂上觅食,对他浑然不觉。他一只只看过去,真是太美了,身上是白色的羽毛,翅膀却是黑色的,展开来,就像一幅黑白水墨画,而细长的脚,则像高挑的舞者,性感,美艳。没错,就是它们,东方白鹳,整个地球上不足3千只,它们比白金还珍贵啊。
他将目光,缓缓地从它们身上收回。熟练地从背上卸下猎枪,擦擦枪管,推上子弹,然后,装上消音器。他以前从不用消音器,为了这次行动,他特地请朋友定做的。
他端起猎枪,瞄准。
十字准星,从江涂上划过。一只鸟,又一只鸟。准星所及,无不打了个寒战,似乎它们能够感受到来自芦苇从中的枪管冷冰冰的力量。
枪口在那群东方白鹳的身上,停了下来。
一只东方白鹳,又一只东方白鹳。他犹豫着,不知道瞄准哪一只。最后,他的目光和枪口,同时落在了最后一只东方白鹳身上,它一会低头觅食,一会警觉地抬起头,它看起来比另外几只东方白鹳显得紧张。
他把枪口向空中抬抬,直指蓝天,那将是鸟儿振翅飞起来时的高度。这也是被他瞄准的鸟儿,最后能够飞起的高度。
做好了这一切,他长吸一口气,然后,拣起一块土疙瘩,向江涂上扔去。
鸟儿都惊恐地飞了起来。
东方白鹳也都惊恐地飞向空中。那只他瞄准的东方白鹳,也拼命地煽动翅膀,向前奔跑,企图飞起来。
它细长的腿上,缀着一件东西。这使它奔跑起来,很别扭,也很困难。他看清楚了,那是一只金属鸟夹。它的生命力可真强啊,被鸟夹夹上后,它竟然能够拖着鸟夹,逃开了。
在其他鸟儿惊慌的呼叫声中,它终于也飞了起来。高空,那才是它们自由的家园。他沉着地,缓缓地抬起枪,枪管移动的速度,与它向上升腾的速度,完美地一致。
另外三只东方白鹳在空中盘旋,等待着他们的伙伴。它吃力地努力飞向它们。
他再一次瞄准,然后,右手食指轻轻地、冷冷地扣动了扳机。
“砰——”消音器掩盖下的枪声,像一粒豆子,在炒锅里炸响。
子弹划破空气,如丝绸破裂。
突然,它一个趔趄。
打中了!
一个黑影,从半空坠落。正是那只金属鸟夹。子弹将鸟夹与东方白鹳的脚的连线,击断了。
东方白鹳,鸣叫着,向天空飞去。它的细长的双腿,有力振动的翅膀,在空中,划出优美的曲线。
他收起枪,仰视天空。多么蓝的天啊。
牵挂
妈妈拿起了话筒,犹豫了一会儿,又放下了。
儿子已经很多天没打电话回家了。
妈妈看了看客厅里的挂钟,早上六点半。如果在家里的话,这个时候,儿子一定还赖在床上。妈妈想,那就让他再多睡一会吧,他总是欠觉,年纪不大,都有眼袋了。
妈妈将儿子的房间收拾了一下。虽然儿子早不住在家里了,她还是习惯每天去整理一下。儿子小时候的照片就摆在书桌上,妈妈用手轻轻擦拭,怎么一眨眼,儿子就长那么高了呢?每次看到儿子这张照片,妈妈就觉得这是个奇迹。儿子的照片边上,就是电话,妈妈拿起了话筒,摁了几个号码,又放下了。这个时候,儿子应该正在上班的路上吧,如果他一边骑车,一边接电话,会很不安全的。
妈妈拎起菜蓝,去菜市场买菜,卖西红柿的大婶很热情地和她打招呼,妈妈买了几个西红柿,这是妈妈每天都买的蔬菜,因为儿子从小就喜欢吃西红柿,妈妈也喜欢上了。从菜场回来,路过电话亭的时候,妈妈忍不住看了一眼那部红色电话机,她当然不会这个时间给儿子打电话,儿子正在上班,也许在谈什么业务,或者被领导喊去谈话呢。妈妈笑笑,每次想起儿子,妈妈总是忍俊不禁。
吃过中饭,妈妈坐在沙发上,手又一次搭在了电话机上。儿子吃过饭了吗?他会不会午休一会儿?这孩子,从小就不肯午睡。也许现在工作累,他会休息一下,那么,这个时候打电话给他,会惊醒他的。妈妈想了想,将手从电话机上,抽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