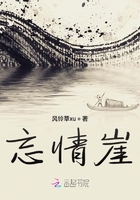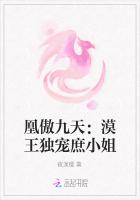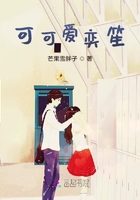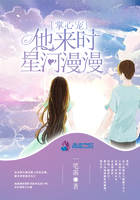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六年农历大年初一,我出生在甘肃灵台一个小的很不起眼的小平塬——寺底村。这是一个南北约8公里东西2公里长的山塬,与陕西的麟游为邻。黄土高原的特征是残塬沟壑,多少有点平坦的形态,人们不管它大小都叫塬。与平原相比只是一丁点儿的小平台。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那才叫平原呢。我们这里只能是西北黄土高原上黄土高坡走势形成的小平台。仅这点地理位置对于出门是沟壑,风吹石头牛羊遍山坡的黄土沟人来说,也是得天独厚的条件了。
我的先祖据说是从山西大槐树下过来的移民,繁衍生息不知多少代,无文字记载。仅有的历史见证是至今还生长着足以有5个壮汉合抱的古槐和古杨,我想这恐怕是先祖从山西移植的槐树和杨树吧。树作为先祖的影子永远扎根在寺底塬上。我的老屋就在这个古槐和古杨树底下。塬的另一个特征是正东崾岘处三面为沟,悬空成一个疙瘩台,台内有庙宇,陆续修补已逾千年。庙前有一辽阔地,南有土屋朝北。一木瓜树穿屋土壁长高有数丈,树身粗如面盆,枝粗如手指。木瓜官名文冠果,本是藤类,生在土崖边,一般高不过三尺,而这文冠果却巍然成树,如一棵槐树挺挺凌空独耸,在大西北实属罕见。因而这文冠果树和塬上的古树是寺底塬的历史见证,文冠果树因寺底塬而独有,寺底因文冠果而得名,文冠果长在疙瘩庙上,故寺底塬也叫“疙瘩塬”。
疙瘩塬南北两侧有山梁对称,直通沟底,把疙瘩庙凸起,这疙瘩如凤头,两侧山梁如凤翅,文冠果树似凤冠,塬为凤背,古树是凤尾,正如风水先生所言,此地丹凤朝阳,文脉十分旺盛。
其实,疙瘩塬上疙瘩庙的文冠果树是寺底塬实实在在的见证,庙内有一碑文:
大明永乐三年,岁次乙酉秋七月,白子岐竺模儿二人,因此山狐虫连鸣七日七夜,闻此,心凝议观未往,而反画地成方相戏,忽然,土块成泥、石粒生火,骇谓水火既济,即罢。戏登山行至模瓜树下,视有神卦一幅,讨询其事始知,南海观音原栖与斯,遂创修土殿一座,以作妥神之所,迄今百有余年,乃改修大殿三楹,创修伟陀殿一间,名其山曰:“慈土院”,恐其久而弗知,故泐石以藏记之。
经理人:张明坤 王彦章 左西岐 牛惠元同立
院 主:傅明山
时大明嘉靖元年,岁次壬午,季秋之月,敬泐
这是疙瘩塬如今留存的仅有的一块碑文,记载了修此庙的起因,从这段文字得知,木瓜树年代久远,已经巍然成树,后才有疙瘩上的庙宇,可见木瓜树至今生长近千年是有充足理由的,至于南海观音菩萨栖身于此修建庙宇,是一种天运人时的征兆,只能自圆其说。这棵近千年的木瓜树,作为一种生命形式,在寺底塬的疙瘩梁上干旱不惧,严寒不畏,至今绿叶常荫,年年岁岁花盛叶茂,果实丰盛。塬上是唐朝宰相、杰出文学家、政治家、诗人牛僧孺和大诗人牛峤的故居,至今古墓犹存,访者不绝。木瓜树造化不凡,文冠果实是杰出文人的化身,小小的疙瘩塬,竟然有如此旺盛的文脉流淌,可以说是山西大槐树老祖宗有识有胆,慧眼识宝地,耕云种月,生长五谷,繁衍后代,才能有彪炳青史的牛僧孺和牛峤。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话不假。几千年的大槐树和木瓜树,深深埋入这黄土里面,根深叶茂,与日月同辉,和天地共存。而人的生命有限,一代一代,人是树的化身,树是人的影子。我小时听先辈说,一棵大树有多少叶子,这个地方就有多少人,每片叶子和每个人一样,都有不同的身份和职业。其中叶子中最绿最大的那片经过春夏秋冬、风霜雨雪,以极旺盛的生命力不凋落的是文人的化身。这话虽则没有科学的论据,但冬季在树上可以零星地见到个别不落的叶子,这恐怕就是文人的化身吧。老树发新枝,一茬一茬,四季交替,年年岁岁,叶子落了又长,长了又落。我想老人这种朴素的论断还是能说明问题的。
我家老屋旁边有一棵最大最老的古杨,附近还有六棵古槐,共有七棵千年之久的大树。虽经岁月沧桑,历史变迁,后人采伐,风蚀雨凋,至今仍有一棵古槐和一棵古杨。我想这古树的叶子随着岁月和时间的推进,照老人的说法,不知要生长出多少个文人呢?我简直自豪的无以言说。
我从3岁时就殁了母亲,天生的命贱。当时正处在上世纪60年代,闹饥荒,没有奶吃的我也没有粮食吃,整天哭叫不止。古槐是我生命的摇篮,春天嫩黄嫩黄的槐芽,是我最好的食物,姐姐常常采摘煮熟给我吃,我不知吃了多少年,吃了多少叶子。那些叶子是生长将军、文人、贫民抑或乞丐?当时只是为了活命,吃饱就行,无须知道将来成什么。但是我很清楚,至今我的血脉里仍然流淌着树的叶汁。父亲兄妹10个,加上我姊妹5个,我是最小的一个,都是张口要吃要喝的。叔父嫌人多,我整天哭喊要吃东西,我一哭闹,就把我扔到门前那棵大槐树底下,要摔死我。奶奶和姐姐含着泪水不知多少次把我抱回喂养,我才得以活命。一直长到8岁,姐姐领我到村学里报了名开始上学。到12岁的时候,我能上初中了,因饥饿和营养不良,瘦小的我长得如猴子一样,常常得病。父亲是他兄弟中唯一有工作的,在寺底塬为邻的陕西麟游山里教书。他看我在姊妹5人中长得弱小,加之家境不好,就领我随他上学。
麟游遍地是山。杂草丛生的野山,是关中八百里秦川最西北处的深山,贫穷与荒凉,不如疙瘩塬。我上的高中是麟游县唯一的中学。这个县城在历史上很有名气,是隋唐皇帝的离宫,隋时叫“仁寿宫”,唐时叫“九成宫”,有“隋唐离宫之冠”的赞誉。老师讲课常常说到麟游当时的繁华景象如海市蜃楼。身居长安古都的帝王将相,不愿待在繁华的长安,太宗高宗皇帝常驾幸九成宫,而且春来冬往,几乎每幸都在半年以上,可见这里对皇帝的诱惑。唐朝宰相、著名的政治家魏征撰文对九成宫的空前盛况和贞观之治作了详尽的描述,此宫“冠山抗殿,绝壑为池,跨水架楹,分岩竦阙,高阁周建,长廊四起,栋宇胶葛,台榭参差。仰观则迢带百寻,下临则峥嵘千仞。珠璧交映,金碧相辉,照灼云霞,蔽亏日月……”是为《九成宫醴泉铭》。由此我们可以想到当年九成宫富丽堂皇的景象了。醴泉铭碑由唐代75岁高龄、杰出的大书法家欧阳询亲笔书写,成为中华民族书法艺术的经典之碑,是历代书家研习的名帖,历经千年的风雨沧桑,原貌依旧,完整无缺地保存着,成为国家重点保护的文物珍品。我读高中的时候,是这座“圣碑”的崇拜者。读古碑、制拓片,是我们业余时间最惬意的事情。回想起来,我对书法的爱好源于这座神圣的古碑,加之父亲有一手功夫极深的唐楷书法,所以父亲是我的书法启蒙老师,我的最初写字完全得益于九成宫碑的熏陶和父亲的教诲。高中阶段正是“文革”的后期,那时的知识贬值和匮乏是可想而知的。学工学农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必修课”,“最高指示”和“两报一刊”社论是我们的必读之物。由于贫穷和磨难,我的忧患意识使我小小心灵里产生了很多幻想,对于知识的渴求是我最大的满足。有一次我在整理父亲的陈书旧报时,无意间翻到了两本发黄的旧书,一本是《唐诗三百首》、一本是《古文观止》,翻着翻着,我被那精彩的篇章和优美的诗句陶醉了。那本《古文观止》被我翻得破烂不堪,是这些优美的诗文营造了我精神世界的家园,使我干枯的心灵得到了滋润。我的语文成绩一直是班上最好的,作文常常被语文老师讲评,张贴在校园的墙报专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