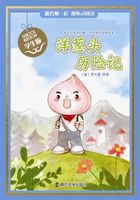一、十岁那年我病了,与妈妈沾点偏亲的林医生看了我的CT报告单后直截了当地说:“带孩子去省城检查一下吧,这个病灶不太好。”这句言简意赅的话,像一道魔力灵验的符咒,使原本幸福的三口之家顿时陷入昏天暗地的劫难中。几天下来妈妈丰满光泽的脸颊就变得消瘦黯淡,头发也像一团枯草无光泽。在此之前爱美的妈妈一直热衷减肥,每天不是跑步就是游泳,临睡觉前还得抽空晃一百个呼啦圈……反正浪费好多时间,浪费好多的钞票,减肥效果却不甚明显。那几天她瘦了,按理说应该高兴才对呀。相反的是,她从医院回来后饭也不做,衣服脏了也不洗,就是搂着我哭,伤心欲绝的样子;爸爸呢,倒没像妈妈那样凄凄切切,把电视音量调到最响,人却躲到阳台上一根接一根吸烟,呛得我直咳嗽。妈妈搂着我,一会儿摸摸我的脸,一会儿摸摸我的手,好像不认识我一样。实际上,我知道,她恨不能把全部的母爱倾注于一举一动中。我呢,索性随弯就弯,闭上眼睛一言不发,做出一副虚弱疲惫的样子。
去省城的车票买好了,全家各司其职,爸爸从市场买回一条当地特产——大马哈鱼,说是给省城的战友带的。妈妈去银行取了一大笔钱。最疼爱我的奶奶知道我的病情从乡下赶来,她哭了一夜,眼睛肿得像烂桃子一样。
出发那天,奶奶把我最爱玩的悠悠球放进包里,然后搂住我,不说一句话,只是汹涌地哗哗地流眼泪。奶奶越是这样,我越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难过和惶恐。但是第一次出远门的兴奋战胜了暂时的伤感。上了火车,我又跳又蹦,甚至给邻座阿姨唱了一首我最拿手的动画片《西游记》的片尾曲:“白龙马,蹄朝西……”在没来省城之前,我心目中最大的地方以为就是我居住的小城了。等下了火车后,仰头看那些摩天大楼,像要刺入云端时,我惊诧极了,也纳闷极了。楼房怎么能盖得那样高?比我家的二节楼高百倍。妈妈紧紧扯住我的手,我知道她怕我走丢了。我走丢过一次,那时我四岁,上海服装厂来我们这儿展览,人潮如流,妈妈看好一件衣服,就和货主讲价,好久未果。我实在无趣,就自己溜溜达达走出很远。直到回头时,瞥见身后尽是陌生的面孔,我慌了。但很快又安静下来,面不改色,心不跳,站在商场西出口。我想妈妈一定会来找我的。站了有一会儿,也不见她出现,一转身,看见身边有卖苞米花的,闻起来味道香甜,就说买一碗,妈妈在后边一会儿来付钱,于是我有滋有味地吃起苞米花来。当妈妈满头大汗找到我时,我吃下最后一粒苞米花,她毫不留情地把我揍一通。不过,我还是挺高兴,离开妈妈的管束,独自欣赏多姿多彩的世界,感觉很新奇,很美妙。其实正是这种不受束缚的好奇心,使得我在省城住院七天里认识了小小,并成为最好的朋友。
二、爸爸的战友王叔叔已在医院门口恭候多时,他远远地打招呼,走到近前,与爸爸握手、拥抱、寒暄。
因为有王叔叔特殊关照,看病手续简化许多,医生佟阿姨看了各种检查单子,说:“是一个小息肉,在手术室就可以搞定,准备手术吧。”
手术很顺利,我的病情不重,但需住院观察几天,我们在高档病房住下。爸爸说没大病是万幸,这回咱们享受一下。不管高档病房设施怎样豪华,住着如何舒服,我是一百个不喜欢。因为病房里总有一股难闻的来苏儿味,那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的味道,令人精神紧张的味道。所以我趁妈妈去卫生间的空档,揣上悠悠球,鼻腔里塞着白纱布条堂而皇之地跑出来。之所以这么果断跑出来,厌烦来苏味儿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我从窗户里看到楼下公园有丁香花在盛开,一嘟噜一嘟噜的紫色小花在风中荡啊荡,那么自由、惬意。我颠颠地在花园里撒欢儿,像只挣脱绳索的小狗。如果我沿着花园小路一直跑下去,在小路尽头摘几朵紫色的丁香花,然后回到病房,大概就不会结识小小,也不能有下面的故事……可是那天我着魔一样想独自走走,体验体验没有妈妈约束的天马行空。
我在公园草地上抓蝴蝶,捉螳螂,很是自在地折腾起来。可玩一会儿,就觉得没意思,真想找个玩伴。花园里除了那些沉默不语的花呀草呀,再就是穿着病号服来回散步的病人。很快,我就把搜寻的目光定格在丁香花丛——花丛后边的围墙居然有一个大窟窿。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侧耳听到有孩子玩闹的声音。我毫不犹豫钻过去,眼前是另一片天地:一排矮小而破败的房舍,院墙坍塌,门窗洞开,有几家门上涂着黑色的带圆圈的“拆”字。一群和我一般大的孩子们在进行悠悠球比赛,你不让我,我不让你的,谁也没有注意到我这个“墙外来客”。悠悠球!我最擅长的游戏,手心都有些痒了。不过在没完全掌握情况之前,我不会贸然加入他们队伍的,否则,输了多没面子!我沉稳地审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告诉你们吧,我的悠悠球玩得相当地道。悠悠球有几十种玩法,什么劲力旋风、瞬雷出击、横刀夺爱、冲上云霄、风起云涌等,而我最拿手的是劲力旋风,悠起来出神入化。我看了一会儿,心就有底了,他们的比赛没有章法,多是随意发挥,只要球不停下来,就能得到一阵嗷嗷的叫好声。摸清他们拙劣的玩技后,我决定向他们挑战!
“谁敢和我比悠悠球?”我底气十足,声音沉闷地说。我是想声音洪亮,可鼻子里塞着纱布条,没法洪亮。他们没把我这个小孩伢子放在眼里,继续嘻哈着。
我知道此时是我闪亮登场的时刻了。
我掏出悠悠球,双脚站定,摆好姿势,手一松,用腕力把悠悠球向下抛出,手保持水平,手掌向下,悠悠球便在绳头处不断转动,那个蓝色的悠悠球闪着诡谲的光晕,像一道划过暗夜的流星。这就是“劲力旋风”的魅力,是我最拿手的,靠它使我成为小伙伴们心目中的英雄。接下来几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彻底让他们停下手中的悠悠球。你猜对了,我是想给他们一个下马威,震震他们。
四五个小脑袋同时凑过来,把我围在中央:
“教教我吧!”一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毛头小孩用崇拜的口吻央求我。
有几个小孩干脆管我叫起了师傅,我也就厚着脸皮答应了。
“嗨!你会新月漫游吗?”一个头皮剃得发青的光头小子站在人群外,拖着两挂脏兮兮的白鼻涕,似乎不服气。
我没回答他,轻蔑看他一眼,手一摆,崇拜者们赶紧退后几步,为我腾出更大的空间。我提提裤子,胡乱塞塞鼻子里快掉下来的纱布条,于是一场精彩的悠悠球表演开始了。我飘得很卖力气,他们毫不吝啬地把掌声给了我。这时,我得意得几乎忘形,全然不知身后有一双嫉妒的眼睛盯着我。一时间的交口称赞,让我兴奋得晕了头脑。我从那些崇拜的目光中体会到巨大的成就感,便言传身教起来,而且毫不保留。他们支棱耳朵认真地听。我这个爱臭显的毛病,像我爸。我妈总说,我就是我爸小一号的翻版。就在我口若悬河地给他们白话时,那双暗中嫉妒的眼睛喷火了。他悄悄接近我,猛地从我手中抢下悠悠球,走了。注意!我这里用的是“走”而不是“跑”,可见抢球人何其猖狂。那些先前俯首帖耳的崇拜者,这会儿一反常态起哄:“抢东西了!”
师傅被抢,徒弟们跟着起哄,一群狼心狗肺的家伙!在徒弟面前不能丢面子,我全然不顾那小子比我高半个脑袋,咬牙切齿地去追。光头小子大步流星顺路往前走,走到半路,好像还弯腰摘了一朵蒲公英花闻闻。我追上他,理直气壮地扯住他的后衣襟,希望他把悠悠球还我。谁知他稳稳站住,一脚横扫过来,我“妈呀”一声重重跌个仰巴叉,鼻子磕在尖利的石块上,顿时血流如注。我捂着鼻子,杀猪般地嚎叫着。他也吓坏了,扔下悠悠球,猫着小腰跑了,边跑边说:“看你还敢不敢显摆了。”我这才明白,原来太张扬了不是什么好事,总会惹人妒嫉。徒弟们见势不妙,一哄而散。我哭了一会儿,看没人理就自己爬起来。我向来都这样,面子比疼痛重要。
“鼻子还在流血,擦擦吧!”一个戴红纱巾、个头比我猛些的女孩递给我一卷纸巾。她的脸被纱巾罩着,五官看不清,给人一种神神秘秘的感觉。
我接过女孩递给我的纸巾,背过身去擦净鼻血。因为我不乐意让一个女孩子看到眼泪和狼狈。
“谢谢你!”我大方地向她伸出手。我看爸爸和王叔叔见面就是这样握手。可是她没有伸出手,反而咯咯笑着跑开了,红纱巾跃跃地飘着,像一团燃烧的火焰。
三、妈妈一路喊我的名字找到我,我的狼狈相确实把妈妈吓蒙了。她捧着我的脸,像捧着一件宝贝,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细致检查,见并无重伤才放心。接下来她教训我,说我不省心,总让她操心,可乱跑啥呀,人生地不熟的。再接下来,她还说什么,我一点也听不下去,因为我对刚才那个戴红纱巾的女孩充满好奇。其实戴纱巾没啥奇怪,我也戴过,在刮大风的时候,妈妈怕我迷眼睛就用一条柔软的纱巾将我头包上。躲在朦胧的纱巾里看外面感觉很奇妙,树啊房子啊车辆啊,全都变成淡淡的红色,给人一派温暖的感觉。难道她也怕迷眼睛?不对,今天天气很好,一丝风也没有。那么只能说她爱美,是个爱臭美的女孩,像我同桌李当当,长相平平,却总逼我喊她美女。
第二天我打完针,实在无聊,脸贴在病房的玻璃上看天。天气不算晴好,有风,几片云彩黑膏药一样贴在空中,两只一大一小的白鸽从对面楼顶不厌其烦地飞起又落下,好像母鸽在教幼鸽试飞。窗户下那几株矮小的丁香树,开得正旺,这边一丛,白的;那边一丛,紫的;中间一丛,粉的,一群小蜜蜂就眼花了,不知落在哪朵花上采蜜了,只是嗡嗡地飞上飞下,像要开会商讨一番,于是这片小天地就变得热火朝天,充满了生机。我急了,也想出去,可是妈妈不让,她怕我再遇上昨天那个光头小子。是的,我不想再遇上他,我想遇上红纱巾女孩,想看看红纱巾后面那张脸。人就是这样,越是想不为人知的东西,越是想看个究竟。忽地,太阳像个技艺高超的魔术师,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抖开万条金丝,再看黑云早已无踪影了。金丝遍地流淌开来,满视野像抹了一层鲜润的蜂蜜。丁香浓郁的芬芳招来几只我叫不出名的鸟儿,它们落在枝条上,枝条就富有节奏地微微颤动。鸟儿的胆子极小,有一点儿动静就“突”地逃了。可是用不多久,还会再回来,而且认准要落在先前那丛枝条上。我实在按捺不住了,趁妈妈不在病房的机会,我又跑出来。跑出来做什么?目的很明确,我还想见到戴红纱巾的女孩。
我轻车熟路地钻出围墙窟窿。在一座破房子前,有一抹红色特别显眼,那红色似乎有强大的吸引力,我想也没想就“啪嗒”“啪嗒”地跑了过去。是戴红纱巾的女孩,她蹲在地上看书。离她不远的凳子上坐着一个老奶奶,似乎睡着了,头垂着,阳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那头发就显得更白了。女孩真是个怪人,为什么总戴着红纱巾?
她认出了是我,却没有站起来,虽然戴着纱巾,但我能感到她快速在我脸上扫了两眼。我知道她是担心我的鼻子。今天是周一,昨天在这里玩闹的孩子都上学了,这里很安静,缺少人语的地方,总是荒凉的。几座没来得及拆迁的老房子破破烂烂、无精打采地立着,像一个迟暮老人,丧失了活力和斗志。房子与房子之间的电线东拉西扯,蜘蛛网一样交织,有几根电线已经老化,外皮破损露出里面锃亮的铜线。几棵柳树不甘寂寞地在风中摆着不算稠密的枝条,似乎向天上飞过不肯落下来的小鸟呼喊,停下吧,歇一会儿。小鸟呢,不领情,呼啦啦地往更高的天上飞去。看来在这儿居住的人们大部分都搬走了,只有红纱巾女孩一家和其他几户人家还在这里坚持着。
红纱巾女孩见我来,表现并不是很热情,继续低头翻书。嘿,小女生面皮薄,这我知道。于是,我主动跟她套近乎,挨着她身边蹲下来,明知故问:“看书呢?”女孩用鼻子哼了一声:“嗯。”那是一本彩页的《唐诗三百首》,不是很新,书脊下面已经开裂,可能里面有掉页的,她翻开那页已经缺了一半。《唐诗三百首》我在五岁的时候就全会背,而且一字不差,现在我已经十岁了,早就对它不感兴趣了。在我六岁半那年,也就是上幼儿园大班那年,我爸就从书店给我捧回了十几本厚如砖头的世界名著让我读。
见我半天不吭一声,她清清嗓子,似乎要向我显摆什么,开始照书念:“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诗在我刚会说话时就会读了,她这么大了才会读,真是可笑!我不由“嗤”了一声,像皮球漏气了似的。我笑话她是有理由的,不是空穴来风,她读错一个字,把xiàng读成了jìng,却还不知道,仍是念得很投入,脖子一伸一缩,一副陶醉的样子。
“那个字不念jìng(应为三声)!”我不客气地纠正道。
她理直气壮地说:“我奶奶说念jìng,就念jìng!”看,她还辩解,对我主动为她纠正错误好像不屑。
“哈哈……”我夸张地大笑起来,鼻子一抽一抽的,还故意把声音抬高,显出一种高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