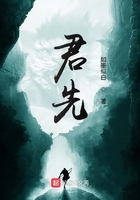“慢着——”
曹安康刚要走,白太后却又叫住他:“昨日命你去办的事如何了?”
曹安康略一反应便明白过来,忙回身禀报道:“回太后娘娘,国公他老人家方才已从西圣门入宫,正如娘娘所料,老人家诸事皆已心淡,却只对一件念念不忘,一听那位的消息,便赶不及地来了。若是不出差错,这会儿想必已与那位……”
大约是觉得这个称呼有些不妥,曹安康又改了口道:“……与那位神医见着了面。探子来报,始终不见太医入宫为皇上诊治,那位神医一旦被阻住去路,恐怕清心殿内更不好了……”
曹安康说着,低下了头去,言语间也不敢有喜怒。
清心殿里的圣上毕竟是太后的亲骨肉,夺宫之举还是要等太后首肯,若身为母亲的太后娘娘心一软收回了懿旨,先前对承亲王的许诺便也就随风而散了。
白太后的眸光始终暗沉,静默了一瞬,只若有所思地“嗯”了一声。
未曾收回成命。
“奴才这便去了。承亲王那边儿怕是等急了。”曹安康看懂眼色地退了下去。
太后对陛下已全然失望,哪怕他身负重伤命不久矣,太后所要做的并非以母亲的名义亲自前去探望,而是命她的心腹带上淬毒的兵器,将其斩杀在龙座之上!
此时形势显而易见,清心殿内那两位可谓孤掌难鸣,既无兵力增援,又无神医诊治。与母族作对的下场,今时今日才能叫皇上看个明白!
四月的长安城,这一****光大盛,晨曦中迎来了封后大典,自宫中流传出来的消息称那位皇后已怀有龙嗣,百姓们更是奔走相告雀跃欢腾,大帝的喜事便是大秦百姓的喜事。
然而,日光照在巍峨的秦宫之上,这上百年的偌大宫城却沉浸在肃穆冷清之中,仿佛那些雕梁画栋和姹紫嫣红,随时会来一场兵变或宫廷内斗,令原本风生水起的帝王或枭雄永远止步于史册的某一页。
距离龙华殿不远处的长廊内,北郡药王被人堵在了转角处。
那人的陡然出现逼得北郡药王骤然停下了脚步——须发皆白,面容苍老,是已过古稀的年纪,着一身华贵便服,负手而立,自有一股身居高位者的凛然姿态。目光矍铄,直视白苍。
放眼长安城乃至偌大的九州大地,能让白苍止步不前之人,除了清心殿里那位年轻的皇后,唯有眼前这位老人。
惯常冷漠不问对错的白苍一句话也说不出,竟将目光移开,无法再与老人对视。
“发誓永生不再回长安,为何又回来?”对面的老人倒先开了口,语气却并无质问,只余悲凉,“既然回来,为何连家门也不入?老大,为父尚未入土,你却早已替自己立下衣冠冢,那座孤坟在为父的心里埋了十八年。连父母兄弟家族都能放弃,你今日回来,又是为了什么?”
白国公白邕,膝下三子一女,本应个个皆是大秦扛鼎人物,谁曾想年过古稀,却已儿孙散尽风雨飘摇,怎能不悲从中来?
最优秀的长子、白家原本的继承人,二十余载的养育之恩,只以一座衣冠冢给了世人交代,如何能令老父释怀?
白苍仍低着头,无法从十八载的生疏中回过神来,他可以在几位阁老面前装作陌生人,可在面对父亲时,到底有些无法伪装。
“父亲……”白苍开口,轻描淡写,“我欠了两条人命……”
“那是你三弟的妻儿,要恨该是他去恨,他恨了十八载不认白家,可人人却都知晓他是白岳大元帅,仍姓白,仍是白家的人。可你却将名姓都抛却,十八年无音讯,连你母亲去世也不曾上过一炷香。有什么恨忘不掉,比离家去国还要沉痛?连亲恩家族也要背弃?若非今日为父赶来与你相见,是否等为父入土,你也不肯归来瞧上一眼?”白国公字字血泪,俱是年迈之人的沉痛。
白苍无话可说。
一瞬间,眼前浮现出那个女孩纯净灵动的眼眸,笃定地对他说,等我五年,我会治好你的病,五年时间,我会为你化一只幻蝶。
五年方至,他不辞而别,离开了鸣山。她下山寻他,眼见他的冷漠躲避,却无半点纠缠。
晏氏族人坦荡而认命,她依旧纯净的眼眸似积了千堆雪,捧着幻蝶给他,唇边染笑,声音清澈:“我来并非强求你和我一起回鸣山,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会撒泼放肆。我只是来给你送一样东西,一样五年前答应了要送给你的东西。幻蝶,晏氏少主人的灵气所化,有解百毒之功效,故而你所瞧见的晏氏卷轴中记载,晏氏少主人有起死回生之力。你的寒毒,可以解了。”
不谙世事的少女,出鸣山只为给他送灵力所化的幻蝶,她甚至坦率地说既然和他成不了一对,她会遵从族中的安排与晏氏雪狼一族的继承人成婚。世事繁华,并不一定比晏氏更重要,喜欢的方式有很多种,她对他的这种也是喜欢,以幻蝶为证。
然而,她终究没能再回去,一出鸣山,什么都由不得他们,他肮脏的家族血统和卑劣本性,以阴毒的“取次花丛”设计她怀上了白岳的孩子,设计她和她的孩子最终死于非命。
幻蝶还活着,触碰时似还温热,可那个女孩遭剖腹而死,胎儿夭折腹中,她空洞而绝望的双目是他漫长岁月里久久不散的噩梦。那一年,晏染刚满二十岁。
白苍的双目忽然红了,年纪一大,连落泪都可耻,他摇头,声音嘶哑浑浊:“我过不了自己的坎,一辈子过不了,尽管我杀人如麻,为白家做尽刽子手之能事,可我过不去她的坎……”
“她已经死了,躺在冰冷的地下十七载又八月,白苍自那日起也已死了。父亲,你只当我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做了白家的逆子,做了大秦的叛臣,我绝不会再回去!”白苍被逼出了绝望,这绝望自十八年前始,****夜夜痛心切骨地啃噬着他。
话音刚落,宫墙上方忽有几只寒鸦扑棱棱飞起,似受了惊吓般凄惶地叫了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