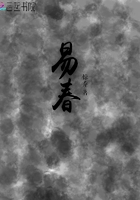一日,柳上元下楼买菜,难得下一次厨,想为自己做点好吃的,刚下楼没走几步远,听到身后有人叫他,他纳闷,在这个小区几乎没人认识他呀,谁在叫他?他转回头,一看,是胖胖的丁燕。丁燕一看到他,急忙迎上去寒暄温暖。看样子她已经知道柳上元致富有成的事了,要不然,何至于前倨后恭,之前不是还讽刺他缺心眼吗?现在不好意思说了。
正想着,果然丁燕就开口了:“柳上元啊,之前的事你也别计较,是我不对,几年前对你的态度不好,别放心上啊。你想想中学那会儿,放学回家的路上,我还骑自行车载过你,对吧?以后都是邻居了,和平共处啊,老同学。”柳上元心想,再怎么样,我也不能跟一个女人较劲吧,于是,和颜悦色地说:“丁燕啊,当时你说什么了?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了?”
丁燕于是笑的更大声了:“你不记得就好,当我什么也没说。从此,咱们就是好邻居了。哎,你住哪?改天去你那里做客,我住五号楼三单元,是租的房,我就在附近上班,不像你啊,大老板,能买得起房。”柳上元讪笑着谦虚着,别过丁燕。
丁燕还真是说来就来,没几天,就来拜访柳上元了。柳上元赶忙招呼,沏好香茶,摆好果盘,就等着她开口唠嗑了。丁燕一如既往地开玩笑,只是在玩笑的间隙她很想知道柳上元何以就“一夜暴富”了呢?在她还默默地租房子,进入体制内工作,月入四千元,在别人看来已经羡慕地了不得的时候,她却不满意了。
她开始眼红起柳上元的这点成绩了,一个上学时学习不怎么样,结交一群狐朋狗友,吊儿郎当的人,怎么就坐上大众车,住上公寓楼了?这才毕业三年而已啊!哎,没办法,有些人就是命好。她望着柳上元微微笑着的脸,却只是羡慕他的命好,他自然不会告诉丁燕他在这几年里经历了怎样的情感波折和努力奋斗的日子。
他每天陪客户喝酒到深夜,回到家狂吐不止,有时候甚至回不了家,直接从楼上滚下来,小腿骨折,住院住了几个月,才得到领导带着歉意的欣赏,从而事业飞升。他的事业不都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吗?没有努力,没有拼死的决心和勇气,谁人可以轻而易举地走向成功?所谓成功,也不过是在正确的道路上拼了老命地摸爬滚打,一次次摔跤又一次次爬起来前行,坚持到最后罢了。
之后,丁燕再问什么,柳上元已记不起来了。中间,她似乎故意吊他胃口,随口说了几句关于师圆的话,柳上元本来想继续问,可是想到丁燕上一次已经鄙视过她了,不能再让她小看自己,因此,还是不要多说为妙,就当自己没听见。丁燕一看柳上元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心想他可能已经不想师圆了吧,这下正好,也就没必要瞎担心了。
本来,她说那些话也只为了试探一下他的态度,这一点柳上元早就料到了。都是同学,也不好说破。等到下次丁燕再来的时候,柳上元表面上依然客客气气,可心里却有点厌烦她了。她的话题永远是上学时的那点破事,要不就是单位里的鸡毛蒜皮又勾心斗角闹得不可开交的秘闻,那一群看似特别正经实则无聊透顶的人整天在想什么呢?他们的世界真的很复杂,柳上元琢磨不透。
有时候,柳上元实在不想听她的啰嗦,就直接给她讲一些特别重口的恐怖的新闻或是信息,或者故意向她吹嘘一些不合常理的个人发家史,翻来覆去的,每次聊都是这些内容,丁燕也听烦了,那就正好可以不用再说了。柳上元终于达到了他的目的。丁燕自此少有登门拜访,他的世界又恢复了平静。想来,丁燕也只是他这段生活中的一味调剂吧。
日子就这样平凡而过。又过去四年了,柳上元事业上蒸蒸日上,张雨婵和梁画可的画廊经营地红红火火,赵亮吉和爱人在本市开了一家音乐兴趣班,收益可观。李维舟和曹煌合力开了一家健身房,生意有旺季有淡季,好在他们齐心协力,正在一步步地把健身理念推广开来。都是好兆头啊!在第五年的新年来临之际,大家都沉浸在新年所带来的愉悦氛围中。人人都期望在年关时着力做好自己的手头工作,争取对新年有一个完满的交代。
开着车,开到一家茶楼边上,柳上元和他的好哥们一起约好下午茶。这是难得的时光,趁着腊月二十三小年之际,出来坐坐,多美妙的午后啊!柳上元总是不知不觉地回想起若干年前,他和她刚开始初恋的那个新年,他们一起在公园看雪,在元宵夜猜灯谜,看庙会上的杂技表演。。如今,一去不复返了。
都是过眼云烟了,好漫长的十几年啊。他等啊等,可惜终究不如意。这期间,李维舟和曹煌没少给他安排相亲,然而他已经厌倦了这种方式,即使姑娘长得多漂亮,他都视为无物。几次三番,他们的热情被打断了,最近到没有给他介绍对象了。但是见了面,依然口不饶人地骂他,都多大年纪了,还不结婚生孩子?你爸你妈怎么劝你的,哎!柳上元固执起来,他们是知道的,任谁劝也不行。
眼看奔三了,新年过后的第一个元宵节就是三十岁的人了,三十而立,古人都早已给自己划定了目标,先成家后立业,家庭稳定了,男人似乎更增加了在外拼搏的勇气。然而现代人并不这么想,尤其是男人,社会给她们的压力太大了,大到买不起房子便不能结婚的危险地步,居然房子是丈母娘的刚性需求,因此一波又一波的男人们不得不为了房子而前赴后继地努力进取。
尤其是现代都市青年人的婚恋观都变成了先立业后成家,只有自己事业稳定,有足够能力给另一半幸福生活的前提下,他们才会想到结婚,这是时代赋予人的思维模式。
柳上元又何尝不急!大龄青年的头衔一旦加身,仿佛全世界都会躲着你,他们的眼神足以杀死他几百次了。他也积极尝试同各种风格的姑娘相处,最终却都不欢而散。他不知道自己想找什么样的伴侣,他甚至不懂得如何谈恋爱,生命中对贪恋的激情被浇灭之后,他就显得手足无措,那种被人抛弃的感觉他还记忆犹新,他自此知道了自己的恋爱方式是错的,无论付出了多大的时间和精力,最后都证明是错的,他后悔不已,后悔自己强摘不属于自己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到头来结果是这么可悲。
他又有点庆幸自己的付出,尽管失败,那也是他青春年华里最美的日子,那些傻到不行的时光,那些只属于他一人,那些只能在静静的午后品味又嘴角拂笑的小故事,成了他繁忙工作中的一杯精神咖啡。
十年,总是一个可以纪念的年份。听着陈奕迅的《十年》,柳上元有所触动。这一年的春节,为了庆祝而立之年,大家又风风火火地组织了同学会,男男女女奏出了家庭,加入了新年狂欢的派对。柳上元和好兄弟们自然不甘落后,举杯交盏,谈论时事,好不快意。只是,还没有见到他想见的身影。同一个城市,只是一南一北,却可以几年不碰面,想来,真是咫尺天涯。人心如果远了,对面即是天涯。惆怅中带着落寞,寂寂睡去。
第二天一早,头晕中带着眼浊,柳上元还是挣扎着洗把脸吃妈妈做好的早餐。新年里,要多陪陪父母尽孝心。吃完饭,还是要出去逛一会儿,这样脑子更容易清醒。走着走着,竟然走到了一个游乐场附近,他停下脚步,蓦然看到了前方有一个似曾相识的背影抱着一个孩子。难道真的是她?不可能吧,这么巧?昨天晚上心里还想着为什么几次的同学聚会她都不去,转眼她就出现了,还抱着孩子?他心想,无论如何,喊一声,如果是她,见个面说句话也无妨啊。
柳上元在心里鼓足了八百个勇气,走上前叫她:“林师圆。”师圆轻轻回过头,一看是他,满脸的惊讶,微微一笑说:“是你啊,好久不见。”“是啊,好久不见,你最近好吗?”师圆幽幽地说道:“有什么好不好的,目前就在家带孩子呗。”柳上元看到她的两鬓似乎有了一些皱纹,身材也有所发福,夸张一点,简直比学生时期胖了两圈。皮肤没有以前湿润了,头发也不那么整齐了,衣服上有小孩的脚印,孩子在地上一闹,立即抱过来,左右晃着哄着,这姿态跟十几年前的那个小姑娘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柳上元就这样静静地观察着她的每一个动作,感觉心里的那个人早已远去了,再也不会出现了。他的梦就此破灭了。柳上元怔怔地站在那里,师圆的孩子闹着要回家,她同他道别,然而他并没有听见,只是看她远远地走开了。假如他是跟她一起生活到现在,那么她的变化是可以被他在日常的点滴中融化、感知并接受的,但事实上并没有。他忽然感觉自己一点也不喜欢她了,以前对她的诸多思念居然顷刻间烟消云散,理想总是会被现实打败的。
多么漫长的岁月呀,断断续续又十几年了吧。虽然不是非她不娶,但是心里总是难以放下,从初中一年级见到她到现在,确切算来,已经有十六年了,这全都属于暗恋吗?他也说不清楚。不过,现在事实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一切都过去了,风淡云轻的帷幕即将打开。
原来,人都是会变的,之前想的有多好,等到真的见了面,发现也不过如此云云。之前在脑海里过滤过无数遍相逢的场景,其实,真的面对面,却是千言万语只能无语。有些事,有些人,见过了也就见过了,没有话要说,能说出来的全都是多余的。柳上元这才明白,这就是人世间一个非常普遍又非常怪异的定律。你所想象的跟你见到的全完是两回事。喜好幻想本没有错,错的是总渴望着把幻想变成现实,或者把预想的幻境在现实中重新演过一遍,怎么可能呢?来不及彩排,来不及预演,而那个人也终难体会到你的心境,难以配合你的表演,他或她只能在自己设想的情境里生活,于是感觉越走越远,越来越虚无。只剩下青春的尾巴在摇晃,终于走到了散场的时刻。
柳上元闷着头,无声无息地走回家,想尽快躺到床上再睡个回笼觉。梦中,他又一次看到了那一树茂盛的荼蘼,长长的枝条垂到地上,枝上怒放着无比灿烂的小白花,照亮了蓝天,照醒了绿地,也照进了一颗枯寂已久的心。。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