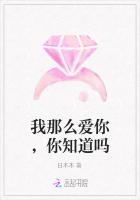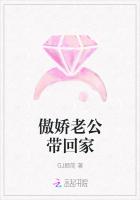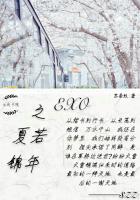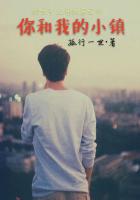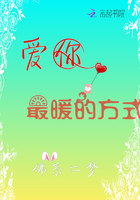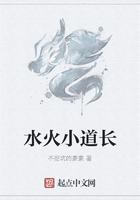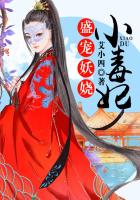那是多么有力、温暖而柔和的手。小迪妈妈眨眨眼睛,也有力地回握了朱德之的手。已经许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小迪妈妈从心里冒出这种念头:那是一种棋逢对手,高处过招,不言而愉的喜悦。
看到他俩握手,TONY稳步迎了上来。
朱德之大手一挥,对TONY说,“都上车,先送他们回酒店。”
(接上)
第二十三节
周日的早上,小迪醒得很早。她的卧室笼罩在紫色的晨光中。窗帘是紫色的,床边的帷幔是紫色的,衣柜的门是紫色的。而周遭的紫色并没有让人觉得压抑。
窗帘的亮紫上加了一层暗纱,如果把纱束起,那么就是明亮的紫色;如果放下,亮紫色就像被推开到远方的一个梦,时而躲藏时而隐现。
床边的帷幔是中紫,比较沉稳,沿边走着波西米亚的花边,也让这种沉稳随着室内空气的流动和人的走动而活泼起来。室内温度不冷不热,由于湿度调节得好,小迪没有觉得有一丝闷热的感觉。
只是飘窗上两扇大玻璃窗,正被雾气服帖着,让整个房间显出紫色水晶的魔幻境界。
时间还早,才六点五十,天刚蒙蒙亮。
平时这个时候的清晨在小迪眼里都是模模糊糊的,一直模糊到抵达学校坐在被六盏白炽灯照得亮如白昼的教室里。今天因为学校停了所有的晚自习和双休补课,所以当小迪习惯性地醒来时,她有点不知所措。
她爬起来,拧亮灯,拿起抓绒睡衣套在身上,爬上飘窗,在雾窗上写字玩。
每一笔画的后面都是正在慢慢醒来的早晨。小迪通过横竖划出的玻璃镜面向外望去,对面的楼房有些许的窗口亮着灯,这些灯光微弱而游离,不知是亮了一晚的疲惫还是即将被早上的晨光吞没的戒备,晨曦的灯光不像初入黄昏时亮起的灯那么皎洁、那么自信。
就像此刻的小迪。一个平时在同学、老师眼里都是自信、沉稳很少犯错的少女,其实内心也有迷茫与迟疑。她早已习惯一个人呆在家里,父母的工作决定了他们来去的不确定性,但就是因为这种客观上的不确定性让小迪主观上学会了与自已相处。
雾窗上写着霍小迪的名字。
她喜欢写自已的名字,迪,道也,又有开导,遵循的意思,比如启迪,就是一个很美的词;在《诗经》大雅中也有一句“弗求弗迪”,妈妈曾告诉她这里的迪就是用,相比与无欲则刚,她更同意“弗求弗迪”。只是什么是自已的诉求呢?最好的朋友琴台可能在未来的一年半时间都不能与她为伴。而就在不久,她刚得知了其实这个家的屋檐下住着的不再是一对夫妻。
昨晚,她虽然试图和周天喻周叔叔聊起这个话题,但是她最终放弃了。她无法确定,如果妈妈连她都没告诉,是不是也没告诉任何人。
她是一个藏得住秘密的人,何况这个秘密也是对她隐瞒着,那么,她应该继续装作不知道吗?她想起以前在一本书里看过一个患了绝症的人,他的家属怕他受不住死亡的威胁而向她隐瞒了病情,而他其实早已知道,但也顺从了家人的一番苦心,到最后,虽然病魔仍旧夺走了他,但他与家人之间的理解与体谅却感动了众多读者。
也许她也应该这样吗?不过,这并不一样吧,因为生命的死亡是一条单轨迹,且不可逆。而一段婚姻的死亡却是多轨的,不仅可逆而且可生发多种不确定因素、
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绝不是因为购房什么的而假设离婚。那么,爸爸还是妈妈,他们谁出轨了?有了别的亲爱的人?
小迪把雾窗上的迪字的由字部分全部抹平,路灯昏暗的光在冬天的风里更加扑朔迷离了。
通过事实这一滤镜,小迪回忆起真实生活中的父母,突然觉得原来在细枝末节处其实早见端倪,比如,爸爸经常睡楼下的沙发上,他们之间好像从来没有一起照过相,也没怎么牵过手,只是以前他们工作很忙,妈妈在家,爸爸就不在家。妈妈不在家,爸爸就争取在家。
从小迪记事以来就是这样,所以她一直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正想着,手机铃声响了,这么早,会是妈妈吗?小迪从窗台上蹦下来,一看是爸爸的电话。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