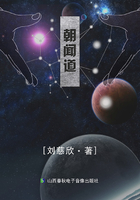狱吏亲自去找来躺椅,禁卒们手忙脚乱地把蓝二叔抬出监门。崔聪还嫌不快,一声“混账!”往狱吏屁股上踹了一脚。狱吏敢怒不敢言,便迁怒于手下,也大骂一声“混账!”踹狱卒的屁股。
陈瑸见此滑稽场面,不禁哈哈大笑。
“大老爷?”犯人似乎从笑声中觉察到什么。
§§§第四章:假释
光阴荏苒,转眼已是腊月十五日。
新知县上任途中被公差误捉,关进南监一事,在台湾府、台湾县引起一场大震动,对此事,知府胡德百思不得其解。派人到南监核查,想查清是哪一个公差所为。无奈此间向来办案稀里糊涂,对老百姓想抓就抓常常无案卷可查。胡德拐弯抹角询问陈瑸,被抓时为什么不表明身份。陈瑸回答说,一上岸便发现情况不对头,条条路口都有土民把持,如果表明身份,恐怕更有危险。既然衙役们搞错了,便将错就错,好瞒过土民,顺利过关。
胡德听来也觉有理,就不再追问了。然而,他胡德也非等闲之辈,他派人了解陈瑸进南监后的活动,便产生满腹狐疑。你陈瑸说路途上不表明身份,是为了遮掩土民的耳目,那么为什么进了县城,关进南监仍然隐瞒身份,一直让人关了十天?在这十天里又换了几个牢房,而且与那些番民打得火热,这不明摆着要摸我的老底,暗中算计我吗?
虽然陈瑸的行为略使胡德不安,但他毕竟是老奸巨猾,绝不会因此而慌了手脚。一来你陈瑸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二来县衙上下都是我胡德的亲信,若违背我的旨意,你说话没人听,做事没人帮,没有爪牙你想爬也爬不动;更重要的是,我毕竟是你的直接上司,你七品县官又如何敢动我五品知府?我且垫高枕头,看看你陈瑸有什么能耐!
而陈瑸到任之后,并无什么大动作,只是叫僚属将各类卷宗送来,他逐件披阅,几乎足不出户。时或找下属问问情况,熟悉一下新任所的情形。
他在台湾县府的二堂办公。这是一座柱梁结构的大屋,前任的家产早已搬走,而陈瑸仅负一行囊渡海而来,身外别无长物,于是这县衙二堂显得空荡荡的。这台湾县的治所设在台南,虽说与广东同处一地带,此时毕竟时序已届隆冬,这大屋便显得更加阴冷。二堂的后壁有一块大画屏,原来镶嵌着一幅《福禄寿图》,陈瑸嫌它俗气,叫人拆卸下来,换上一幅他手书的明人于谦的诗作《石灰吟》:
千锤百击出深山,
烈火焚烧自等闲,
碎骨粉身浑不顾,
只留清白在人间。
这是一幅行草中堂,笔酣墨饱,遒韧苍劲,倒与二堂的格调十分协调。办公用的长条几就摆在画屏下。长几上,摆放着南监犯人的案卷。说是案卷,其实十分简单,前面是几句空空洞洞的由头:抗交朝廷税赋,聚众犯上,图谋反叛。在这由头的后面紧跟着大串姓名。
几天来,陈瑸都在深入复查此案。案卷上那三句由头,他逐句琢磨。
按照朝廷规定的数额,土民都已交足,而且手上也都有税单。何来“抗交朝廷税赋”?官兵进村要钱,他们如鸟兽散,躲都躲不及,又怎么称得上是“聚众犯上”呢?民变闹事,确有这种迹象,但他们提出的要求不过是释放被扣押的乡亲和减免额外征收的税饷,这与反叛能挂得上钩吗?
左思右想,陈瑸都觉得县府给三百犯人所加的罪名难以成立。上任之日,他将错就错,让化装成兵卒的土民押送入监。在南监那十天,可以说是他有生以来最苦的时间。但是,他的收获却是难以估量的。首先,他通过与在押犯人的接触,掌握了案情的第一手材料,有助他在复查这个案件时分析、判断。其次,了解到台湾地方的一点历史和现状,比他渡海之前所了解的情况丰富得多,也生动得多。同时,也初步接触了当地的民风民俗,特别是第一次与被称为番的高山族老百姓接触,纠正了以往的许多偏见。
他认为,三百犯人是无辜的,应该赦释。
一会儿有几个班头来见知县,询问衙门几时放假。陈瑸十分干脆地回答:“今天就放吧,让大家回家赶上大扫除和送灶君。”
班头退出去后,陈瑸心头一阵紧迫。是啊,今天是腊月十五,不管是穷人、富人,都操持过年的事了。那么,南监三百无辜犯人呢?这个时候他们的心都比油煎还难受啊!三百犯人牵涉到三百个家庭,父母盼儿郎,妻子望丈夫,儿女们更是望眼欲穿地巴望父亲回家团圆。骨肉情深,令人怜悯。身为知县,为民父母,更应在这个时候体恤民情,为老百姓做件好事。本来,他已将上述情况行文上呈知府,这么多天了,上峰却毫无反应,好叫他心急啊!
陈瑸正怔怔地想着心事,老仆劳伯又来催他吃饭:“老爷,饭菜已热过两回,您再不吃又凉了。”
陈瑸说:“等一会儿吧,我正忙着呢。”
劳伯有些嗔怪,说:“再忙也得吃饭呀。老爷一天到晚地忙,哪里有这么多事情要办呀?”
陈瑸叹了口气说:“唉,现在只想办一件事,可是,连一件情都办不成啊。为了释放三百土民,我入仕以来,未曾这样劳神过。”
说起这三百犯人的事情,劳伯偕同陈瑸渡海到台湾上任,一上岸就接触了这件事,头头尾尾他是有所知晓的。那天刚出罗汉门,就碰上土民搜查,受了一场惊。后来,他又被强留在村寨当了十天的人质。自己虽未受任何皮肉之苦,但十天里他成天为主人的安全担忧,多少有些怨气,于是,便对陈瑸说:“这三百犯人被捉入监,委实冤枉值得同情。不过,那群番民的所作所为,也的确很野蛮,很粗鲁。”
陈瑸想听听劳伯的意见,问道:“你说土民野蛮,何以见得呢?”
劳伯说:“我们刚刚上岸就被捆绑,差一点性命难保,难道您忘记了?”
陈瑸沉吟良久,感慨地说:“这也是迫于无奈的事情。贪官以吏役为爪牙,吏役以人民为鱼肉,人民则以官吏为仇敌。据我亲身经历,番民倒是知情识义,有理有节的。”
劳伯向来佩服主人襟怀,当即赞叹道:“老爷以德报怨,实乃菩萨心肠。”
陈瑸进一步开导劳伯:“你已亲眼看到番民愤懑激烈,若不怀仁抚恤,他们将会做出更过火的事情,台湾岂不是永无宁日?”
劳伯更明白陈瑸的心思,点着头说:“奴婢明白了。老爷,吃饱饭再理会此事吧。”劳伯一再催促,陈瑸这才放下手上的案卷,打开饭桶的盖子,端起饭菜来吃——这个饭桶,是劳伯叫木匠专做的保温器具,内壁边上填上破布败絮,中间放置饭盅扣上盖子,热饭不会很快变冷。
虽然离开家乡到外地当官已两年多,但陈瑸的饮食习惯依然保持着家乡的特色,每餐要有一点点雷州人喜欢吃的咸海味:虾子酱、蟛蜞酱、咸鱼干、鱼露等,周而复始地轮流佐餐。陈瑸扒了一口饭,点了一些虾子酱,有滋有味地咀嚼着。一会儿,他忽然问劳伯:“唉,上餐不是还有半边咸鸭蛋吗?”
劳伯自然还记得,忙解释说:“上餐给你煮了一个咸鸭蛋,见你只吃了半边,我以为不好吃,便扔掉了。”
“哎呀,太可惜了!”陈瑸当真有点心疼地拍了一下大腿,说:“那鸭蛋腌得特好,蛋黄都涌出油来了,含在嘴里,香香酥酥,叫人回味呢,怎么说不好吃呢。我是留着那半边今餐下饭的呀!”
劳怕听明白了主人的话。两年来,他跟随左右,熟悉主人的性格,他虽领七品俸禄,却长年节衣缩食,到了令人见了也还不相信的地步。劳伯说:“老爷呀,你已今非昔比,何必这么节省的呢?别说一餐吃一只鸭蛋,就是吃一百只,一千只也不为过。如今你够吃、够穿、够花,还这么节省干什么?”
陈瑸听了淡淡一笑,不无风趣地说:“你不知道,你陈老爷是个守财奴吗?”
劳伯当然相信主人不是守财奴,但拼死拼活又是为了什么呢?
陈瑸似乎明了老仆在想着些什么,意味深长地对他说:“别想那么多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用完膳,陈瑸又向劳伯打听:“我和你商量开一方小园种瓜种菜,这事情办得如何了?”
劳伯告诉他,小菜园已经围好,再翻一遍就可以种东西了。陈瑸听说小菜园已开好,频频点头称许,连声说:“甚好,甚好。记住,一定要种苦瓜。”
劳伯说:“记得,记得,你看,苦瓜种籽都买好了。”
陈瑸从劳伯手上接过苦瓜籽,细致地辨认。这苦瓜籽确属上乘,颗粒均匀、饱满,与木鳖籽差不多,果壳平滑晶亮。陈瑸放在手中把玩,半天舍不得放下。劳伯又向主人请教:“请问,大老爷为什么特别喜欢吃苦瓜呀?”
陈瑸回答道:“苦瓜有君子之德,自苦而不苦他物。”
劳伯想了想,觉得主人言之极是。是呀,苦瓜炒牛肉、苦瓜酿肉丸、苦瓜炒虾丸……不管和什么混在一起,其他食物半点苦味都沾不上。想到这里,劳伯豁然开朗,兴致勃勃地说:“读书人与种田佬就是不一样,比如这些道理,我们就说不明白苦瓜自苦而不苦他物,堪称君子。难怪老爷喜欢苦瓜,因为苦瓜确实很像你的为人。”
主仆二人正津津有味地对话,忽听县丞崔聪在高声吆喝:“府尊大人驾到。”
陈瑸忙放下碗筷,抹抹嘴,并嘱咐劳伯赶紧收拾,打开中门,第一次迎接州官莅临。
陈瑸这是第二次见到知府胡德。第一次是从南监出来,到府署报到,交割部文。第一次见面陈瑸就对他产生一种威慑的感觉。论年纪,二人不相上下,但论模样则相差甚远。陈瑸身材瘦削,尤其颜面见瘦,双颊收缩,下巴很尖,皱纹又多,显得很苍老。而胡德则牛高马大,方脸宽额,脸色红润,油光闪亮,裹着一身官袍,即使在堂上静坐,也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
陈瑸将胡德及其随从迎入客厅,分序落座,劳伯逐一敬茶。胡德眼睛骨碌碌扫视客厅一番,见往日衙门的使妈、婢女都没了踪影,心想,这陈瑸倒有点眼力,那几个漂亮的婢女他已调往府衙,留下的是二流货,他竟也瞧不上眼,可能已经辞退了,便故意问:“陈知县,那几个使女呢,为何不给她们点活干?”
陈瑸说:“我都辞退了。”
胡德试探道:“准备换一批新人么?”
陈瑸答道:“非也。县衙差役数额已足,不必再用使女了。”
胡德感到不可理解。心想:你陈瑸假正经,离家几千里,连家眷都不带,是何居心,还骗得了明眼人么?正想拿几句咸咸淡淡的话撩拨他,陈瑸这回却先开了口:“府尊驾临,不知有何见示?”
见陈瑸一本正经,胡德也只得公事公办,打着官腔道:“食君之禄,当为君效力。我辈梦寐以求,无非国泰民安,岂有他哉?”
这话倒挺合陈瑸胃口,神情顿时显得开朗,不无快意地道:“府尊所教,实乃卑职夙夜所思。”
胡德先予赞誉,接着探询,说:“如此甚好。陈知县,对治理台湾有何良策?”
陈瑸停顿了一下,迅速梳理思绪,很认真地回答上司的提问:“卑职才疏学浅,说不上有何良策。唯有遵循圣意,不遗余力,抚民理番。”
“陈知县所言极是。”胡德似是不由自主地拍手称赞,“番民不理,则台无宁日。”
话题渐渐深入,谈及政事,陈瑸的兴趣便越来越浓,而且他觉得上司与自己的思路基本一致,希望能达到共识,真正找出一条能使台湾稳定和发展的路子。在上司面前,当然应该尊重他的意见,陈瑸由衷地向他请教:
“近来台湾民情鼎沸,大有生变之嫌,府尊大人请赐良方。”
胡德说:“依愚拙见,根子在监中三百犯人。”
陈瑸当即附和道:“卑职也如此看法。”他顿了顿,等待知府就此问题作出指示。谁知胡德却反问道:“贵县准备如何处置此三百犯人?”
陈瑸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如何处置三百犯人,自己早就写成呈文送上去了,怎么又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公务繁忙未及披阅,还是已经阅处明知故问?陈瑸的脑子迅速转了几转,决定不管他看过还是未曾看过呈文,自己的观点还是应该直陈而无须隐瞒。就是自己的主张不妥,他是顶头上司,今日大驾光临,是个请求纠正的好机会,说出来让他批评,也受教益。
“府尊大人容禀。”经过一番思索,陈瑸当着知府的面重申呈文的观点,“卑职一到任,就遇上这个大案件,心中实在不安。故将其余事情暂且放下,集中精力处理此案。连日来,我深入查访勘察,未发现三百犯人有违抗朝纲的举动,叛乱谋反的罪名不能成立。至于聚众闹事,抗交税款一罪,因他们各有税单在手,也不能定。既然罪不成立,就应释放。”
“陈知县此言差矣!”胡德听着听着,脸色就变了,听到要将三百犯人释放时,更是怒形于色,嗓门也提高了,“番民向来桀骜不驯,尤以山地生番为甚。对他们,必须施以威严,强制其俯首,才能保境安民。不管怎么说,不服官府管制就是反叛;聚众起事就罪加一等,若将他们释放,便是助其凶焰,日后生番更是无法无天了。”
胡德的一番宏论,使陈瑸大为诧异。诚然,无规矩不能成方圆,治国安邦不能只施仁政,还应伴随刑律显示威严。但是,刑有法,律有典,量罪有个准则,依据当是事实,岂能因番民不驯而横加挞伐?他有心与上司共同探讨,继续陈述自己的看法:“府尊说番民桀骜不驯,卑职也有体会。
然而古训有云:‘子惠元元,不遗在远。’番民同是圣朝黎庶,亦应得到安抚。黎民为国家之本,国法为保其利益而立。古往今来,最易激起民愤的是冤狱,如不及时纠正必定酿成大祸。”
胡德轻蔑地扫了陈瑸一眼,带着讥讽的口气说:“你在大陆汉区任职,见惯顺民,是不是让几个生番把胆子吓破了?”
知府这段话令陈瑸甚为反感。与少数民族打交道,他并非第一次。古田县的山区,就居住着几个少数民族。山地的生活,养成他们刚烈的性情,但绝非像知府所说的那样茹毛饮血、不通人性。他正考虑如何解释,胡德又说话了:“陈知县,你初来乍到,怎能像我了解的那么深入?”
陈瑸双手将案卷捧至胡德面前,恭谦地说:“府尊容禀。卑职一再告诫自己:初来乍到,人生地疏,切勿轻率断案。因此,对每一犯人案情由都作了细心的核查,一一记录于案卷之上,请府尊过目。”
胡德伸出右手将案卷挡回去,粗声粗气地说:“我不看!本府治台三载,对此案了如指掌用得着你来开导么?”
一语道破天机。陈瑸终于弄明白了知府为什么态度这么强硬,就因为此案是按着他的主意立的呀!要处理这个案件,算是啃到硬骨头了。看知府的态度,不按他的意思来办,肯定要得罪这位上司,来日方长,麻烦事肯定不少。如秉公行事,不用说他陈瑸要吃大亏了。可是,假若循着知府的路子办案,土民立即就要起事,势必与官府冲突。不管冲突双方谁胜谁负,流血事件在所难免,台湾县要由乱到治,必成一句空话。那时候,就不仅是得罪知府,还要辜负朝廷,惊动圣上,后果更不堪设想。思之再三,陈瑸觉得仍应据理力争尽量说服知府。方才胡德口口声声说自己对案件了如指掌,那就让他明确地表示意思才是。于是便询问胡德:
“府尊以为该如何处置?”
“快刀斩乱麻,抓紧判决!”胡德一副不容辩驳的口气,“杀几个,充军一批。其余先关起来,拿钱来赎再放!”
陈瑸半晌沉默不语。胡德耐不住了,口气咄咄逼人:“陈知县,你说话呀!”
陈瑸说:“府尊大人,这样不行啊!如果要卑职立即处理,只有一个字:放!”
“为什么?”
“查无实据,罪名不成立。”
“混蛋!”胡德脱口骂了一句,大概立即意识到如此在下属面前过分浅陋,旋即将语调放得缓和些说:“你别以为你才调查,才作笔录,才立案卷,府衙、县衙都在侦查,假如你将他们放出去,而别人又抓到证据那又如何呢?”
陈瑸坦然地说:“如有真凭实据,再将他们缉拿归案。”
胡德的嘴角掠过一丝冷笑,揶揄道:“捉了放,放了又捉,你以为是小孩童玩泥沙吗?你身为知县,可知台湾律典?”
陈瑸说:“卑职到任后,从头学起,略知一二。”
胡德问:“都有哪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