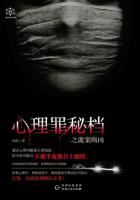张五吸过鼻烟,打趣似的道:“那沙,逼来了,我们躲躲。风大了,我们避避。可那个蝎虎子乱收费,到哪儿也躲不开。八兄,我也知道,大书房炕上比沙窝里舒坦呀。还知道,我一把干骨头了,再跑,就成破头野鬼了。可不跑,先得扎了喉咙。我说八兄,你是条汉子,能不能先管管那些官儿们,别再乱收费了?多少给条活路?”
孟八爷笑道:“开啥玩笑,我哪有这等本事。”
张五长长地噢一声,不再言语。孟八爷却品出了他语气中的嘲讽意味。这一点,他也深有同感。以前,逼急了,他便提枪进沙窝,问这天大地大的银行要钱。现在,一洗手,手头立马紧扎了。
张五慢悠悠说:“还有,那些腐败,兄能不能管管?老百姓都说,党是个好党,可叫那些腐败分子抹了黑。八兄枪法好,把那些腐败分子,一枪一个,崩了,既维护了党的纯洁,也为百姓出口恶气。”
女人笑出声来。豁子也犯傻似的哈哈几声。张五却不笑,自顾抽烟。孟八爷听出了弦外之音,脸有些发烧,灵牙俐齿几十年了,叫张五几句话就打哑了。真是窝囊。
只听鹞子冷冷说道:“这世上,有几个窦二墩?倒是那松尻子黄三太,出了一个又一个。”
孟八爷脸上着火了。
张五又说:“啥道理,我也懂。这风呀沙呀,都和打狐子有关,影响千秋万代哩。我懂,我都懂。但那千秋万代,是很遥远的事。现在,还得活呀。用
长草泥墁了嘴,或索性吃老鼠药,当个破头野鬼,总是不甘心呀。你说是不是?八兄。”
孟八爷的喉结动了一下。
张五又说:“听说,美国老拿人权欺负别国,人权先不谈,先得有生存权呀,先得想个法儿,活下去。知道不?光咱村,就有几十条光棍,他们都要断子绝孙哩。千秋万代,很对。可眼前,先得活下去。”说着,他打个哈欠。
又一个声音传来:“张五爷,救救我们。”这是谝子的公鸭嗓音。
张五笑了:“听,大道理,他们也懂,可能顶饭吃吗?那狼,那狐子,吃一只羊,就损失百十块。这损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那边……”他朝东扬扬下巴,“打一匹狼奖一千五,老百姓奖。你国家保,可人家不保。人家的乡长给我算过账,五年来,我收拾的狼和狐子,叫他们少损失五千只羊呢。在那里,我是英雄呢。开会时,乡长公开说:‘那张老汉来了,要好好招待。发展畜牧业,得欢迎人家来。’我不带一把水,一把面,就能住个一年半载,顿顿吃手抓羊肉。信不?”
孟八爷当然信,这待遇,他也受过。可他也知道,张五说的那儿,是沙漠化最厉害的地区,草山秃头了,草原成沙漠了。
“这回,是他们请的我。”张五指指那几张狐皮,“可这,够判几年了。八兄,你说,我究竟是罪犯?还是英雄?”
“罪犯!”孟八爷干脆地说,“以前,我也是。信不?你说的那儿,几十年后,就没人烟了,畜牧业也罢,农业也罢,都叫沙埋了。”
张五木了半晌,嗒然若丧:“这倒是。”
牧人们涌了进来,打头的是红脸和炭毛子。一进来,他们就用绳子捆了孟八爷。
“你别见怪,孟八爷。”炭毛子笑道,“我们可是受够了。谁保,叫他们保去。老子们,先得保了牲口,一家大小,还指望它们呢。再消耗,就要喝西北风了。只好委屈你了,等收拾了那畜牲,再请你喝酒,给你赔罪。”
“畜生!”孟八爷双眼充血,头发呀,胡须呀,都给体内的气鼓荡起来了。“由你骂,由你骂。”黄二诺诺道。他给张五跪下。红脸、谝子们都跪下了。屋外,还有齐齐的声音:“救救我们吧,张五爷。”
张五哈哈笑了。他捋捋胡须,望孟八爷一眼,“瞧,哪儿都这样。那些警察见了,会咋想呢?”
鹞子狠狠啐一口,冷冷地望孟八爷,脸上的肉棱一显即隐。
“他的兄弟,瘫了。”张五解释道,“上回抓的。我和他,差一点点。”
“那松尻子货,老子饶不了。老子羔子皮,换他张老羊皮。”鹞子的声音很冷。
孟八爷脑中“嗡”地一声:“咋瘫的?”
“打的。”
“谁?”
“还能是谁?”
孟八爷倒抽一口冷气。这事儿,他听说过。他们不是有“靠山”吗?咋瘫了?一想到一个年轻人瘫了,心不由地沉重了。
“张五爷,救救我们吧。”“就是。一枪敲了那狼。”“糟害了多少牲口,数也数不清了。”红脸们说。屋外的声音也乱糟糟的,情绪很是激动。
张五却解开了孟八爷身上的绳子,说:“我要打狼,谁也挡不住,捆不捆都一样望着跪了一地的牧人,孟八爷哭笑不得。他烦燥地摆摆手,“打去打去。老子也回家……吃饱了撑的?吃了苦,受了罪,费了脑子,反叫你们当猪捆了。”
张五哈哈大笑。那鹞子仍是不笑。张五笑道:“可说实话,那狼,可不是一个,打一个会有百个来报仇,“那就来一个打一个。”谝子道。他边说,边偷望豁子女人。女人却正望鹞子呢。
“我哪能守在这儿呢?人家,正抓我们呢。”张五哈哈笑着,却笑出了泪花。他用手抹了泪。“一叫逮住,这辈子出不来了。知道不?按官家掌握的数儿,几十个大案也够了。上次,叫人家把家底都搜了。”又对孟八爷说:“你……可真害苦了我……不说了……我知道,你没私心,是条汉子。可说清楚,我打狐子,不是为民除害。我没那么高的风格,我仅仅是想活命。几个儿媳妇,都是靠狐皮换的。”
鹞子又扫了孟八爷一眼。
张五朝牧人们扬扬脑袋,问孟八爷:“你说,这事儿,我管呢?还是不管?”孟八爷道:“按规矩办吧。这些,都算我踩的踪踪儿,你别插手了。若看中这几张狼皮,我赔你。成不?”
“不行!”红脸嚷道,“再耽搁,牲口都光光了。”
张五对红脸说:“人家八兄,可有日天的本事呢。这事儿,我不管了。鹤子,你也别管。这是规矩。人家踩了的踪踪于,我们不抢。”他又对牧人说:“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们打起来,容易。可我们不能守一辈子。那东西,打一个,来十个,人家千里路上来吊孝呢。闹下去,这地方连人也站不住了。知道不?现在,新疆呀,内蒙呀,都闹狼灾了。”
“我们的牲口,叫吃光不成?”红脸怒冲冲问。
“放心,我会生个法儿。”孟八爷道。
“若有法子,你早生了。”谝子也气呼呼道。他倏地起身,走了。牧人们也骂骂咧咧走了。
孟八爷很是羞赧。
瞅个机会,张五示意孟八爷出去。外面很冷。凌晨了,清冷的下山风吹来,干冷干冷的。牧人们仍在骂骂咧咧,内容很是刺耳。尤其那炭毛子,不干不净,缠夹不清,说了好些混账话。
张五笑了:“听人家咋说?也难怪。谁都指望在沙窝里挖个金元宝呢,却叫狼咬了个屁烧灰。”
孟八爷很奇怪张五的态度。他以为他会恨自己。有时,自责的情绪也会袭来。但他这“卖友”,不是为了“求荣”,他是无私的,心因之坦然了。但他坚信,张五会恨他的。但这次遇面,张五倒跟以前一样。
“我可是恨死你了张五道,“前些日子。现在不恨了。你知道为啥?”不
等孟八爷回答,他又说:“因为,我也活不了多久。”
孟八爷吃了一惊:“咋?”
“吃饭时噎,我估计是食道癌。胃也不好,有时,吃上就吐,可能活不长了。在死前,还得给小儿子娶个媳妇,把债还清,腿一伸,哈哈,就脱孽了。”张五夸张地笑几声,听来,却似猫头鹰在叫。
“快死的人了,犯不着再恨啥人。”张五笑道,“何况,你也有你的道理。”
孟八爷心头噎噎的,很难受,想说啥,又不知该说些啥,便长叹一口气。
“这辈子,没交几个朋友。你,是最好的一个哩。那几个徒弟,想找你算账,叫我喝住了。到阴间,我还想交你这个朋友呢。你可要快些来,我可是寂寞得紧。”说着,张五干笑几声。
孟八爷仰天长叹,又木了许久,才说:“那狼吐下的肉,专治噎食病,你
“吃过几两,也没顶用。”
“以前,可有吃好的。要常吃,多找些,当饭那样吃。老先人传的法儿,总有他的道理。”
“算了。”张五叹息道,“治好,也没用。听说,打五六个马鹿或狐子,就是大案。我至少够判个十年八年了,那牢,还是不坐的好,早死早脱孽。下辈子,变成狐子,叫人家打,再还人家百十辈子的命债……幸好,我没教儿子打枪。那几个爹爹,想学,我没教,我说你们安分些活吧。要是学了,这会儿,也正叫追得飞上跳下呢。”
孟八爷想说:正邪全在于心,与本事没关系,心正了,本事就正了。可没说,因为这道理,张五也懂。
“我的,全教那鹞子了,”张五道,“还有几个……想想,真有些后悔。那鹞子,人实诚,可心狠,老嚷嚷着要报仇。有我在,他不敢做啥的,背了我,说不准。他兄弟可真瘫了,也是个好小伙子,也算我害了他……你可要小心些。”
“活了几十岁孟八爷道,“也没个哈怕的了。伤生害命一辈子了,挨刀子和挨枪子,也是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