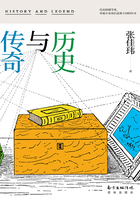“终极解决方案”就是希特勒党羽弄出的对于逃亡犹太人的处死方案。这你一定已经知道。就在我和杰克布下船的时候,一个叫梅辛格的德国人已驻扎在日本东京。一天,他召集一帮日本高级军官开会,转达了希特勒老大哥对他们的私人问候,并问他们有没有考虑过如何处置逃亡到上海的欧洲犹太佬。三万从欧洲漏网的犹太佬,不能总任凭他们逍遥自在,总得有个最终的处理系统。这就是后来他到上海拿出的“终极解决方案”的前提。
梅辛格杀人不眨眼,在波兰杀犹太人就杀疯了。犹太人给了他一个名字:华沙屠夫。1942年6月,也就是在我和杰克布下船的七个月之后,泄露绝密的高级娼妓提到悄悄住进了理查饭店的德国人叫约瑟夫·梅辛格,上海的犹太人就像看到了末日。
杰克布和我走出海关,跟在给我们挑行李的挑夫后面。江边停靠着一排排豪华轿车,一个英国老绅士牵着一头苏格兰牧羊犬,边漫步边和狗进行跨物种交谈,几个穿白色海军裙的金发女童正在打板球,远远地,从外滩公园音乐亭传来露天音乐会的铜管乐,营造着激昂向上的错觉。
我走在杰克布身边,喋喋不休地讲着这座大厦叫什么,那座大楼什么来由。但我发现他和这个假和平假繁荣的气氛格格不入,他心不在焉,或者说专心一意注视自己内心的某个死心眼儿。
后来他告诉我,他在想一个很大的问题,关于迫害。他企图想出一个理由,为什么一些人认为他天生有权力迫害另一些人。为什么只有对他人迫害了,他才觉得自己高大,有力量,正义。推演下去,也就是,越是对他人进行迫害,他越觉得自己高大,有力量,正义。
不过这是后话。他要在很久以后才会把他由两记耳光引起的思考告诉我。在那时,他突然发现我在这个思考题上也能做他的谈手,因为我也常常钻牛角尖地追问人类从来不断的各种迫害到底是怎么回事。
挑夫把我们的行李挑到黄包车聚集的地方。黄包车比乘客多多了,杰克布被抢生意的黄包车夫扯斜了衣服和裤子,最后是靠我给他解了围。他很困惑地看着这种前面带两根直木的车子,琢磨着如何前进后退。等我示范地乘坐到车椅上,让两个皮箱乘坐在我大腿上,他才明白这车没有引擎,全部动力来自两条绛色的胳膊,两条静脉曲张、肌肉暴凸的腿。
他说:啊,你居然让他做马来拉你?
我说:你不让他拉让谁拉!
他四下看了一眼,无数只破草帽下的黑眼睛直直瞪着他,希望他不满意他原先挑中的车夫,他们可以再有一次入选机会,可以来为他做“马”。
他说:我不坐把人变成牲口的交通工具。
我不耐烦了,问他到底走不走,江边风又大又冷,路还远着呢。
他说:你懂吗?这就叫非人化。希特勒就是把犹太人非人化之后,才让其他种族这么恨犹太人的!
我心想,他怎么不幽默了?他不是善于从所有事物里找笑料娱乐他自己和别人吗?
我问他:那你想怎么办?
他说:去找辆汽车。我不信上海除了把人变成骡子来拉车就无路可走,就没有任何其他交通工具?
我说:好吧,我等着,你去找汽车,祝你好运。我从黄包车上跳下来。我的打扮像是一切就绪,马上要进入某贵夫人的下午茶会,又尖又细的皮鞋跟儿每一步都有插进石板缝的危险。
黄包车夫一看到手的生意砸了锅,马上拦住我,求我开恩,家里老的小的,都等他的车费去买米,现在米吃不起了,吃珍珠米、碎挂面,米价比一年前涨了许多倍!他叫我别让他们全家今朝夜里吃西北风哦。
我还没说什么,杰克布已经又回来了。没有找到出租汽车。不用我翻译,他也懂了一多半。他想出个折中办法:我和箱子乘黄包车,他自己则步行。
杰克布习惯乘黄包车是到达上海的三个月之后。他无奈地说:把自己变成马去拉车,为了孩子妻子能吃上饭,是了不起的。犹太人做不到这样。
杰克布在船上就买了一张上海的地图,没事便向水手们和我打听,随手圈圈点点,什么电车、公园、大市场、娱乐场,在他心里一盘棋。所以他跟着黄包车快走时,还不时打开地图,一次次核准罗盘。好极了,现在我不用拿出什么主张,这个杰克布主张大得很。人行道上,每一平方尺的路面上都行走或站立着一个人,不急不忙浮动的人脸人头一望无际,杰克布绕过一个人,却立刻跟下一个人撞个满怀。他不停地从人行道上对我耸肩、做鬼脸,表示他对上海的人灾虽然有心理准备,却是远远准备不足。
每一次拐弯,他都机警地看看路牌,再看看手里的地图。最后居然对我说:准备了,快进入你们家的领区了。
我饶有兴味地看着他。这是个机灵人物,生存能力极强,用不了多久就能认上海作故乡。把他丢在这里,不必担心他活不了。
我的计划就是要把他丢到上海,把彼得带回美国。这个计划可真需要胆大、心硬、想象力丰富。心硬,是指丢下杰克布,把他丢在对于他来说事事古怪人人陌生的异国城市。
我把杰克布领进我父亲家的大门,上来迎接的是女佣顾妈。父亲去内地快一年了,凯瑟琳还赖在上海。父亲绝没有想到我杀了个回马枪,回来了。顾妈一边打量“艾先生”,一边讲凯瑟琳的坏话。这是女佣们的一套外交手段,对你好不必讲你好话而只讲你对头的坏话就事半功倍。再说顾妈和我的交情从我十二三岁开始,凯瑟琳嫁进来的时候,早没她地盘了,老女佣心理地盘上,我是个受后妈排挤,终于给挤出门的灰姑娘。
顾妈说:这个艾先生一表人才,做什么事的?她挤眉弄眼地欢欣。
我皱起眉头说:他就是一般的熟人,住我们家付我房钱的!
顾妈又说:哎哟,你不要留这样一个俊先生在家里住,那样你的小妈也不出去打牌、逛商店了,专守在家动艾先生的脑筋!
我说:临时的呀,寻着地方就让伊搬场!
反正杰克布听不懂顾妈和我的对话。我们一个扬州话,一个上海话,热热闹闹地把他讨论了一遍,讨论让他一天付多少房钱够我零花。
顾妈说着,拿起杰克布换下的脏衣服去洗:那我要好好服侍他,你好多赚两个零用铜钿。
我听了哈哈大笑。
上海正在发生粮荒,连我们家都处处可见饥荒的阴影。凯瑟琳的糕点盒子全空了,漏在缝里的饼干渣一股哈喇味,说明她被迫改掉吃零食的习惯已经很久。顾妈在厨房里也出现了一些下意识动作,比如往锅里倒油之前,先把油瓶举到光亮里飞快地看看,倒了油之后,手指头自下往上飞快一刮,往瓶口里一抹,再举起油瓶看一眼,看自己的手指头是否刮下一点油,也看被抹进瓶口的细小油珠是否正顺着瓶子的喉咙口往下流。她对这些新动作并无知觉,但我觉得它们是对我的提醒,更大灾难来了。大灾难终于朝着租界这座孤岛来了。我把杰克布带来的正是时候!我必须在灭顶之灾降临之前不择手段、伤天害理地来营救彼得。所以我见了彼得就说,彼得,我回来是接你去美国的。
他的大黑眼睛马上聚拢焦点,我的脸被他盯得一团火热。我抱住他,呼吸着他海绵浴的檀香皂气味,浸没在他的体温里。
彼得倒是比我刚见到的时候健康许多。集中营、轮船底舱、难民大宿舍染到他肤色上的菜青色,已经褪尽了。所以他看上去白净而俊秀。在粮价激涨的1941年秋天,能有个健康白净的彼得让我好满足。
彼得说了一句什么。我的脸埋在他胸口,没去注意听。他重复了一遍,这回我听见了。他是说奥地利税务局不寄给他税务凭据,谁都无能为力。
我说不用他管这些,就做好出发准备。他问我能不能告诉他,我到底有什么办法,让他从危机四伏的上海朝着安全的彼岸出发。我说以后再告诉他。他把下巴抵在我的头顶上,请我务必告诉他。
我笑着从他的怀抱里撤出,一边说:你可不要知道香肠是怎么做成的。得有多少恶心的环节才能做出美味香肠,你千万别打听。等盘子摆在你面前,好,请吧,滋味好不好是关键。滋味好就行了。
我满嘴胡扯,嬉皮笑脸。他也疑惑地跟着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