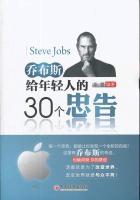抬头,便见到了江。窗外的这条江叫奉化江,从四明山东麓的秀尖山走来。最初它一定也是山川间无数条涓涓细流,迈着轻柔的细步,哼着“叮叮咚咚”的小调,一路歌唱一路汇合而成的。途中,剡江、县江、东江、鄞江又纷纷注入。它也就渐渐地茁壮起来了,由一个清逸柔情的姑娘,摇身变成了粗犷豪放的汉子。嗓音也浑厚起来,澎湃出“砰砰”的涛声。浑黄的江水浩浩荡荡,泛起浅浅的涟漪,恰如翻飞的思绪。它每天都铺展在我的眼前,只是因为疏忽,因为熟视无睹,我从未如今天这般细细地打量过它。蓦然间一股亲切感油然升起。
对奉化江最初的记忆可以追溯到儿时。一年总有那么几次,外公牵着我坐航船去奉化走亲戚。清早,我们在浩河头上船。等舱里坐满了人,撑船老大一声“开船啰”,船就悠悠地起航了。两边的楼房缓缓向后退去,河道里舟来楫往,煞是热闹。行不多久,就到了一个堰坝。坝上左右各安有一个大轱辘,操作的人用比手指粗的钢缆套住航船,然后就有十几个人转动轱辘,船就缓缓地爬上坝顶。等到把钢缆松开,船就由高处呼啦啦地冲进了奉化江。整个过坝的过程新奇又刺激,每每这个时候我总是不安分的,伸颈翘首,抬腿举足要看个究竟,外公就会使劲地按住我,让我动弹不得。
过了坝,水面霎时开阔起来。许多航船聚在一起,排成一字长龙,由一只汽船拖着向上游进发。船轻轻地晃动,江水拍着船舷传来有节奏的“啪啪”声,犹如躺在摇篮里聆听催眠曲,倚在外公的怀抱里,我就进入了梦乡。航船也如公交车一般,有站点的,我的美梦总是被船老大到站的吆喝声所撕碎。于是,船舱里经过一阵骚动,后复归安静,又开航了。
这段航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翻石渡”。大概是“翻石”同“番薯”发音相差不多的缘故,许多宁波人都把“翻石渡”叫成“番薯渡”。我的外婆、阿姨都这么叫,我当然也不例外。后来是外公告诉我,正确的叫法是“翻石渡”。相传在这个渡口曾有一块巨石,因潮起潮落的巨大冲击,巨石被翻转移动远离了渡口,因此而得名。确实,奉化江到这里拐了个急弯,水流也湍急起来。船进入这段江面后,船老大就会招呼大家坐稳了,把孩子看住了。
奉化江从我办公室的窗前流过,就抵达了三江口。在那里同余姚江汇合,成了甬江。然后就声势浩大地奔东海而去。现在想来,我自踏上工作岗位后,同这条大江总有着丝丝缕缕的牵连。
从农村插队回城后,我进了一个船厂。船厂紧贴甬江边。当时那是一个荒僻的所在,不通公交车,只有一小时一班的长途车经过。刚进厂时,正值寒风猎猎的隆冬。我和五个伙伴被安排在一间破旧的二层楼房里,呼啸的江风从门缝、板缝往里灌。推开房门,眼前就是一大片滩涂。冬天是修船的淡季,滩涂上寂寞地矗着几艘帆船。远眺,滩涂的尽头滋生着丛丛高过人头的苇草,秆枯叶萎,在朔风中瑟瑟发抖,看着甚是凄凉。涨潮了,浑黄的江水一波接一波地盖过来,眨眼间就覆盖了那片滩涂,也覆盖了我的心。儿时亲切又温馨的江变得那么可恨又可憎。
刚从艰苦的农村出来,又跌落到如此荒凄的所在,自然是又失落又惆怅又无奈。生活总是不会缺少刺激,除了上班,我把剩余的精力都花在打牌、闲聊上。在牌局中,饭票、小钱来来往往,刺激那已显麻木的神经,在闲聊中借天南地北趣闻、时政美女慰藉已枯涩的心灵。当然,偶尔我也会独自在江堤上彷徨徘徊,对着滔滔江水发呆,心底里就会如江水那般溅起几点白白的浪花,难道就如此一直颓唐、沉沦下去?面对浑黄的江水,我找不到答案。
冬去春来,那一丛丛苇草绽出了嫩芽,孕育出盈盈绿意。一艘艘长年在海上接受风浪洗礼的帆船开进了厂区。它们斑驳苍老,满目疮痍,气息恹恹,我可以感受和想见它们在大海中颠簸前进的艰辛与艰毅。沉寂了一冬的厂区也“砰砰砰砰”展露出它应有的生机。我的工作就是挥斧拉锯,把帆船身上的累累伤痕一一抚平,让它们重新焕发搏风击浪的能量,重展激流勇进的英姿。当一艘艘来时如衣衫褴褛的老叫花,去时如油光鲜亮的棒小伙的帆船扬帆起航时,我会久久地默默注视它们,心头浮起丝丝缕缕的成就感。帆船可以重修涅槃新生,人生同样也可以奋发进取。春风吹绿了大地,也吹暖了我麻木的心,我感觉我应该做点什么了。于是,我开始了学习,每隔一天往返三十里骑车到市职工业余大学上课,空余时间就阅读和做作业。生活很累但充实。荒僻的所在,在春风里也缓缓露出了它的妙味。上班时,拉锯挥斧时的间歇,汗水淋漓中能观赏到潮起潮落,聆听到江涛拍岸。业余时,或是背着夕阳临风阅读,或是同年轻的朋友一起在江边漫步,侃人生,侃爱情,侃时事,侃生活……人生的憧憬、未来的希望、待展的抱负,都点点滴滴洒落在大江的涛声里。我的文学梦也是在江边阅读时萌芽的。四年后,我取得了大专文凭,离开了船厂。
现在,我工作的单位又紧邻江边。潮起潮落的江水浑浊、浑黄。其实,最初它也是清的,是山间清清的溪流,走着走着,泥沙俱下,它开始浑浊。这也如同人生,最初也是纯洁的,长着长着,物欲俗念日增,人就开始世故圆滑。这究竟应该庆幸还是憎恶?我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