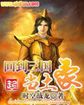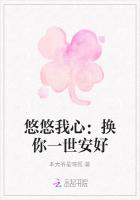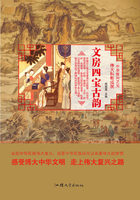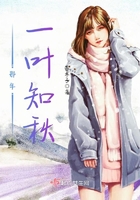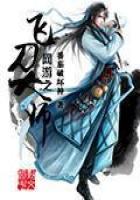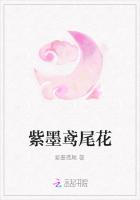1938年日机对重庆的轰炸是远距离试探性的攻击,而1939年的轰炸则进入频繁、野蛮、大屠杀阶段。
1939年1月,日机接连多次对重庆进行轰炸。其中,15日的轰炸是日机空袭重庆以来造成伤亡最多的一次。此次轰炸后,国民政府提高了反空袭的意识,加快了防空队伍和防空设施建设的步伐。
从2月至4月,日机没有飞临重庆上空,原因有二:其一,此时值重庆多雾季节,整个重庆几乎天天裹在浓雾之中,能见度极低,日机从空中根本无法找寻轰炸目标。其二,从往次轰炸中,日军已经发现,他们的飞行技术和投弹技术训练不够,致使投弹命中率很低。于是,日军集结飞行员于基地,补充装备,加紧训练,为以后轰炸重庆作准备。另外,也出于减少空袭次数,可以麻痹对方的考虑。
5月的重庆,天气晴朗少云。日军抓住这个时机,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五四”惨案,创下了二战史上一次轰炸造成死伤最多的纪录,给重庆带来了特大灾难。
6月~9月,日机又对重庆进行了频繁而又疯狂的轰炸。这几个月的轰炸,与以往的轰炸相比,具有明显的特点。其一,轰炸范围更加广泛。日机不仅轰炸繁华的市区,连近郊甚至远郊也成为攻击目标。其二,施行无区别轰炸。居民住宅、学校、工厂、医院、外国驻华机构及领使馆都未幸免。其三,除白日轰炸外,还采取夜间不定时轰炸战术,延长骚扰、轰炸时间,使重庆时时处于惶恐不安之中。
1939年日机对重庆的轰炸之所以呈现出上述特点,与1939年时局密切相关。
首先是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敌,助长了侵华日军对中国腹地城镇实施航空进攻作战的嚣张气焰。
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和国民参政会议长。他和国民党中委、宣传部长周佛海,国民党中委、政府实业部部长陈公博等形成了亲日汉奸集团。抗战刚开始,汪精卫就主张妥协投降。1938年11日3日第二次《近卫声明》发表后,在日本政治诱降的诱惑下,汪精卫加快了公开投降日本的步伐。他指定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和梅思平为他的代表,到上海与日本参谋部官员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秘密会谈“和平基本条件”,并于11月20日与日本签署了反共卖国的《日华协议记录》,规定:日华共同反共,缔结防共协议,承认伪满洲国等。根据叛国投敌具体行动计划,汪精卫等于12月18日潜离重庆飞抵昆明,次日和已在昆明的周佛海等叛国外逃至河内。配合汪精卫等人的叛国行动,22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重申过去提出的“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具体提出了对国民政府招降的条件。汪精卫于29日发表“艳”电响应,要求国民政府根据日本首相近卫提出的承认伪满洲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与日本交换政府意见,以期恢复和平”,并无耻地鼓吹,对于日本,本着冤仇宜解不宜结的根本意义,努力转敌为友,这样,“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30日,汪精卫在对日本的“四点希望”中提示日本方面“对重庆可施以致命的轰炸”,死心塌地当日本走狗。
汪精卫的投敌卖国,为虎作伥,使日本认为,抗战后方必会因此人心大乱,主和派势力会因此而占上风,日本趁机加强对重庆的轰炸,会给国民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促使国民政府瓦解、屈服。
其次,国民党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加重了日军以炸迫和、以炸迫降的幻想。
武汉失守后,日军改变了对国民政府以军事打击为主的政策,将其主要兵力移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随之,国民政府也将其政策的重点转移到了反共反人民方面。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是国民党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标志。这次全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斗争”。会议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会后,国民党陆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等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的文件。在这些反共文件指导下,国民党军队在各地制造了一件又一件的摩擦事件。
国民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的举动,使日本改变了对蒋介石的策略。1939年2月,华北日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所拟的“和平计划”中,改变了过去坚持把蒋介石下野作为“议和”先决条件的策略,转而要“尊崇蒋介石上将的地位而给予崇高位置”。3月初,日本新任首相平沼在国会演说中正式提出:“蒋介石将军与其领导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虑其反日态度,与日本共同合作,谋东亚新秩序之建立,则日本准备与之作中止敌对行为之谈判。”继从否认国民政府改为承认国民政府之后,日本又从反蒋变为拉蒋。
在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的双重作用下,汪精卫集团投入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怀抱。日本认为,对一贯坚持反共立场的蒋介石采取同样的手法,也会收到同样的效果。因此,在政治上拉蒋的同时,日本加紧了对国民政府、国民党党部所在地重庆的轰炸,妄图·23·
达到以炸迫和、以炸迫降的目的。
其三,远东慕尼黑阴谋使日本航空进攻更有恃无恐。
武汉战役期间,英、法出于保护自身利益,同德国签订了出卖捷克的《慕尼黑协定》。占领武汉以后,日本感到再扩大侵略已力不从心,于是迫切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中国事变”,巩固已经在中国掠得的利益。日本把中国再来一个慕尼黑协定的希望寄托在英、美等国身上。英国由于战争阴云已密布欧洲,无力顾及远东,希望以妥协的办法来保护其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利益。美国不愿卷入对日战争,已有准备参加对它有利的谈判,维护其在华利益的表示。这样,在日本的请求下,英、美人士便往返穿梭于日、蒋之间,充当起“中日冲突”的调停者。经多次会谈,1939年7月24日,日、英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英国表示“完全承认”战争状态下的“中国之实际局势”。承认“在华日军为保障其自身之安全与维护其侵占区内公安之目的计,应有特殊之要求”。同时承认”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于日军之敌人之行为与因素,日军均不得不予制止或消灭之”。在这个协定中,英、美不但承认日本占领中国领土的合法性,而且允许日军对抗日根据地采取包括大轰炸在内的一切战略手段。英、美等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纵容,助长了日本亡华的野心。
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1939年日机对重庆的轰炸在空袭次数、出动飞机架次、投弹数量等方面,都比1938年大有增加,因而重庆在人员伤亡、房屋损毁方面,也比1938年损失更加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