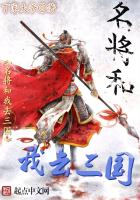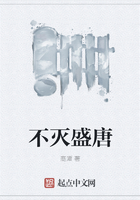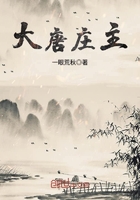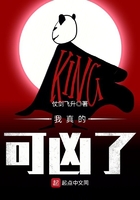国民政府各机关和军事委员会相继迁到重庆后,重庆遂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指挥中心。并且,随着重庆经济、文化教育、交通运输等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重庆在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地位越来越突出。
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政治舞台在武汉。国民政府迁渝后,这个舞台随之转移到重庆。1938年10月,中共驻武汉代表周恩来等和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报馆迁到重庆。1939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以公开身份在重庆与国民政府合作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为了更好地进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于1939年1月13日决定在重庆建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作为中共中央国统区的派驻机构,由它负责领导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及部分沦陷区中共的工作。以后,各民主党派、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力量均相继集中到了重庆。重庆成了战时中国各种政治力量汇集的地方,成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利用这个舞台,中国共产党妥善地解决了和国民党错综复杂的关系,维系了国共合作,并大力开展对民主党派、地方实力派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爱国人士的工作,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益巩固和发展,使重庆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保证了抗战的最终胜利。1945年9月3日《新华日报》社论分析抗战胜利的原因时,指出了国共合作的重要作用。社论说:“值得我们庆幸与骄傲的,乃是团结抗战的大局,终能依赖各方的努力,特别是依赖蒋委员长的远见与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努力,得以维系不坠,而达到今天的最后胜利。”·41·
与对日抗战的政治中心转移相伴随,国内经济中心也转移到了重庆,使重庆成为抗日时期全国的民营工业、农业、商业、金融、贸易、交通的“中枢”。
抗战爆发前,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下游以及沿海地区,是我国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商城市。据国民政府实业部统计,1936年初,江苏、浙江、广东等沿海省市的工厂占全国登记工厂的70.75%;资本额占全国资本总额的70.49%;工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76.99%。上海已登记的工厂占全国已登记工厂的31.39%;资本额占全国资本总额的39.7%;工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31.78%。这些工矿企业如毁于日本人的炮火,将大伤中国民族工业元气,严重削弱抗战实力;如果被日本占领,将为侵华日军利用,助桀为虐。因此,卢沟桥事变后,一批爱国人士如胡厥文、颜耀秋等陈书国民政府,恳请政府资助厂矿内迁。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迅速作出工厂内迁决议。由政府拨迁移补助款106万元,在运输上给予便利。在民营工业家的积极配合下,从8月中旬开始,掀起了大规模工厂内迁高潮。内迁厂矿先迁至武汉。当武汉战事吃紧时,第二次内迁至西南。到1940年工厂内迁结束时,经政府所属工矿调整委员会协助的内迁民营厂矿有448家,随迁工人12164人,内迁机件材料7.1万吨,其中迁至四川的厂矿占大半,达254家。据统计,迁入重庆的民营厂矿为225家,占内迁总数的50%,占迁川厂矿总数的90%。同时,第10、20、21、24、29、31、50等七大兵工厂也先后迁到重庆。到1940年,重庆拥有159家机械厂、17家冶炼厂、23家电力厂、120家化工厂、62家纺织厂;其他行业40家,共429家。重庆成为大后方唯一的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区和战时的“中国工业之家”。
抗战爆发后,金融业先后内迁,公营和私营银行汇集重庆。抗战前,重庆的公私营银行包括总行、分支行处、钱庄银号等共59家。到1941年底,在渝银行总行有18家,分支行处72家,钱庄银号53家,共计143家。不仅垄断全国金融事业的中国、中央、交通、农业4行总行或总管理处和中信、邮汇局设在重庆,而且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河北、湖南、安徽等省银行也集中于重庆。重庆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的金融中心。
由于沿海工商业相继内迁重庆,重庆人口猛增,使本来已很发达的商业贸易更加繁荣。到1941年,重庆的各类商号达到1.4万余家,从商人口达10余万人。重庆成为购销国内货物,集散外贸物资的中心。
国民政府迁渝后,重庆交通运输得到飞速发展,成为大后方的重要交通枢纽。到1941年,重庆已有民营轮船公司14家,其中以重庆民生实业公司实力最为雄厚,开通了重庆至长江中上游沿江各重镇的10条水运线,共有轮船288艘,总吨位6.4033万吨。川江流域重庆区另有木船4万艘左右,年运输量约达250万吨,船工计30万人。为加强重庆与西北、华中的交通联系,还开通了川湘、川陕水陆联运线。公路运输方面,国民政府除全面整修了川湘、川黔两条公路外,还改造、增筑了重庆连接成都、遂宁、老河口、贵阳、广元、宝鸡、兰州、迪化的公路线,并与中国至印度、缅甸、苏联的国际公路线联接。航空运输方面,由于中国航空公司、欧亚航空公司的迁渝,新航线的开辟和机场的修建,重庆成为了大后方的空运中心。到1940年,重庆已开辟了重庆至香港、成都、宜昌、乐山、贵阳、西安等10余条国内航空运输线。1941年底,重庆至河内、仰光、加尔各答、阿拉木图等国际航空线也先后开航。
抗战爆发后,重庆也成为大后方的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中心。为保存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大批高等院校和科学文化机构纷纷迁往重庆。迁渝的高等院校有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35所,加上重庆原有的重庆大学和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占全国高校的34%。迁来重庆的具有当时国家一流水准的科学研究学术单位、文化机构也很多,如国民政府国史馆、中央广播电台、兵工署弹道研究所、中央工业实验研究所、中央农业实验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国立编译馆、商务印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中央电影制片厂等100多个单位。另有相当数量的中等学校和10余家报纸迁来重庆及附近地区,重庆因而呈现出学校、文化机关云集、文人荟萃、群贤毕至的局面。
由于重庆成为抗战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活动和外交活动中心,重庆成了侵华日军重点攻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