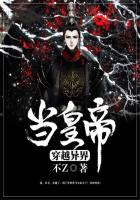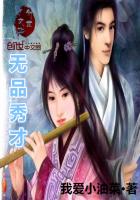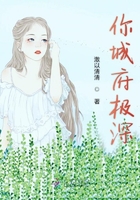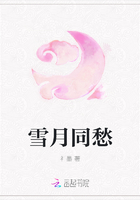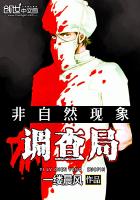重庆军民对日寇轰炸的坚毅斗争精神不仅鼓舞了全国军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和决心,而且博得了国际赞誉,在国际上树立了坚韧不拔、愈炸愈奋的形象。在空袭连绵中,驻重庆的各国新闻单位都对中国抗战进程和“重庆精神”向全世界作了宣传报道,许多来渝国际友人回国后宣传介绍了重庆的反轰炸斗争,使世界逐渐了解了重庆和中国,扩大了中国抗战在国际上的影响,大大提高了重庆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使重庆由一个僻处内陆腹地的中等城市一跃而成为与伦敦、华盛顿、莫斯科三大城市并驾齐驱的国际名城。
1939年8月,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到重庆访问。这是抗战爆发以来首次来华访问的外国政党首脑,也是重庆国际地位日隆的象征。重庆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蒋介石和尼赫鲁会谈的那一天,困遭日机反复轰炸,会谈过程中会谈者曾三度避入防空洞。尼赫鲁在重庆还会见了博古、林伯渠、吴玉章等中共领导人。尼赫鲁对重庆的访问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后来他在自传中写道:我想不到有任何不幸的命运能够摧毁这个有古老历史而现在又很年轻的民族的精神。
国际社会舆论普遍谴责日机轰炸重庆,并对重庆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国际反侵略运动各国分会纷纷谴责日机对重庆人民的滥炸,宣传重庆军民的反轰炸斗争。英、美政府对日机轰炸重庆及其驻华使馆等在华利益受损提出严重抗议。1940年8月,美国国务卿赫尔在接见新闻记者时,向记者叙述了重庆被狂炸的惨状,对日本的狂炸行径进行了批评。他明确指出:“此种暴行,无论在何处何时发生,均为吾人所衷心谴责。”他对日本轰炸平民表示厌恶,·044·
并表示要对日本实行禁运。
重庆的防空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好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由重庆回国后撰文赞誉重庆防空设备为世界第一:“警报发出后,除中国飞将军、高射炮队、防护团体等各就岗位,执行歼灭敌机或减少损害的神圣任务外,市民扶老携幼,鱼贯入洞,仿佛欧美上工厂的情景,解除警报后,鱼贯而出,仿佛下工厂的情景。”
重庆人民英勇的反轰炸斗争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1939年12月,美国新闻通讯社记者杨格访问重庆返香港时发表讲话,赞扬“重庆一切,均充满生气,与东京之萎靡不振,实有天壤之别,中国前途甚为光明。”英国《泰晤士报》针对日机狂炸重庆发表《中国英勇抗战,已蔚为强国,将负恢复远东繁荣重任》的评论。评论指出:“日本飞机最近狂炸重庆,对于战局方面,实无丝毫影响。中国人民过去曾倍尝痛苦且于忍耐力持久力方面,更具悠久之传统,决不因任何形式之胁迫而放弃其抗战建国之目的。目前全世界任何地域,对于最后胜利信念之坚,恐无出中国之右者。”
1941年11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发表演讲,对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儿的断瓦残垣,我们无庸掩饰,不过重庆人和英国人一样,满不在乎,炸毁的地方,他们已大半的从[重]新建设起来了。实在说,对于他们的断瓦残垣,我们感到骄傲,因为它们是为争取自由而付出的代价,同时它的存在也象征我们愿意付此代价的符号。实在谈起来,在重庆若是住在一间完整的屋子,几乎是一种极坏的享受,这里对于像完整的屋子等等并不重视,这些差得太远,这里所重视的以及中国人民所具有的显明的美点,是勇敢的心和不能破碎的精神。并不是所有远东的炸弹足以挫折中国人民的精神。……他们和英国人民一样,以不可动摇的坚毅和永久的愉快来接受这些炸弹,每个炸弹带来的爆炸、死亡、毁坏和废墟,看起来使他们的团结越密切,使他们一贯到底的决心越坚固。”1942年6月15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对英国民众发表广播演说,盛赞重庆的伟大:“自日本开始进侵中国,迄今已有五载……中国仍屹立不移,足以象征中国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决心之重庆,乃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一名词。为各自由民族而言,重庆乃联合国家所有振奋之精神之象征;为独裁者而言,重庆乃若干民众甘冒危险忍受痛苦不接受侵略之束缚之象征。……例如余可提及日机故意轰炸各大学,然此等轰炸并未达到其预想之效果,中国学生于临时之大学,继续攻读不辍。吾人于亲眼获睹此等艰苦之余,实感无限欣慰。此乃中国前途最佳保证。重庆之民气仍极高涨,斜枕于扬子江上的重庆城,到处断垣残壁,然附近山丘与河流,均经开发,市民亦孜孜不倦,使一切生活照常进行。在空袭警报网及防空洞方面,重庆直可与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较而无愧色,重庆之应成为世界理想中之一项事物,实无足异。”罗斯福总统曾致书重庆市民,对重庆市民在反轰炸斗争中的坚毅精神给予了高度赞颂:“余兹代表美利坚合众国人民,敬致此卷轴于重庆市民,以表示吾人对贵市勇毅的男女老幼人民之赞颂。远在世界一般人士了解空袭恐怖之前,贵市人民迭次在猛烈空中轰炸之下,坚毅镇定,屹立不挠。此种光荣之态度,足证坚强拥护自由的人民之精神,绝非暴力主义所能损害于毫末。君等拥护自由之忠诚,将使后代人民衷心感谢而永垂不朽也。”
重庆良好国际声誉和形象的获得,是重庆人民坚韧不拔,流血流汗,顽强奋斗的结果。
资料1:
蒋介石在陪都各界庆祝
还都大会上的致词(1946年4月24日)
“各位先生同志们:本席感觉今天是政府迁都重庆八年以来最光荣最快乐最值得纪念的一天,我们政府在抗战局势艰难危急的时期,迁都重庆,经过长期艰苦的奋斗,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固然是全国军民同胞一致努力的结果。然而我们重庆同胞与政府同甘共苦,共患难,生死成败相一致的关系,较之其它各地尤为密切。回想敌势猖獗时期,重庆每天都要遭受敌人残忍的轰炸。市民同胞的生命财产遭受不测的损失。然而大家为表示对于抗战的忠诚,对于政府的拥护,前仆后继,效死而去。这种忠贞不二艰苦卓绝的精神,是本席梦寐难忘的。至于重庆市民在抗战期间输财输力之多,尤为全国其它各地之冠。这种伟大的贡献,在将来抗战史上必将大书特书,而永垂国民效忠国家的良好模范。本席生长浙江,从事革命起于广东;然至13岁离乡以后,即无一地连住八年之久如重庆者,所以重庆实为本席的第二故乡。……尤望各士绅同志,推老老幼幼之心,协助本市政府,妥为教养,才能安慰先烈在天之灵,也才能奖励社会的忠贞气节。最后本席谨祝重庆日益发展,重庆同胞生活日臻康乐,而成为全国模范的都市。”
资料2:
抗战胜利纪功碑碑文
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起,国民政府西迁入蜀,重庆建为陪都,巍然系中华民族命运之枢机,为国际视听所属集。日军集五十年储蓄之力量,倾孤注于一掷,中国局势,履濒危迫,而根本迄不动摇,战争之第四年,日本迁怒树敌,凶焰益张,奇袭珠港,肆扰海南。亚洲之战争既与欧洲合流,中国遂自独立作战之孤军进而为民主阵线远东之一冀,嗣此意德先后瓦解、日本亦势蹙力竭,终于偾蹶。在此八年之中,国际舆论,目重庆为战斗中国之象征,其辉光实与历史同其永久。洎战争胜利,国府还都之次年,重庆市民庆国运之重光,懔收京之不易,逮碑中衢,用示来叶。群历共艰虞,知其始末,属笔纪事,故不得辞,尝谓旋乾转坤之事业,必赖有睿智仁勇之领袖为之纲维,忠贞勤奋之人民效其心力,而地理形势亦为其助。……
当时会引曾来论地理形势之言,谓中国形势为四川为首,荆襄为胸,吴越为尾。一旦国家有事,但使首脑无恙,则扬子下游之战局无论如何险恶,根本不致动摇,重庆定为战时首都之国策,实已决于是时。国府西迁之后,敌兵深入,西抵宜昌,虽敌方之海陆军力限于夔门,而空军之战略袭击则集中于重庆。战争前期之三四年中,闹市为墟,伤亡山积。然而重庆以上百万之市民,敌忾越强,信心愈固。财力物力之输委,有逾于自救其私,实造民族精神之峰极。
古人有言,国於天地,必有舆立,重庆之所以无忝为陪都,不仅以其地理形势使然,亦此种卓越精神有以副之也。国民革命初步之成功,即为中国真正建设之开始。西南古为神州隩区,四川尤称天府;战时既已为国家之力量之中坚,战后亦将为重工业之策源·444·
地。重庆承四大河流之汇,上溯四江已达康黔滇青,下循扬子东通于海;一旦计划中之川境铁路公路系统完成,与西北西南脉络贯通,则重庆将进为新中国工业经济之重心,大西南之吞吐港,其进境何可限量。……十年之后,将见大桥横贯两江,二千平方公里,二百万市民之大重庆涌现于华西。以西南之财富,弼宗国繁荣。后世史象,循流溯源,深究中国复兴之故,将知重庆之于国家,实不止于八年战时之献效已也。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之日毂旦,国民政府主任重庆行辕兼代主席张群敬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