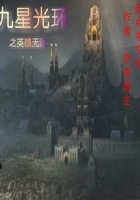「侍卫长请吩咐,今次抹绿必不辱命……」剑婢抹绿平时冷若冰霜,在黑衣男面前,却有半分惶恐之色。
「哼!」
「侍卫长不信任抹绿?」
侍卫长沉思了许久,才缓缓转过身来。他的声音非常冷森,根本不带任何感情:「哼!事关重大,今次本尊亲自出手!」
「侍卫长要上昆仑一趟?」
「哼!」
侍卫长不搭理她,直接推开了大门。
若有人正眼看向侍卫长,必定会大吓一跳。他身披一件墨黑色的斗蓬,头戴草帽,全身装束密不透风,没有露出半吋肌肤。不过最吓人的,是他居然是个无脸人;或者说,他的脸就像一个无底黑洞,没有眼耳口鼻,却有一团墨黑色的迷雾缭绕。
黑洞不断在吸缀附近的光线,以致谁人走到身边,都会感到温度骤降,异常阴寒。
幸好侍卫长的作风比较低调,他走出贵宾室时,先以一条白色绒巾遮脸,以免在街上造成恐慌。
「哈,这么巧!」
没想到一踏出贵宾室,他就发现了自己的猎物。
原来司马琼是最先一个吃饱,却没耐性等其他人用膳,便先和其他南斗子弟道别。却没想到她才踏出茶楼,进入一条较僻静的后巷,就和披黑色斗蓬的侍卫长碰个正着。
「不好意思。」侍卫长借故撞了司马琼一下。
「喂,你……」司马琼脾气差,正要骂他为何走路不长眼睛,无意中却瞥见了他的脸。
「哗!啊,我晕了……」无脸的侍卫长虽然以绒巾遮脸,但还是露出了黑洞般的额头,相当吓人。结果侍卫长毋须出手,司马琼已自动跌入他的怀中。
与此同时,茶楼内的南斗修者正在等店小二结账。
无意中,白头子留意到一个麻袋遗留在饭桌上。
「我们那一袋一直由豆腐保管,这一袋是谁遗漏的……」他们马上联想到司马琼。
白头子一直看她不多顺眼,趁机揶揄道:「哈哈,刚才硬要分开两袋,死命不让我帮她拿,到头来还是忘了带走!」
万星儿冷笑道:「我们还给人家吧。她发现布娃娃丢失了,不发飙才怪呢!」
「就是呢!我们上昆仑山是找连体姊妹,她上南斗山却为了捡破烂,就几个布娃娃。哈哈……」白头子当然没忘记自己的「驮兽」身份,女神说要还,他还不马上附和?
于是,白头子提着那袋布娃娃,出去找司马琼。
「咻咻—」
他经过那条僻静的小巷时,同样留意到黑影闪过。
「司马琼在我们『凌月宫』手上。你去放话,叫昆仑圣地交出连体姊妹!」后方响起一道非常森寒的男声。
「谁呢!?」无脸的侍卫长可真是来去如风,白头子还未瞧清楚他的面容,就已消失不见。
凌月宫的侍卫长,绝对强势的人物!女皇千里追杀亲生女儿,众御婢失败了,终于逼使侍卫长亲自出手!
******
夜天和叶长诗被关在谷底一个岩洞里,由两串大铁索捆锁,司马韬还施加了法力封印。
只不过,铁索和封印都不能真正困住夜天。现世中宗师们集体闭关,这道封印强度最多只达三阶中上,对登临四阶的夜天根本起不了作用,结果两下子就能破开。
「难度太低了,完全没诚意。」夜天冷笑连连,也解开了叶大姐的封印,一起踏出岩洞。
对他们来说,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脱离深谷。
那具残旧的浮台,似乎是连接外界的唯一途径,但浮桥已被升上谷顶,而夜天身在谷底,却找不到操作它的滑轮,看来司马韬存心要困死他们。
「这里呼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夜天悲鸣。
更悲剧的是,上方早已被无数粗大的千年老藤遮蔽,阳光根本透射不进。谷底非常幽暗,夜天即使已修到三阶,修为不弱,亦感到举步维艰。
到了现在,他终于明白司马韬为何没多在意封印的强度了。能破开封印又如何,只要未学会御空飞行,还不是一样被困谷底?
走着走着,夜天发现前方有一个黑潭,然而它死气沉沉,就像一潭死水,感受不到任何生机。这种彻底死寂的氛围,让人很感憋屈。
「下次就不管你,自己开溜算了。」夜天晦气,趁机拧了拧大妹子圆润的秀脸。
「嗐,谁让你救?」叶长诗一把推开了他。
「还说,就不该让你跟来。」夜天摸了摸脸,笑道:「下次只带二妹子,至少她比你会打,会自己照顾自己。」
「呃,你才不懂照顾自己呢!」叶长诗嘴角微噘,佯怒道:「在茶居里,是谁照顾你的?谁帮师父你老人家做饭、打扫、洗衣服呢?」
但大姐想起茶居,又不免一阵感叹。在茶居吃好住好,无忧无虑,干嘛要作贱自己,跟师父老大出来「历险」,还得身陷万丈深渊?
「我不管,总之老大你快点想办法。跟你关在一起,别人还会……误会我们哪!」她一边嘀咕,丰臀极不自然的扭来扭去,还搥了夜天一下。
夜天讪笑道:「哎啊,这里连蚊子都飞不进来,办法是没有的了,我们等死吧。」
他一时间想不出法子脱困,心情亦无比郁闷。若不是听人家说,自己的身世跟李氏姊妹有关,他才会攀山踄水,老远来到昆仑山寻人。岂料人没找到,自己却交上了一连串的恶运。
回想这几天的经历,其实也算曲折离奇,也有不少地方令人想不通。首先,「天河五煞」之一的枯藤居然被封在昆仑禁地,而他的手下青藤,很可能掳劫了李氏姊妹,藉此将夜天引到其藏身处。至于枯藤有何目的,为何要打伤他,夜天却毫无头绪,唯一较肯定的,就是昆仑圣地没「窝藏」连体姐妹,青藤才是元凶。
如果说姊妹俩本身是一个谜,那夜天体内的神秘光球,则肯定蕴有更重大的隐秘。光球是否与姊妹们有关系,有什么关连?这一切一切,又是否牵涉到自己的身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