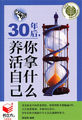我记得很清楚自己是怎么去的医学院。那天是正月十六,新年放假后的第一天,是中国传统开学读书的日子。魏表哥的太太和他的妹妹坐着她们自己的马车送我去上学。马车那时候刚从西方引进,一般认为是极大的奢侈品。因为我几乎没有什么衣服和书,所以我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马车里。我们走近医学院时,看到一栋两层楼的、半西式的房子,一块牌子上用中文写着:中英女子医学院。我离开父母和舅舅、独自来到上海找寻的医学院到了!
办完手续后,我见了X先生,又被介绍给Z小姐,她是个矮个子,说着一口很快但很差的上海话。我又和表嫂跟她小姑一起被带到住宿的地方。她们呆了一会儿,告诉我千万要把她们的家当作自己的家,又说了很多祝福的话之后走了。可我从此再没回过魏家,这有两个原因。首先是魏表哥的朋友请他作保时,他断然拒绝了。他说他不想为一个无足轻重的表妹的多种多样的麻烦事操心。在他家除了他以外,别人都对我很好,只有他对我十分傲慢,我宁可对他家的别人,特别是对他母亲显得不知感恩,也不愿意再回到以他为主人的那个家去。
我不愿回魏家的第二个原因是每次魏家的女眷来学校看我,我都窘极了。她们浓妆艳抹,珠光宝气,又缠着小脚,让我在年轻的同伴面前为自己拥有这样的亲戚感到羞愧,我的同伴跟我一样,对于她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几乎是不近人情地讨厌。但我又不能对她们说:“请你们别再来了,因为你们让我难堪。”所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回访,这样过了几个月,这些太太就不再来了。
至于三伯,虽然他常常住在上海,我不常看到他。因为他那时候正积极参加革命地下工作,和警察捉迷藏,所以我不容易见到他。
我住宿的房间里有六张床,但我只记得五个同屋中的两个了。她们是姐妹俩,姓尹,我们叫她们大尹和小尹。我都叫她们尹姐姐。大尹对我很好,要是包括她妹妹在内的别人嘲笑我,她会帮我。我那时候少年老成,一本正经,举止不脱乡土气,又操着一口常州方言,因此被上海人嘲笑。另外,我也是个穷学生,穿着旧衣服,对自己的外貌一点不在意。这些都让我成为笑柄,被那些觉得自己聪明、富有、都市化的女孩子看不起。
至于X先生的女儿,我很快就开始躲避她。她和她一个年轻的阿姨一起上学,两个人同住一间宽敞、陈设华丽的房间。她们还单独吃饭,而不是像我们那样在饭厅用餐,她们又有自己的贴身女佣,总而言之生活得像公主一样。她们有与魏家的女眷同样的庸俗虚荣心和对财富的炫耀,但却没有她们的善良和慷慨。从第一次见面起我就认定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我们始终没成为好朋友。
我交往最多的是尹家姐妹、一对表姐妹唐小姐和刘小姐,以及宋小姐,她们都和我差不多同龄。我们成了一个小集团。因为年龄和端庄的举止,大尹是我们的带头人。我唯独在她面前觉得谦卑,她也是我唯一像孩子一样崇拜的人,尽管我对小集团里的别人也挺喜欢,特别是宋小姐后来成了我最好的朋友,直到她几年前不幸亡故,当时我已经在美国瓦特大学读书了。
学校的主课当然是医学,分成中西医两系,由X先生和Z小姐分别担任主任。他们不仅是主要负责人,而且在医学院成立的最初两年里也是唯一的医学教师。
Z小姐精力充沛,可是华而不实,缺乏一个领导者所必要的坚忍不拔的性格。不管是否与医学有关,她什么都教我们,而且都同时进行!但因为她自己知识浅薄,而且几乎完全不懂怎么教学,她只当成了个很差的老师,让我们都恨她教的任何东西。可是,因为我们都是新来乍到,没有人知道一个现代的学校应该是什么样的,因此我们接受了学校从课程到穿着的一切安排。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们是中国当时尚在婴儿时期的新式教育机构和一个经验不足的老师的牺牲品,她浪费我们时间和精力的唯一可能的借口是她完全没意识到她对我们的伤害。她坚信自己开办这所女子医学院是对社会的一个重大贡献!
在这里我要举例说明那儿对医学的完全不科学的教学方式。我们的化学课连一个试管都没有,我们只被要求背诵所有化学原素的中文名字,它们的特性和相互之间的反应。医药学方面也只是死记硬背,各种药的名字,它们的样子,它们能治的病的名字。解剖学的课本有三大本,这并不是简单的生理学课本,而是描绘了人体的每块肌肉和骨头,叫做《人体构造学》,是由某个医学传教士从英语翻译过来的非常专门的研究性书籍。Z小姐让我们把这些全部背诵下来:不仅是一百多块骨头和五百多块肌肉的名字,而且是它们附近连接着什么肌肉和骨头。我们被要求全部背诵时,除了书里的几张简图外,连一张人体图都没有,更不用说人体和有关部件的蜡制模型了。
中国人当然从小就要背诵文学经典以打好教育的基础。但不管那些作品有多难,它们至少是文学,就算不押韵也有自己的节奏,因而我们可以用大声朗读来记忆。小时候父亲让我背诵那些历史地理名字的时候,我以为自己攀登了不可跨越的高峰,现在才知道那只是为Z小姐打前站!幸好因为我有跟父亲读书的经历,而我的头脑还年轻敏捷,所以我觉得记住那些奇怪的名字术语还不太难,常常能记得功课的五分之三到四。因此,我被认为是全校最聪明的学生,还得到一块金表作为对我好记性的奖励。
Z小姐也是个没有规律的人,常常心血来潮地让我们一大早,比如五点钟,上课。我们这些无知胆怯的女孩把任何命令都看成新学校天经地义的事,完全照办。我们在冬天早晨的黑暗中颤抖,在烛光下用冷水盥洗,然后不吃不喝准时集中在煤油灯下的教室里。下了课,Z小姐会回房去睡觉,可能睡到中午才起床,我们当然不能照办。
学中医时,我很幸运的是唯一读过《黄帝内经》而且能记得其中三分之二内容的学生。X先生知道后非常惊奇和佩服。因为他自己从没有背诵过这本书,他开始在我面前觉得不好意思。这种情况对我来说十分尴尴不幸,因为无论何时我有什么严肃的问题要请教他,他总是从眼镜上方瞪着我,甚至说:“小姑娘,你在考我吗?”
但他为人和气,是个中国人说的“儒医”。他考虑到年轻人头脑的局限,所以对我们要求不太高。他教课的时候也很平静有序,因此我们在他的课上也心绪平静,甚至有时喜欢上他的课。他教过我们的一本书讲的是如何治伤寒,我还记得其中有一条训示是:“不要测体温!”
我们的第三个老师是刚从美国学成回国的Y小姐,她也是唯一懂得怎么教书的老师。她的主课是英语,但她也教我们数学。我学英语是从头开始,我们的课本叫《基础读本》,字母表之后的第一课是:“一只猫,一只老鼠,一只猫和一只老鼠。”(“A cat;A rat;A cat and a rat”)读完这本书后,她让我们读当时在上海的中国学校里非常受欢迎的《博德温读本》(Baldwin’s Readers)系列。半年到一年后,我们又学英语语法,用的课本是内斯菲尔德(Nesfield)的《英语语法》(English Grammar)。三年后她离开我们时,我们已经几乎读完了《博德温读本》系列的八本书,也完全读完了《英语语法》的四册。
Y小姐是个能干的老师,她不仅让我们注意每句话怎么翻译成中文,而且注意每句话的结构。她让我们反复抄写一句话,开始是写简单而短的句子,然后是复杂而长的句子,以便我们体会如何用不同的方式充分表达一个事实或一种感情。
Y小姐和Z小姐好像不太合得来,当她在年底(我不记得那是第一年还是第二年)提出要离开时,我们都哭着求她别走。只有她的课我们喜欢,X先生的课还可以忍受,Z小姐的课那时我们完全无法应付了。我猜不管一个人多么坚定,如果一群真诚的女孩子哭着恳求她别走,她大概不会忍心离开吧。因此Y小姐留了下来,又教了我们两年,所以她一共教了我们三年。就凭着我在英语方面的这点薄弱的基础,我后来通过了政府的考试,赢得奖学金于1914年夏天去美国留学。
虽然学校里没有化学或解剖学的实验课,但因为Z小姐开业行医,我们有很多和病人接触的练习机会。不幸的是,我是个非常敏感的孩子,家里又曾出过不少艺术家,所以如果我碰到的病例是手术甚至分娩,我会觉得那种经历十分令人作呕。因为我比班上其他学生都小(我们是正式班的学生,包括尹家姐妹、郭小姐、吴小姐、姚小姐和我),我请求Z小姐考虑我的年龄让我先免于医疗实践,并保证一年以后参加所有实践,但她不愿为我破例。
Z小姐是个好恶极端的人,不幸的我成了她爱恨的牺牲品。她高兴的时候,我是神童,她生气的时候,我是班上的害群之马。她会把学校发生的一切不寻常的事说成是我的责任,不管是谁打破了一件名贵的瓷器还是谁在她花瓶里插了朵漂亮的花。某天她会代表学校发给我一个金表,奖励我的功课做得好,第二天她又会因为我胆敢不听话跟她顶嘴威胁要开除我。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意识到这个学校教学方式的荒谬,我不希望被开除,所以我能做的就是随大流,我的同学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我最害怕的是夜晚的分娩。Z小姐被从梦中叫醒去病人家时,总会变得很暴躁,常常毫无道理地严厉训斥我们。而且,因为西医和手术那时候在中国还处在起步阶段,几乎所有人都只有在中医或接生婆无济于事时才找西医。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病人一般已经生命垂危,我最怕的就是这种情况,特别是因为我从没见过正常状态下的分娩。
但更糟糕的是,我们六人并非轮流出诊,而是一有病人就同时出发。到了病人家,我们都得站在Z小姐周围,听她尽可能清楚地解说。但我常常是又困又冷又饿,对整个过程十分讨厌。我会自我安慰地发誓第二天就退学,所以Z小姐的话听不听都无所谓。因为我比别的学生矮,我会站在她们身后,多少躲避开那种令人恶心的场面,可是那个受苦女人的尖叫和呻吟像钢刀一样刺透了我的心,而且取出的婴儿或者已经死了,或者被切成几块,或者因为父母的什么病已经腐烂成青紫色。我们目睹的病例没有一个是正常健康的,因此我自然相信孩子都是这样出生的,并且把分娩看做世界上最可怕的事!
如果我生来就渴望学医而我的父母又希望阻止我,那他们再不会找到比这个医学院更合适的地方来达成他们的目的了。但更不幸的是,我本来就不想学医。加上对肌肉和骨头的死记硬背、Z小姐心血来潮和缺乏人性的教学方式、和我以上描绘的可怕经历,我心里脑中很快完全没有了任何学医的欲望就不足为奇了。我当时下定决心,不管以后我学什么做什么,总之一定要跟医学完全无关!
但我直到三年后才离开那个医学院。其中的原因不难解释。首先,我说过我不知道学校应该是什么样的,所以不信任自己的反应,又没有长辈可以商量,因此不敢为所欲为。第二,我仍然记得舅舅警告过的我的短处,主要问题是我缺乏耐心。所以,当有些人再也不能忍受,请我跟她们一起离开学校时,我说:“我得训练自己的耐心!”有时候我甚至相信那些可怕的经历是上天安排的考验,我应该习以为常。第三,要是我离开这个学校,又能去哪儿呢?去家人居住的四川成都?那我为什么从前要冒犯父亲不肯早回去呢?我又从中得到了什么?去广州?舅舅对我一两年前拒绝他亲自教育我的慷慨好意、不愿留在他家,现在却一事无成地回去会怎么想?转学吗?谁又会帮我解决实际的经济方面的问题呢?本来就对我不满的父亲难道不会更不愿出钱?如果父亲停止了经济方面的资助,舅舅看到我缺乏耐心还会愿意帮我吗?我怎么才能让他相信医学院内外的种种荒谬绝伦的事?他和父亲会不会认为我每过几个月就要转学呢?
不行,我除了呆在这个学校外别无选择。三年以后,我十七岁了,父亲突然命令我马上回成都的家。他接二连三地给我发电报,甚至在最后一封电报中威胁说要是我不回家,他就停止经济资助。因为舅舅当时已经按照先前的约定停止了对我的经济资助。我只好打好我的少许行李,登上了去汉口的蒸汽机船。直到回家以后我才了解父亲命令我回去的原因。他觉得我到了该订亲的年龄,但他了解我的个性,因此不愿意不经过我的同意就给我订亲。他知道要是他那样做,我会顽固地留在上海,就算他不给我经济资助我也宁可饿死决不屈服。如果我离得那么远,他当然对我无能为力。
虽然我在那个医学院的经历并不愉快,它还是象征了我所追求的东西,所以我离开时的轻松感中也夹杂着悲伤和失败感。幸运的是,Y小姐正巧教完三年,根据她跟Z小姐的约定正式离开那个医学院。因为她去汉口过新年,我选择了相同的轮船,和她一起旅行到汉口,她住特等舱,我在普通客舱。我不仅享受了跟她一起旅行的特权,而且心里还不无恶意地高兴地想:就是我留在那个医学院,也不会有Y小姐教课了,而Y小姐的课一向是使那个学校还可以忍受的唯一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