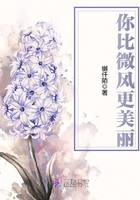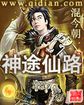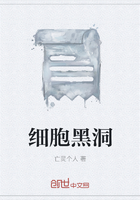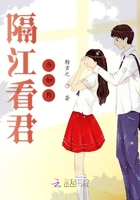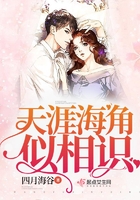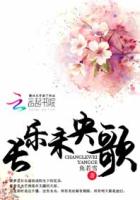在秦惠文王于公元前325年正月称王后,“四月戎午,魏君为王,韩亦为王”。“其后诸侯皆称王”。这给秦惠文王敲响了警钟,各诸侯国不甘示弱,纷纷争雄。形势迫使秦惠文王争雄于各诸侯国的忧患意识。要率领军马回雍州祖庙祭祖,三畤原祭天、陈仓祭地、祭陈宝,用神灵、宗教统一秦人秦军的思想,用狩猎活动演练秦军将士。
那么,此次“西巡猎祭”当为何时?从以下便可证明,当为此“丙申”年的夏季仲月,即五月仲夏了。在《石鼓文》中就能找到依据:《乍原》诗中“亚若其华”,即好象美丽的花朵;《马荐》诗中“马荐”,即青草丰盛碧绿;《吴人》诗中“勿勿代”,即既要祭祀灶神,又要祭祀其它神灵。为什么在此只提灶神?《礼记·月令》中载:“仲夏之月,日在东井”,“其祀灶、祭先肺。”①即五月仲夏,太阳的位置在井宿,夏天祭祀的对象是灶神,祭品以肺为上。这些就能证明此次“西巡猎祭”是在公元前325年的五月。另,《汉书·郊祀志》载:“故雍四畤,春以岁祠祷,因泮冻,秋涸冻,冬赛祠,五月尝驹,及四中之月月祠。”②其中“及四中之月月祠”就是说一年四季中的中间一月祭祀,夏季中间一月便为五月。“五月尝驹”,即五月尝两岁的幼马。五月是仲夏之月,亦为榴月。故此次秦惠文王“西巡猎祭”便在前325年,此“丙申”年的五月。
出行的状况如何?“猎祭”的军伍是精选了的“工车阜马”;秦惠文王乘座的“銮车”“四马其写”、“六辔骜骜”、“左骖騚騚”、“右骖馯馯”……秦王之师从东方的咸阳宫出发,一路西行。其军伍车骑浩浩荡荡、旗帜飘扬,荡起烟尘蔽天;长途跋涉,经过两天的行程,前往雍城、三畤原、陈仓。
此次为“猎祭”。“猎祭”是把祭祀同狩猎结合在一起的。前文已经述及,秦人崇尚祭祀。其实祭祀是利用上帝、神灵在做人的工作。这是人类从诞生以来思想发动和思想统一最锐利的武器,使用的时间最长、长盛不衰。秦人对此武器掌握得最牢靠,运用及时,能发挥最佳效益。狩猎实际上是在练兵,做军事演习,提高战斗力。这次猎祭对刚刚称王,别的诸侯国继踵称王的秦惠文王,意义绝非一般:既荣耀显赫,又心有忧患;既是炫耀,又在收笼人心;既告神灵,又演练兵马。
此次猎祭持续了好多天,秦王之师,从咸阳宫出发,浩浩西行,途经“郿邑”,“舫舟西逮”在渭水西行。在雍州、三畤原、陈仓祭祀。庄重的祭祖、祭天、祭神灵。在河捕鱼,在陈仓狩猎,还顺便祭祀了“陈宝”……对此般重大事件,秦人史官采用《诗经》般高雅优美之诗,予以记述,镌刻在十枚硕大的圆石上,“刻石记功,志碑传远”。这便是被后人称颂的《石鼓文》。
“书家第一法则”的确立
上述,我们确定了《石鼓文》具体的制作时间,即《石鼓文》产生在战国中期,具体的说,《石鼓文》是公元前325年五月制作的。这就为我们具体的考量其为“书家第一法则”提供了坚实的依据,不是凭印象来谈“书家第一法则”的。这就能用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具体的参照,尤其是战国早期之前的大篆、金文作比较,来确定其是否为“书家第一法则”。从比较中,我们就能看出《石鼓文》作为“书家第一法则”的极具个性特点的不同之处。
一、之前的甲骨文、金文,均属刀刻或铸造;《石鼓文》明显有了笔意,这在《石鼓文》之前是没有的。遍寻甲、金资料,未见有笔意,只有《石鼓文》,笔意浓浓,让后人看见了书写状。
二、之前的甲骨文、金文偏旁部首没有固定、随意性强,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石鼓文》的偏旁部首已经固定,使人有规律可循。如运用最多的“马、车、鱼、辶、水、走、阝、木……”
三、之前的甲骨文、金文中均或多或少的羼杂象形字;《石鼓文》已经完全用线条来书写,象形字的痕迹已经蜕尽。
四、之前的甲骨文、金文形体多变,或长、或扁、一器一形;《石鼓文》已经固定成汉文字的基本方块字。
五、之前的甲骨文、金文结体多变,或疏或密,随意变体;《石鼓文》的结体,疏密有度,随意性大减。使观者觉得疏密适量,即平和却又雄强。
六、之前的甲骨文、金文线条多变,或粗或细,有时一小黑点可代表一横画或一个字;《石鼓文》的线条粗细已经基本一致,相当的协调,但却不死板,运用“飞动”、“活泼”,却又基本一致的线条。
以上六点,便确定了《石鼓文》在中国汉字书法史上的最高地位,既“书家第一法则”的地位。
“书家第一法则”内涵的初探对被康有为称为“书家第一法则”的《石鼓文》书法艺术的内涵,余猜度多年,试图从以下几方面试探:
一、在章法布局上:《石鼓文》有行有列,规整庄重、古茂雄秀却又随形布局。汉文字从启蒙时新石器红陶钵口黑色宽带纹上的符号开始,就做到了随形布局。至成熟的甲骨文、金文更是如此。古人根据龟甲片的大小,青铜器饰字的部位,合理随形布字,均恰到好处。只是那时大多有行无列。即字竖有行,横不齐。到金文鼎盛时期及后期的文字,亦有行有列。如胡簋、墙盘、逨盘、虢季子白盘、秦公鎛,中山王鼎,中山王壶、壶等。只是那时的器物,均一器一形,一器形一文字布局,并非统一。像《石鼓文》此般成十篇幅的巨形书法作品尚属首次。
此十枚石鼓尽管均做鼓形,但大小轻重不一,最小的200多公斤,最大的400余公斤,高矮不同,布局上全不一样,做到“有行有列,规整庄重,古茂雄秀却又随形布局”
二、在字体的结构上:《石鼓文》首创汉字严谨结体,为后来小篆、楷书树立典范,打下基础。试想没有《石鼓文》的首创结体,那么小篆将是何等模样,也不会是“或颇省改”即成的小篆。张怀瓘“仓颉之嗣,小篆之祖”的结论是准确的。此处参照金小萍《石鼓文临写法》①在此,使人联想起初唐书法家,书法理论家欧阳询着名的《三十六法》。看来《三十六法》中所形成的理念,在《石鼓文》
中已经首先体现出来,只是至初唐才被此一代宗师欧阳询明确地提出,并形成了理论。那么,《石鼓文》的首创,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三、在用笔上:《石鼓文》更创新路,为之后的小篆楷书淌开先河。古贤在书论中提出:“书法无它秘,只有用笔和结字耳”。前文述及结字,本条即述用笔。《石鼓文》用笔线条饱满圆润、笔意浓厚,多用曲线。其曲线变化众多,弧度优美、方而不矩,转角多用圆,线条遒劲有力,“折直劲迅,有如镂铁”。起笔藏锋逆入,欲右先左,欲下先上。收笔回锋疾提,或小驻顿笔后疾提。各种曲线,即弧笔,亦逆入后,用捻笔圆转。而半弧、环弧、圆弧多用接笔。长弧、曲弧均逆入,捻笔后,回锋疾提。笔速适中,因捻笔而保持中锋用笔,笔力得宜,不露圭角。“劲者山立,柔者禾垂。”
四、在笔意和笔势上:《石鼓文》自有其采。笔意和笔势的关系是,笔意体现在笔势中,笔势是笔意的反映。那么《石鼓文》的笔势和笔意如何呢?吴昌硕对《石鼓文》用四个字便归纳了出来,即《石鼓文》“古茂雄秀”。大凡书家均知:颜真卿的楷书“雄劲”;王羲之的楷书“秀逸”;铁线篆如唐孙过庭言“篆尚婉而通”。而三者兼而有之的只有《石鼓文》,况其“古茂雄秀”。此便体现出《石鼓文》的书者当时的心境,既平和、又极具向上力。书者的技法娴熟,用墨亦不愠不火。笔意和笔势运用到炉火纯青,以至出土1300余年来,使无数的书家倾倒膜拜,至今未见临贴者能与之比肩。
五、在《石鼓文》的书法风格上:论者甚繁。由于他们没有弄清《石鼓文》产生的具体年代,也只能从直观的感觉中,对其风格加以论述。如唐初苏勖云:“虞褚欧阳共称古妙”;唐张怀瓘:“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又云“折直劲迅,有如镂铁,而端姿旁逸,又婉润焉”。元潘迪:“其字画高古”。清孙承泽:“遒朴而饶逸韵”。清方朔:“劲者山立,柔者禾垂,行若奔云,止若据槁”。清刘熙载:“如龙腾凤翥”。清康有为:“金钿落地、芒草团云”……上述古人,或从笔画、笔意、笔势上说:或从结字上谈;或就整体感觉言;或是归纳总结,都是对《石鼓文》风格的评价。对《石鼓文》的风格亦少不了吴昌硕的“古茂雄秀”。这也是其风格的最好表述。其实细观其文十篇,也有区别,不尽相同,最好的当属《而师》《銮车》《吴人》
《车工》《零雨》《马荐》;其次是《吾水》《田车》;再次是《乍原》和《沔》。最能反映《石鼓文》风格的当是前6篇。说明十篇《石鼓文》可能不是一个人书写或不是一个人一次写成。故对《石鼓文》十篇笼统戴一顶帽子也亦难全面;而全体论《石鼓文》的风格也无可厚非;或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石鼓文》的出土地点考
对《石鼓文》的具体出土地点,从唐武德年间或者再早一些时间《石鼓文》出土后至今,外地学者基本上无多大争议。原因是“石鼓文在县南(天兴县)20里许”,“近在关中”“陈仓籍甚”“陈仓石鼓”云云,都肯定了石鼓文出土的范围。因为雍城(凤翔县),唐肃宗至德二年析雍县增设的天兴县,陈仓县(宝鸡县),都在今日的宝鸡市范围之内,故外地学者的认识是趋于一致的。而对石鼓文的出土地点之争,多是宝鸡境内的具体地点问题。即具体的是石鼓山、凤翔县南20里,魏家崖,或其他什么具体的地方。
《石鼓文》出土地点的研究,除了必须的证据之外,尚须和《石鼓文》的制作年代及主要事件联系起来看。正因为如此,郭沫若把《石鼓文》之制作年代定在秦襄公八年,即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秦襄公作西畤时所作,对《石鼓文》的出土地点他述为“据《元和郡县志·天兴县下》云‘石鼓文在县南20里许,石形如鼓,其数有十’。唐天兴县即秦雍县,石鼓所在地则所谓三畤原也。”凤翔的学者便以此为据,称《石鼓文》出在凤翔城南20里。李仲操先生研究《石鼓文》多年,把《石鼓文》的制作年代定在秦宣公四年,即公元前672年,认为这是秦宣公在渭河南作密畤时所作,证据有唐代着录、明、清的《凤翔府志》
《宝鸡县志》,清嘉庆十三年《重修石鼓寺记》的碑文。以此确证其出土地点为宝鸡市郊东南十余里的石鼓山。蒋五宝先生的《陈仓石鼓新探》亦作了具体考证,认为《石鼓文》当是秦文公二十一年(前745年),为纪念国都——渭之会落成而刻制的。出土地点便确定在河东岸的魏家崖。这些学者的研究,特别是国内外着名学者郭沫若的研究,对《石鼓文》的研究提出了思路,作出了铺垫。我的《石鼓文》研究亦是在李仲操先生的带动下进行的。据我对《石鼓文》的研究,据秦惠文王称王当年回凤翔祖庙祭祖、三畤原祭天、陈仓祭地、河鱼祭、陈仓祭陈宝、鸡峰山北麓打猎的主要事实,对其出土地点提出以下观点:
先按着录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看:
(1)初唐,武德年间(618年~626年),吏部侍郎苏勖记打本(拓片)石鼓文卷首云:“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此记石鼓在“关中”。
(2)唐永徽三年(652年)章怀太子李贤在《后汉书·邓骘传》注中谓“今岐州石鼓铭”。此记石鼓在“岐州”。
(3)唐李嗣真(?~696年)在《书后品》中说“史籀堙灭,陈仓籍甚”。此记石鼓在“陈仓”。
(4)唐开元时(713年~741年)的张怀瓘在《书断上》载“甄丰定六书,二曰奇字是也。其迹有《石鼓文》存焉。盖讽宣王畋猎之所作,今在陈仓。”此记石鼓在“陈仓”。
(5)唐代大诗人杜甫(712年~770年)在《李潮八分小篆歌》开始称“苍颉鸟迹既茫昧,字体变化如浮云。陈仓石鼓又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此直称其为“陈仓石鼓”。杜甫在此诗后边云“巴东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杜甫在巴东的时间当在765年至768年之间。
(6)唐窦蒙在其弟窦臮《述书赋上》作的注文中云“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十枚,并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见打本”。此书《述书赋下》云“大历四年七月点发行朱。”大历四年(即公元769年)“点发行朱”,即点圈终止。就是说窦氏兄弟的此书是公元769年写成的。此记述石鼓文在“岐州雍城南”。
(7)唐代方志着作《元和郡县图志》,成书于元和八年,即公元813年,因北宋的后图佚,又称《元和郡县志》在天兴县下载:“石鼓文在县南20里,石形如鼓,其数有十”。此记“石鼓文在天兴县南20里”。
当然,唐代着录石鼓文的还有其它着作,如韦应物、韩愈的石鼓歌等,他们均以为是周宣王的刻石,看的亦是拓片,没有明确的出土地点。这里只选录其有明确出土地点的七条。此七条中:(1)言“在关中”,(2)言“岐州石鼓”。“因陈仓在关中西部,于唐时属岐州九县之一,此为大的地域概念。”①李仲操先生的上述见解无错。(3)言“陈仓籍甚”,(4)言“今在陈仓”,(5)言“陈仓石鼓”。均明确记载石鼓文在陈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