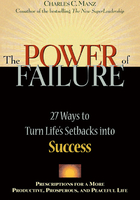瘦子踌躇的站住了。她即刻转身向他点点头,走进门,隐藏了半个身子在门后,嫣然的低声说:“请进来呀,不要紧的!”
瘦子大胆走进去了,门关了,里面是欢欢喜喜的,外面是太太平平的,然而不久,来了一个维持治安的警察。
他是附近的站岗的,他早已看清楚了这幕剧,然而这对于官厅是违禁的。他耐得烦在这家人家周围逡巡着,向门隙里张望着,在屋后的窗下倾听着。
“妈,客人来啦。”翠花婉转地欢呼着把瘦子引进房。
瘦子是长于跟女人游戏的。这样的溜进女人房里也不是破题儿第一遭,女人,他很欢喜的,至于赔本跟女人去周旋,却为他所不喜。在翠花的大方的呼唤声中,他早已分晓这女人是不是属于他所欢喜的一类的,但是既来了,也只得瞧着办。
母亲端了一杯茶和一盘瓜子进房,便走开了。翠花陪瘦子坐在梳装台两边,彼此互看了一眼,她开始问:“先生贵姓?”
“吴。”
“在那里得意?”
“没有得意过,打流,吓吓,你贵姓?”
“客气!客气!——我姓刘。”
“你的芳名是——?”
“翠花。”
“呵,翠花——好漂亮的名字!——人更漂亮呢!今年几岁?”
“十九,怕不相信吧?”
“不相信,还不到呢!——你的先生……”
“我还没有——”
“那末,你是在学校里读书的吗?”
“书是读过的。”她红着脸,低了头弄衣角,立即又抬了一下头,眼睛瞧着梳妆台,手在台上画着,一壁说:
“原先我在初等毕过业,到十三岁,父亲死了,没有法子,后来就跑到这条路上来啦。家里有母亲,有弟妹,要吃饭阿,先生!要是肯帮忙,能够留在这里,真是感激不尽!”
“那倒也无所谓帮忙,只是——”瘦子吞了下半句,瞧着翠花苦笑着,随即伸了伸懒腰。
“请到床上歇歇吧。”静默了一阵之后,翠花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颇有点过意不去。她走出房,让他去考虑一下。她走到母亲那里,将情形报告了,两人脸上浮出欢笑来。总之,瘦子即令不留在家里,只须给一二元茶围钱,目前就一切都没有问题了。
瘦子横躺在床上,心中也不算很冷静。原先是只想怎样能开脱,只想怎样使他那皮匣的四五块钱没有丝毫的损失,然而现在觉得绷子床还柔软芬芳,屋子还干净华丽,女的脸子也不错,也读过书,穿着还雅素,娇小伶俐,怎见得比女学生少奶奶减色?玩玩女学生,吊吊少奶奶怎见得不花费分文?况且那全是享乐,这则除享乐之外而对于某一方面还有所谓“帮忙”的性质的,花两块钱他是已经决定的了,但也不情愿白送掉。当翠花进房坐在床沿了,他开始握住她的手,摩抚着,渐渐的由浅入深的逗她,将她攀倒,做出各种的游戏,且交谈着。
“你们在这里多久了?”
“三四年了,原先在秦淮河夫子庙一带住,是一礼拜前搬过来的。”
“听说干你们这种事的近来不大方便啊,为什么不到妇女习艺所里学一门正当职业,或是到落子馆里去唱唱?”
“还讲得到方便,唉,不准登在南京末,简直,连暗的都得查禁呢!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要养活一家人,进习艺所能养我一家吗?能使我的弟妹上学吗?如果能,再好没有,我进习艺所就是。至于落子馆,我嗓子不好。像她们,唱完了落子,还不是依然干我们这样的事?我以为如今当官的也真有点奇怪,把我们赶走,不准挂牌子,罚钱,拘押,那向真吓得够了,可是唱落子的那种办法他们倒赞成,哈哈哈!真奇怪!”
“落子馆里姑娘们是在那里说书劝世,不准穿着得奇形怪状,不准唱淫词浪调,究竟和你们两样一点的。”
“什么两样,一个模子,我到过那里,她们说的什么书,简直在那里唱戏,有些戏还是客人点的,一块钱一出。”
“你的话固然不错,但那究是官厅许可的娱乐机关呵!”
“所以我说如今当官的就有些奇怪啦。——如今我也什么不埋怨,我只埋怨我父亲死得太早。要是他能够使我在高等里毕过业,学了三民主义,那我也就用不着干如今这个路。我同乡的一个姑娘和我在初等里同过学的,年纪比我大两岁,可是她在高等毕过业又进过年把中学,听说她在湖北干过宣传科呢!百几十块钱一月,多惬意!不过声名也不大好,听说她在外面姘了数不清的同志,这和我们又高超了多少?”
“那是恋爱啊,恋爱是很神圣的。你知道吗?”
“我知道的,一个男人勾搭上一个女人,这就叫恋爱,勾搭不上女人,就去找窑子,这就叫做嫖,比如客人爱了那窑子,窑子也爱了那客人,这也还是叫做嫖,因为窑子是要钱的。但是他勾搭上的那个女人多半是有钱的,有饭吃,当然她不要钱,甚至倒贴钱都可以,但也得请她吃大菜,看电影。若是那女人境遇不好,你得供给她的衣食,若是和她正式结了婚,还得养她一世,这就不算嫖吗?——先生,您今天肯上我这儿来,总算看得起我,而且我是很爱你这种人的,你很爽气,我求求你把我们这回事也看成恋爱吧,犹如你和没有钱用没有饭吃的女人恋爱了吧,你也不必把它看成神圣,只须把它看成慈善事业就得了吧。——你晓得我们当窑子也不是没有一点骨气的,我们不像那些已经嫁了的女人,背了男人跟姘头跑,一辈子不见自己男人的面,我们只要那客人认识我,随他那时欢喜我,他就可以来满足了去,只要他每次给我们袁世凯。——我晓得你先生就是为着这一点看不起我们喽!但是,在从前孙传芳坐南京时代,我们生意好,很好混,我们也晓得摆臭架子,呃,不是知心的客人,我们也不轻易留住的,可是如今不同了,不准挂牌子,又什么都贵了几倍,所以,我们很苦楚,先生,只要您愿意,我总不会忘记您请帮帮忙留在这里吧!”
“无所谓帮忙,我曾对你说过的,我也不是不愿意,我听了你一番话,我不但欢喜你,还很佩服你,可是我对你说过的,我在打流,我没有许多袁世凯,我身上只有五块钱,我赌咒都可以的,等明天设了法再来吧,对不起得很,明天准来就是!”
“你真的有五块钱吗?先生,哈,哈,哈,这就够了,你打流,我知道你不是连晚饭米都没有的;我们要吃饭,你也要吃饭,全都要吃饭,你没有多少钱,我们也不会剥你的皮,是不是?好!我们不讲钱多少,你就留在这里吧!”
她嬉笑颜开的说,一手搭在瘦子肩上,把脸凑近他的脸,亲密的和他吻了一吻。
这时大门忽然有人重重的敲了二下,他母亲去开了门,进来的却是个警察,接连又一个,还有一个在门外,是原先那个站岗的。
“有什么吩咐我们吗,巡官?”
“我们是调查户口的,你们家里有几个人?这里就只你一家吗?”
“就只一家,我有二个女儿,一个孩子,连我自己四个。”
“你的女儿多大?孩子多大?”
“大女儿十九,孩子十二,小女儿才八岁。”
“那末,刚才进来的男子是谁?”
“是——没有,没有男子进来啊!”
“瞎说,明明有男子进来的,跟在一个女子后面。”
翠花给房外的盘查声惊骇了,从床上跳起来,向房外偷看了一下,即刻脸色苍白了,战栗的轻轻奔到瘦子前嗫嚅的说:“见鬼,巡警来了,真倒霉,我们还是大大方方走出房吧,免得他们搜,你答应是我哥哥就是。”
瘦子昂然走出房,不久翠花也走出房,于是巡警走近瘦子说:“你是谁?”
“我是我。”
“呵,你是你。这女子是谁?”
“是我妹妹。”
“这太太是你什么人?”
“是我母亲,怎么样?”
“不怎么样。”
巡警忍耐着,回头对翠花的母亲说:“你不是说你的孩子十二岁吗,”说着,用手指着那瘦子“看他的样子,就连二十三十也有啦,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
“十二也好,二十三十也好,这全是我们自己的事,大概也不妨害公安吧?”
“什么?不妨害公安?你说的!可是公安局里不能由你这末说,你们应该明白你们干的是什么?不必费话啦,走,走,一起走,一起走。”
这屋里登时起了一阵无谓的纷乱:母亲作出下贱的样子,噜噜嗦嗦哀恳着:瘦子换了柔和的态度,镇静的分辩着;翠花两手捧着脸,低声的饮泣着。但不由人噜嗦,不由人分辩,更不在乎那低声的饮泣,全都应该走,留了一个警察守着门其余两个押着她们走。
正要回家的阿富和妹妹在门外的微光中瞧见了这一队,阿富奔着喊:“姆妈——阿姐——你们还到什么地方去啊,这时候,——我们饿透了,晚饭呢?”
他抢过警察前,拖住母亲的手,嬉皮娇戆的纠缠着,那赶不上阿哥的小女孩却哇的一声哭倒在远处的街旁,尽在那里放赖。
一九二九,五,三十。于上海。
(原载一九二九年八月《新女性》四卷八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