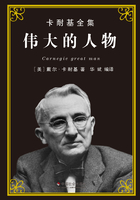她心中一荡,不确定他是否已经得知了什么。
咽了咽口水,迎着逼视,她喘了口气,清脆回答:“林砚,我未婚夫叫林砚,他也是我上司和大学学长,这次我是跟着他一起来的。不信你可以去安小姐那里查,是不是有这么一号人。”
“哼!”回答她的,只有一个不屑的语气。
他没再说什么,而是转身走到书桌前坐在,姿态慵懒地靠在椅靠上,手垂在椅侧下,将那支没点燃的眼搁在桌面上。
粟薇薇被他捆成一条毛毛虫,在地摊上蠕动了几下,没挣开,双脚又无法站立,只能仰面躺在地上,滴溜溜的眼珠子转得飞快。
她不知道那声哼,代表是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该死的男人到底有没有发现异样,或者说,他什么都没发现?
“喂!我真的不是故意冒犯你,把我放了,我会给你赔礼道歉的。”眼看男人自从坐在书桌上就没动静,她呆了一会,开口试探。
“闭嘴!”暗哑的声音含着不容置喙的霸气命令。
这个声音……真像纪程然的,不过他是不会用这样恶劣蛮横的语气,跟她说话的。
除了担心纪程然的安危,她现在又面临着能不能脱身这个困难。饶是她心思活络,一时间也没了主意。
看这情形,他应该暂时不会对她做什么。
粟薇薇壮了壮胆子,又说话:“我可以闭嘴,你能不能先把我松开,刚才绑太紧,血液无法顺畅流动,我手疼腿疼,腰酸背痛,脑袋也晕晕的。”
既然不能来硬的,索性就先示弱,反而女人装装柔弱也不可耻。
“真的,我刚才后脑勺撞到地上了,现在很晕沉,很可能会摔成脑震荡。还有脖子,刚才被刀刃划了下,已经伤到动脉,我感到血液源源不断流出来,再流下去,你就算不杀我,我也会休克死去的……”
他越不搭理,她就越喋喋不休说个不停。横竖一个态度:你不放了我,我就烦死你!
书桌前,男人缓缓睁开眼皮,目光停留在地上那一团桌布上。
已经很多年,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这样聒噪吵闹了。
无论她是什么人,只要他想捏死她,几根手指就足够了。但这一刻,他却突然打消了主意,也不去理会,就那样任她一个人在那里自言自语,说个没完没了。
到了后半夜,粟薇薇口干舌燥,像是被人塞了一把沙子,喉咙干哑再也说不出话来。
她颓然不已,跑也跑不了,现在连话都说不出来,万一大小姐他们发现她丢了,上来找她时,岂不是连救命都喊不了?
越想越后悔,差点没把肠子悔青了。她发现这一晚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后悔中度过的。
巴黎的冬天没下雪,不代表就不冷,尤其对于从小在南方长大的她,更是受不了冷。前半夜被他丢在地上,就算有地毯,也浑身冻得瑟瑟发抖,四肢早已麻木冰凉僵硬。
身体上的不适还是其次,心灵上的折磨才更致命。
她多希望,纪程然能够像往常那样,在她身陷危险时突然出现,像救世主拯救她于水深火热。
她等了整整半夜。
如果他没事的话,一定会来救自己的,可她等了这么久,都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纪程然,你还好吗?
想着想着,她的眼皮不由自主慢慢阖上,中途勉强撑开了几次,最终都无济于事,折腾了一晚上,最后还是捱不住困累交织,身体扭成一团,沉沉睡了过去。
黑暗中,男人站起来走到她身边,居高临下打量她,面具下的俊眉,以微不可见的迹象拢在一起。
点了根烟,放在嘴边吸了两口,他收回目光,冷酷不语,迈步往甲板外面走去。
这一夜过得极其漫长,又似乎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天就亮了。
当粟薇薇再次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日上三竿,温暖的阳光从窗户外面照射进来,打在了她的头顶上,洒下一室光辉。
她揉揉眼睛,脑子还有些混沌,初醒来并没有觉得不适,等她的睡意终于过去后,再睁眼打量四周时,赫然发现这居然是她自己居住的客舱,而她就躺在铺着厚厚丝绒的床上,身上还盖着米白色的大棉被,又暖和又舒适。
“做梦了吗?”她不可思议地摊开手看了看,心里五味杂陈,怎么可能是梦呢?
她还清晰记得躺在地毯上的冰冷,记得全身被布条困住的酸麻和痛楚,还有那个男人带给她的恐惧和森冷……一幕幕那么真切,怎么可能是梦?
可要不是梦,她怎么一觉醒来,就好端端的睡在自己的客舱里,身上还盖着被子?
她可不认为那个男人会好心到把她送回客舱。
种种谜团,持续到客舱的门打开,她看到外面的人走进来的那一刹。
“纪、纪程然?!”
她猛地从床上跳起来,不敢置信。
他似乎也被她这样猛烈的反应吓了一跳,端着托盘的手一动,清隽的脸,挂着和煦温暖的笑意:“起来了?醒了就过来吃饭,我带了你最爱吃的培根三明治。”
“太棒了三明治——等等,现在不是说吃的时候。”粟薇薇反应过来,光着脚从床上跳下去,三两步奔到他面前,踮起脚尖捧住他的脸,上上下下吃了一顿豆腐后,终于确认,这不是梦。
“纪程然,你昨天去哪儿了啊?”她嘴巴一扁,鼻子一抽,豆大的泪珠毫无预兆的从眼角滚落下来。
一整天的担忧、害怕、恐惧……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宣泄。
她想了一个下午一个晚上的男人,心心念念牵挂的男人,就这样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如神祇降临,在她快要被绝望淹没的时候,又升起无尽的希望。
纪程然放下托盘,展臂把她拥入怀中,像哄小孩子一样拍着她后背,“乖,不哭了,我这不是没事回来了么?应该高兴才对,怎么好端端的又哭了。”
“你没有受伤吧?”她边嚎啕大哭,边拉起他的衣服查看,反正又不是没看过,索性把他外套都脱了,来来回回查看一遍。
“我没事。”
“不许骗我,你要是没事的话,为什么昨天都不来见我?”粟薇薇也不是好糊弄的,差点就把他的裤子都给脱了,直到门外传来一阵咳嗽声,抬起头,正好见到安心雅和林砚站在门外,正一脸惊恐地盯着她的举动,目露谴责。
粟薇薇僵住:“……”
炒了个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