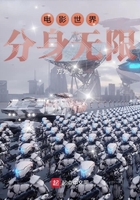审堂审到这种程度上,也真是为难了柔水港城这二个有头脸的人物。
亏顾塞鼎先前有知,知道田无勤的这案子不好审,才拉了邱掌柜一起来。
邱掌柜还以为顾塞鼎有眼光,看重他,那知他是把他拉来垫背的。
现在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地步,二个有头脸的人都说过要严刑逼供,却都被对方给驳斥了。顾塞鼎好生麻烦,说道:“那你说,不严刑逼供,怎么能使这个臭书生招供?”
邱掌柜道:“其实,方法是很多的,其实我也想严刑逼供,看看这个臭书生怎么在严刑下招供的?”
顾塞鼎道:“那我们的意见不是一致了吗,真是多此一举。”
邱掌柜却突然道:“你以为我吃饱了撑着没有事干,才会出此下策?”
顾塞鼎眼珠一转:“那你有什么下下策,说出来听一听?”
邱掌柜没有好气地道:“什么下下策啊,我现在是有上上策,总比什么个臭书生火烧赤壁的来得高明。”
顾塞鼎马上眉眼笑了:“那就听你的高明之处。”
邱掌柜这个上策说出来可是让顾塞鼎大吃一惊,邱掌柜说:“那就是把这个臭书生给放了。我看他就是浑身臭,怕把你这县衙也弄臭了。”
顾塞鼎虽是大吃了一惊,但还是很赞同邱掌柜的话:“大掌柜的,你这句话确是有理。书生臭,臭书生,我深有体会,真的怕他把我这清清静静,公公正正的衙门给搞臭了。”
邱掌柜逼进一步:“那你还不快把他放了?”
“放是可以的,可总得有个口供,比如说这臭书生真的没有放火烧死的事。”顾塞鼎这句话可是憋着一股气,要不是邱掌柜说这句话时,对他直眨眼,行动还是那么鬼鬼崇崇,他早就对邱掌柜光火了。
他们是有多年的朋友了,行事说话都有一种默契,他知道邱掌柜说这句话肯定心中有鬼。
田无勤跪在堂下只是听他们两人在自说自话,根本没有向他问口供的行动,心中好生纳闷,这县衙的审堂过案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当然,他也听到他们一会儿他说要将他严刑逼供,一会儿又是他说要将他严刑逼供,可到头来还是没有这样做,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在搞什么鬼名堂。而且他作为秀才,也知道严刑逼供的厉害,也最痛恨官府用这种严刑逼供的方法,屈打成招。现在看这两个家伙已是说要将他无罪释放,可是喜出望外,眼泪鼻涕都快要出来了。一面又有点得意,他毕竟是秀才,知道律法,想必这二个家伙也知道朝庭律法的厉害,不敢知法犯法,对他屈打成招了。可是跪了那么长时间,双脚可是跪得酸痛了,心里很是不爽。
邱掌柜既然同顾塞鼎大人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就拿着鸡毛当令箭般对着田无勤道:“臭书生,先站起来,先站起来,这么长久让你跪着,没有拿条凳子给你坐,真是老朽的疏忽了。”
话说得漂亮,手脚去不见动,田无勤还是先跪着。他叫他站起来,他就能站起来,那他田无勤也在这里好设话了。
田无勤没动,邱掌柜却动了。他走到田无勤面前,拿着一张供纸,对着田无勤说:“大秀才,你只要在这张纸上画了押,就可以无罪释放了。”
有这么容易的事啊?田无勤心中一动,怕不会是诱供吧?继而又一笑,这烂眼糊也太少看人了,他是秀才,会不认得字吗,这下,只要拿过邱掌柜手中的供纸,一看不就明白了。
田无勤虽然不能深知官场中那种弄虚作假的伎俩,但一张含糊其词的供词绝不会有欺骗人的把戏能瞒过他的眼睛。
“那我看一下可以吧?”
邱掌柜象看穿了他心中所想的那样,笑笑道:“当然可以。你可是秀才啊,什么东西能瞒得过你呢。”
田无勤拿过供纸一看,这黑纸白字的写得一清二楚,简单的一句话说,他田无勤与草地放火烧死二个人的事一点也没关系,也就是说草地中发现的二具尸首确是另有死因。不过,田无勤放火烧草地没有经过官府的许可,烧了草地后,还殃及无辜烧了柔水港城几家民居,那是罪不可释。本来要打他大板,但看在他曾是秀才的份上,从轻处罚,就让他在牢房里多呆几天,以似凭罚。
这样的一份供纸,合情合理,田无勤还觉得有点太宽大了他,当即是感激淋涕,高高兴兴,百般放心地在供纸上画了押。
邱掌柜见他画了押,也高兴地道:“这下我们也对本城民众有个交待了。”
事情就这么简单,田无勤这样的审案过堂,就好象是去看了一下县衙大堂一样,就被县役押着重回了他坐的牢房。
顾塞鼎大人一直看着,对邱掌柜所做的事一点也不在乎,等邱掌柜将事办好,他突然问道:“邱大掌柜,你心中另有小戏戏吧?”
邱掌柜被顾塞鼎问得一呆,当即道:“书生好糊,但大人毕竟是大人,我这小把戏怎么能瞒得过大人的金睛火眼呢?”
顾塞鼎嘿嘿奸笑道:“我能同那个书生比吗?我从来就不能同书生比的。我天生就是当官的料。”
邱掌柜赶紧点头哈腰道:“那是,那是,大人是天才吗。”
顾塞鼎也不脸红,说道:“邱掌柜,那你说说你的小戏戏是怎样的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