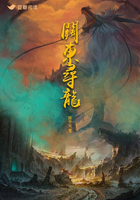从上海坐船到天津需要一天一夜,大约是次日早上到达目的的。幸好赵汉业不晕船,只是坐久了稍微感觉有点眩晕,比那些把苦胆都差点吐来的人强多了。这艘船叫“顺天号”,是英商太古公司的客货两用船,可是吨位并不大。头等“大菜间”只有六个舱位,每两人一间。这种票很难买,一般都是很多天前就预定完了。剩下的全是二等舱,四人一间,分上下铺。跟坐火车比起来,活动范围要大得多,可坐可躺,还可以到甲板上逛逛,一日三餐也很不错,只要不晕船,这样的旅行还算比较舒适的。
同舱还有两人,一老一少,听口音好像都是南方人。开始彼此都无交谈,到了下午互相渐渐攀谈开,老的是去天津省友,少的则是去投亲谋职。这几日奔波劳顿有些疲劳,赵汉业简单应付几句便躺下休息,不一会沉沉睡去。不知睡了多久,突然被两人说话声吵醒。赵汉业也不便发作,毕竟现在还是白天,别人都要正常活动的。原来那个小伙子刚从外面回来,见到几个茶房正在过道里邀人兜搭子,谁有兴趣都可以入局打几圈。赵汉业知道其间的门道,这里通常“有腥”,说白了就是一个骗局。老者显然也没什么兴趣,懒得应声。见无人作答,小伙子讪讪的回到自己床上躺下。
次日清晨,船在塘沽口停了下来,等了好久也不开。问了船上其他人才知是海河上冻了,轮船开不进去。虽然破冰船开了一条航道,但航道太窄仅容小船通过。轮船上旅客需要下船步行一段路,再转乘驳船才能到天津。旅客中响起一片叫骂声,但已经有人在往下运行李,其他人赶紧去甲板上排队。
赵汉业跟着最后一批人走下舷梯,岸上已挤满了旅客。有的人身边放着大小的箱包行李,在寒风中缩着脖子瑟瑟发抖。等人都下来后,所有旅客由太古公司的人带领,肩上扛着各式行李包裹,排成两列纵队向前鱼贯而行。孰料没走多远就是一处日军哨卡,大家只好把行李再放下一个一个接受盘查。北方的敌兵犹如北方的天气,较之上海的同行更加冷酷严苛,旁边站着一位形貌颇为猥琐的翻译,却是一副傲睨得志的表情,堪比在主人翼护之下张牙舞爪的恶犬,愚蠢和招摇几乎都写在脸上,大概以前也属于层次不太高的人物。
赵汉业冷静应对,安全过关,又随众来到一处码头。码头上停着几艘旧驳船,想必就是太古公司派来专司转载旅客任务的。每条船仅能容纳几十人,赵汉业随便上了一条。人上满了,船驶离码头。驳船设备极其简陋,虽有遮蔽却是四处透风,寒风从各种细缝钻进来,吹到身上仿佛能把人冻僵,窄窄的河道两边结着厚厚的冰,河道里也浮着不少冰块,让人有种置身冰窟的感觉。透过窗玻璃向外看去,两边岸上稀稀落落长着枯黄色的芦苇,冰上有几个孩子在追逐嬉闹,有的伸手去捞河道里的浮冰,实在让人看得提心吊胆。
大约两个小时后驳船驶入英租界,旅客纷纷下船。赵汉业提着行李箱从船上跳下来,踏上这片阔别了四年的土地。看到有客船到港,码头上等着的黄包车夫一窝蜂围了上来。赵汉业登上一辆黄包车,吩咐道:“去劝业场同祥绸缎庄。”
赵汉业不知道这样做到底对不对。从公的方面来说,他一到天津应该首先联络天津站相关人员;而且除了实在无法避免的情况外,情报人员不能跟工作以外的任何人发生频繁密切的接触,至亲好友也不能例外。道理很简单,特工平时也有很多例行事务要处理,如果整天生活在一个屋檐下,这些活动根本瞒不住。自己未经许可擅自回家,这种行为绝对是违反纪律的。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开战以来,与家人一直相互音讯隔绝,存亡未知。赵汉业实在无法等到交待完工作再来探望家里,此刻已顾不上什么纪律了,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父母更重要的吗?他们到底怎么样了,这个问题一年多以来一直萦绕着他,现在马上就要到家了,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结果呢?越是接近答案,他越是觉得心怦怦直跳。
一个小时后,黄包车停了下来,赵汉业胡乱掏出一把钱塞给车夫,调整了一下呼吸,定了定心神,向绸缎庄大门走去。
柜台里站的是一个陌生的胖子,赵汉业心凉了一半。
胖子见赵汉业有点派头,又是坐黄包车来的,热情的招呼道:“这位先生要点什么。小店有上好的杭绸,价格绝对公道……”
赵汉业挥手打断他:“我找赵掌柜。”
胖子有点不悦:“这里没有赵掌柜。”旋即会意,说道:“您找的是以前的掌柜吧?他把铺子顶给我了。”
赵汉业问道:“他现在人在哪?”
胖子摇摇头:“这个我可不知道,拿了钱人就走了,谁还管那些事啊。”
赵汉业又问道:“账房和伙计有没有留下的?”
胖子道:“账房老周也跟着走了,奥,还有个生子。生子!生子!”他朝后面大声的喊了两嗓子。
一个小伙子腾腾腾跑了出来,一看面前站着的是赵汉业,嘴巴一咧,眼泪竟然下来了:“少爷~~”
赵汉业上前用手按着他的肩安慰道:“生子,不要哭,发生什么事了?慢慢说。”
生子抹了抹眼泪,抽抽噎噎的说道:“二十九军走后治安没人管,一群混混来抢布,还说要烧房子,老周叔被打伤了,叔也气病了。后来日本鬼子来了,一个叫王竹林的让叔参加他们的新商会,叔说大不了这个铺子不开了,绝不当汉奸给老赵家丢人。王竹林就向日本人报告,说叔是抗日分子,要日本人来办他。幸亏米铺唐掌柜向叔报信,叔连夜把铺子顶了出去,带着婶跑到陕西宝鸡姑爷那里去了。”
胖子品出来味道有点不对:“你介倒霉孩子说嘛呢?谁是汉奸?参加商会就是汉奸?不参加行吗?”
生子显然很怕他,立刻吓的不敢说话了。
听到这里赵汉业反而很高兴,虽然家里接连遭难,破了一大笔财不说,父母也被逼背井离乡,但现在起码知道父母都还安好,单凭这点就值得高兴了。在战时这远不是最坏的结果,只要人平安比什么都强,至于钱财都是身外之物,不值得为之惋惜。姐夫在宝鸡县政府做个小官,父母过去肯定不会吃苦的。父亲是个急脾气,留在沦陷区就算能低眉顺眼的活下去,他自己也会暗自憋气,这种被人压着的滋味可不好受。去大后方虽然远了点,心情倒舒畅得多。
赵汉业掏出两块大洋塞到生子手里:“好好收着,别乱花,过年回家交给你娘。唐掌柜那件事以后别跟任何人说。在这好好干,我走了。”
生子嘴巴又咧开了:“少爷~呜~呜~呜~”
赵汉业笑道:“你哭什么啊,真是的!”
生子带着哭腔问道:“少爷,你上哪去?”
赵汉业想了想答道:“我去宝鸡找他们。”
临出门前,赵汉业忍不住又仔细打量了屋里的陈设。毕竟自己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年,一砖一石一几一案都承载了多少童年的回忆啊。在自己还够不着柜台时候,就常常站在板凳上帮父亲算账;有时候费尽心机潜入柜台偷出两个大子,跟小玩伴跑出去买关东糖吃……可惜从此以后这里跟自己不再有任何关系了,它的主人是眼前这个洋洋得意的胖子,可是这些跟父母的平安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想到这里,赵汉业心里释然,迈开大步走出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