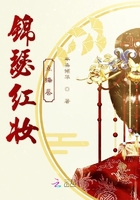婢子前来送点心,敲门无人应,推门而入,但见沈素期瘫倒在地上,“啪”的一声,手中托盘摔到了地上,点心掉了一地。
荷花池深处,池靖卿将适才发生之事粗略讲过,李元略微思索,应道:“据闻王爷你此次谋反之消息传了出去,引起了不小的骚动,部分百姓站在你这边,且又将你与池靖远的身世拿来对比。
皇位受到威胁,池靖远必定心急,那人多半是池靖远的,但轻松潜入了王府无人察觉,也说明了王府戒备不严,此处乃是我们的本营,若这里出了问题……”剩余的话意会神传,不必言明。
池靖卿缓缓点头:“若是池靖远的人还好……”
“二王爷,二王爷……”
话未脱口,只听不远处传来呼唤之声,由远及近,声音带着焦急。
池靖卿脑海中浮现沈素期独自回房的身影,神色微变,起身道:“先生,我去看一看发生了何事,之后的事情我们晚些再议。”
李元心中打趣,若再留下去,怕不知他的心飞到了哪儿去了,摆了摆手,示意他快去。
婢子找到池靖卿,禀报了一半,他便恨不得生出翅膀似的,朝着清心阁疾步走去。
烈日炎炎,清心阁最最适合夏日居住,此处乃是整个二王府中最为凉爽的院落,婢子平常也不从此处通过,所以清净得很。
现下清心阁却成了王府中最为喧闹之处,婢子端着凉水进进出出,从外面请来的大夫为沈素期诊脉之后,冷汗顺着额头往下掉。
一道身影快步走了进来,顿时,闷热的房间清凉了许多,甚至有些发寒。
婢子大夫让出路来行礼,池靖卿大步走到床榻边坐下,但见沈素期面色发白,唇角干裂,额上敷了一块毛巾。
眉头一皱,沉声问道:“她怎么样了,几位大夫?”声音略带戾气,几位大夫面面相觑,皆不愿做那个首当其冲之人。
沈素期的身体是何状况,不必几位大夫明说,他心中清楚,看着沈素期发白的面孔,半响,在大夫们终于决定出让谁先出面之前,开了尊口:“你们都先下去吧,若秦公子在府中,让他过来。”
大夫们如获大赦,以最快的速度出了门。
池靖卿拿下毛巾,她洁白的额头沾着水,触手一片温热,将毛巾放在冷水盆中,再捞出来拧一拧,重新为她敷上。
一系列动作之后,面具人也到了。
见他亲自照顾,心中略有感叹,快步上前,道:“沈姑娘如何了,毒素发作了?”
池靖卿目光未从她身上离开,应道:“一半是毒素,一半是受了惊吓,”话锋一转,“赵子威走之前可有将压制的药物交到你手里了?”
赵子威走得又气又急,压根没有与他多说什么,气头上又忘了将药交给他。
他语气急切,且面色严肃,此时面具即便再想打趣两句,也断不会挑这个时候往枪口上撞。
从袖中拿出药,道:“赵子威走之前将药交给了我,随后我便一直放在了身上,忘了交给你。”
此时他哪还顾得上这药为什么一直没有交给他,池靖卿拿到药,立即喂了一颗给沈素期,收起瓷瓶,道:“如旭……你先出去吧。”
他话中的停顿,不难注意到,本欲问一问赵子威还有无叮嘱什么,但他想要了解沈素期的症状,还要假借外人之手,他如何问得出。
面具轻咳一声,似无意提起:“赵子威走之前曾说过,若毒发,这药喂下去,不出一时辰沈姑娘便会醒过来,不用担心,”瞄了他一眼,“若无其他事,我便先出去了。”
面具出门后,池靖卿握着沈素期的手,盯着她看了半响,忽地,俯身在她额上落下蜻蜓点水一吻,抬起头时,黑眸掠过阴鸷。
面具倚在门前柱子上望风,忽地听门吱呀一声轻响,回身看去,挑了挑眉:“怎么出来了?”话音落,才发觉他神色有异,不由站直了身体。
池靖卿一边走下石阶,不答反问:“李先生人在何处?”低沉的声音带着此时不应有的冷静。
面具微怔,旋即应道:“人在滕春院书房。”李元难得的正经,似预料到了什么。
池靖卿只交代了一句,便朝滕春院走去。
李元见他未留在清心阁照顾沈素期,反而出现在自己面前,竟半点也不意外,只对他招了招手,道:“王爷你来看一下,此处是琼玉城,若从此处一路向京城,途经茯苓、拢德、昭安、凉城四座城池,之后便是黄河流域。”
过了黄河,便离天子脚下仅一步之遥。
池靖卿粗略看了一眼,点了点头:“黄河之后的且先不去理会,茯苓城最近,先攻此处。”修长手指在地图上一点。
李元略有迟疑,沉吟道:“此座城池不可强攻,茯苓汇集了成百近千种药材,若此处遭到破坏,只怕会影响了大越的药道。”
药材不可破坏,城池还需占领。
池靖卿负手立在桌前,目光落在茯苓之后的城池上,半响,道:“茯苓城城主年老,几个儿子一天到晚勾心斗角,谋算着如何继位,从此处打开缺口并不难,”
话锋一转,“只是茯苓之后的拢德,城主是个效忠皇室的、认死理的人,若谈判不成,必要时还需动用武力。”再之后两座城池,倒也无特别之处。
效忠皇室四字一出,李元更显轻松,意味深长道:“若当真效忠皇室,那应认皇室嫡系血脉才是,池靖远终究属于旁支,成不了气候。”
池靖卿眼底掠过阴鸷,声音透着淡淡寒意:“池靖远做事早已惹得人神共愤,收服其他两座城池并非难事,”语气略带轻蔑。
他从地图上移开目光,看向李元,面色略带敬意,沉吟道:“先生,我即刻动身前往茯苓,还请先生留在王府坐镇,攻下茯苓城后,再派人将你们接过去。”
声音低沉,毋庸置疑。
沈素期此次险些遇害,使他意识到应趁早夺回大越,即便不为了自己的野心。
李元眼底掠过赞赏,道:“一切皆听王爷的,若有需要老夫的地方,王爷便传信过来,老夫在官场多年,别的没有,只剩下些经验了。”
池靖卿微微摇头:“先生在官场多年,此言着实过谦了。”唇角微勾,话锋一转,“如旭仍不是个安分的,这阵子便要叨扰先生了。”
面具跟着李元讨酒喝这事儿还历历在目,李元见他面色稍缓,不以为意地笑了笑:“老夫此次可只带了些秦酒,秦公子来了只怕也只得与老夫喝些陈年佳酿,他若不嫌弃,要多少有多少!”
二人相视一眼,皆摇头一笑。
池靖卿说动身便动身,未有片刻犹豫,与李元打过一声招呼,便纵马扬长而去。
李元在清心阁院门找到面具,后者听闻池靖卿出了远门,啧啧了两声:“果然还是美人更使人有动力,但靖卿他单枪匹马的,总有疏忽的时候,这边沈姑娘醒了之后,我们便赶过去。”
算一算时间,沈素期再过半个时辰便会醒了,届时知道池靖卿去了茯苓,定不会再待下去。
李元下意识摇了摇头,且看着他:“这可不成,二王爷若要带上沈姑娘,便会等她醒过来了,左右再怎么着急,也不差这一个时辰,且他还未见到沈姑娘平安醒,即然现下走了,便不希望沈姑娘跟着。”
暗道着面具跟在池靖卿身边这么久,该不会连这点事情都没有眼色。
面具暗道这老先生莫不是喝多了过来的?
唇角微抿,被银面恰到好处地遮住,盯着李元看了半响,毫无恭敬地道:“先生,您看得出靖卿是何想法是好,靖卿担心沈姑娘的安危是真,但他单枪匹马去那人生地不熟之处,能否成功暂且不谈,若路上遇上了池靖远的人,他一个人多少有些应接不暇,我还需尽早赶过去。”
言下之意,即便沈素期不方便跟过去,他势必要随着池靖卿一同前去。
李元以一种意味深长的目光看着他,摇了摇头,道:“秦公子啊,你跟在二王爷身边这么多年了,他办事谨慎,你应清楚才是,若没有万无一失,他岂会贸然前去。”
他跟在池靖卿身边这么多年,难道连后者是何性子都不知吗?李元这话乍一听没错,但细想之下,又不是没有反驳之处。
面具点了点头:“先生更能体会到王爷之意,沈姑娘应快醒了,我进去看看,晚些再去叨扰先生。”
若是平常,面具还会抓着那不妥之处不放,但现下情况不同,更不适合他打趣。
面具快步回了房间,可还是晚了。
沈素期靠在床头,看了一眼大步买进来的面具,秀眉微蹙,抿了抿唇,斟酌了好一会儿,才问道:“秦公子,现下什么时辰了,靖卿他用膳了吗?”
用膳不用膳不打紧,重点在于她醒了过来,屋子空荡荡的,她昏迷之中还隐约听见了他的声音,醒来却未见到人影,所以自然有些不安。
面具隔着银面摸了摸鼻子,不答反问:“沈姑娘适才晕倒了,眼下正是晚膳的晚膳的时辰了,不妨沈姑娘先用膳?”
面具越是回避开,便越是可疑,且他自己还未意识到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