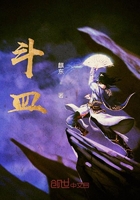她自己也不大清楚自己究竟是为什么而会这么轻易的掉泪,是为了因子刚才行为的粗暴?是因为自己一向都深信着的因子突然的对自己那么不友好?皑皑得不到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答案。她又怕自己这些不争气的眼泪被因子看到,如若那样的话她怕会被因子误解得更深,甚至有可能导致两个人关系的冰冻,这是皑皑目前为止还不想面对的结果。
她现在就因子这么一个贴心能说得上几句真心话的朋友了,另外的朋友不是没有,只是她们都有了自己的男朋友,都有了一个固定的倾诉撒娇依靠的对象,而自己呢?以自己的话是到目前还没人愿意问津。孤独孤独!这个讨厌的魔鬼整天的环绕在她的身边,她有时候深夜里醒来,看到同学们还在忘我的发着短信,内心的孤独感便会象闪电般剧烈的释放出来,拷灼着她那颗并不象她外表那般坚强的心。
她也曾多次设想过自己未来的男人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她也真正的在梦中构绘出了这个男人的具体影象,她看到他站在寝室的大门口,手里抱着象上次马云要送给因子那一个样的玫瑰花,一辆小轿车停在她的旁边,车门打开着,只等着她这位高贵的公主坐上去。每次梦见这些事情的时候,皑皑醒来的面孔总是育着笑意的,那一天的心情也会是很光明的,就好象她真的在那一天经历了这样的事一样,她会跟每一个和她打招呼的人亲切的聊上两句,同学要她帮着到开水房打壶开水她也不会象平时那样的推三拖四。因此在那些个天,她是最平易近人的,也是最让人们觉得她神经有问题脑袋周期性运转而造成的结果。
皑皑悄悄的走出了寝室,外面的阳光见了鬼似的匆匆的隐没了下去,只剩下了西天里一大片懒散的浮云。不知名的飞鸟结成了一大伙,在几百米的高空默不做声的往远处的山岚飞去。天地间没有起风,远处的工厂那高耸入云的烟窗疾吐出来的浓烟遮住了大半个校园,整个校园一片青灰。没有生气,走动的人们象在地狱里为了投上一个好胎而作着最后绝望而又痛苦的挣扎,一个一个的随着时间的前行而匍匐着前进。现在连因子都有了自己的男朋友了,皑皑心里很失落,甚至于有点悲观,她已经完全的将自己归入了那一类讨人厌弃、脱离于人世情感之外的人,她觉得自己被上苍给抛弃了,完全的给抛弃了,忘记了!“不!不能!我决不能这样的认命,孤独决不是我生命中的所有,即使是,我也要用我最大的勇气、最顽强的意志来打碎这个孤独,我不要孤独!我对上天起誓,我不要孤独!”
那晚皑皑在街上逗留了一晚,没有回寝室,当因子在睡梦中醒来习惯性的看向皑皑的床位时,那上面空荡荡的,她的被子依然跟早上叠好的那样整齐,静静的摆在靠窗户的那边,在那里对着月光,似乎正在悄然的盼望着她的主人快点归来。因子是清楚的,皑皑每天晚上都是第一个到寝室的,她从来就不会到外面去过上一个通宵,即使是周末,即使是大家都在网吧里疯狂的玩着游戏,聊着天,只剩下了她一个人,她也一定会安然的呆在寝室里,不会象今晚一样半夜还不归来。“是不是我刚才伤害她了!我也没对她怎么样呀?她一向都不是这么小心眼的。但,那又是什么让她这么晚了还不回来呢?她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希望不要是这样的!怎么说她也是我这两年里最好的朋友呀!再说,这次若不是因为我弄得她不高兴,她又怎么会逃走呢!我也真是,越来越小气了,这哪里象因子呀!好了好了,等明天皑皑回来,我向她道歉是了,我保证以后不那样对她了。菩萨,救苦救难的菩萨,你一定要照顾着皑皑呀!不要让她出事啊!”因子第一次一个人躺在这间诺大的房间里,因为没有了皑皑的呼吸声传来,她有了那种不适应的感觉。
莫科说他从北京学习回来了,想在明天见一见因子,因子埋怨的说:“你还记得我呀!每次打电话来都只是跟我的同学聊,把我搁在一边,若是不明白的人还会认为这电话不是打给我的,而是给她们的。”
莫科哈哈的大笑了几句:“我还以为你大方呢!原来也这么容易吃醋呀!真想不到,想不到!”
因子一时性急话语也就脱离了控制,“现在你后悔了是吧!后悔了还早呢,这次你就仔细的擦亮你的眼睛去细细的找吧!没有人拦你。”当这些话传到话筒的那一边时,莫科却不笑了,直弄得因子还以为他真的不喜欢自己了,就慌忙的扪住了嘴巴,用空着的手在脸蛋上狠狠的掐了几下。
“因子,认真的对你说,我就是喜欢上你了,我其实是很高兴你因为我和其他人聊天而吃醋的,这样说明你已经很在乎我了,我很荣幸,真的。”莫科的话语冰释了因子心里的顾忌与不安,这令她很感激这个男人,她侧着头以开玩笑的形式问:“很荣幸?你说的荣幸是我为你吃醋还是我很在乎你呢?”莫科也恢复了他惯有的轻松,“都是,这些都是!”
下午没课,因子同意了莫科札一起吃午餐,地点是在莫科住的那家宾馆旁。这个饭庄不是很有名,但这里的环境是很幽雅的,往来这里的人也大多都是本地的权贵,因此饭菜的要价比同行业的其他名店要贵出很多。莫科喜欢摆排场,他受不了在请客的时候将客人带到那些自己都看不起的地方,他觉得那样对他来说是在贬低自己的身份,而作为一个靠交际发家的人,最怕的事情就是被人贬低了身份。
皑皑一个上午都没有精神,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在桌面上躺过来的。因子疑惑的看着这个突然之间这么疲软的朋友,总想将自己的手探过去测量一下她的温度,但每次将手伸到她的额前时她都停了下来,她怕打搅了皑皑,怕这样又会扰恼了这个女孩。在课间换教室的时候,因子仍然象以往那样紧贴着皑皑走,皑皑象在做梦一样轻飘飘的,因子怕她会随时跌倒在地,因此也顾不了征求皑皑的意见,从侧面掺住了她的手,直到到了另外一间教室才放开她。皑皑抬起她那双有点迷离的眼睛注视着因子,她象想从因子脸上找出一个什么不好开口的答案一样,但又漫无目的,她最终还是微闭了眼睛一直酣睡到一天所有的课结束。
出了教学楼,因子不放心皑皑一个人回去,就想请她同她一起去应莫科的约,皑皑看好友这样,也就更加不忍心让她为难,其实她自己内心里也是极度的不愿意去当这个电灯泡,她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女人,别人不需要她去的她是绝对不会有想去的这个心思的。皑皑说她一个人回去没有什么事的,叫因子不要这么婆婆妈妈,要是这样,那她皑皑看来以后这大半生都走不出门谋不了生了。
因子固执,她说什么都不愿意让这个摇摇晃晃的人单独走,皑皑想拔开因子搀扶着她的手,但手一伸起来,随即又落了下去,她实在没有一丝一毫的力气,无奈,她只有依靠在因子的肩膀上。
莫科的车子慢慢的停了下来,因子没有发觉,也可能是感觉比较陌生不曾去在意他已经到来,她仍旧扶着皑皑站在楼下的台阶下。莫科看到这个情形吃了一惊,他慌忙从车子里跳了出来,几步快走靠近因子,伸出手去要接皑皑。因子也认出了莫科,看到他来扶住皑皑,也就心中轻松了许多。
“她怎么了?是不是感冒了?要到医院去吗?”莫科拿出对女性特有的关心问因子。
因子瞥了他一眼,似乎是不大欢喜他在她面前对她的朋友有这么的关心。但这种不高兴在莫科将皑皑扶到了车上放在后排坐位上,又反过来拉因子问她有没有什么事时在因子那似乎狭窄却也似乎宽大的心里隐逝了。
“你瘦了一点了!这段时间很辛苦吗?你在电话里不是说每天都很无聊、很轻松吗?”因子有点关心。
“哦!没有什么事。我只不过是不大习惯北京的饮食罢了!”莫科装出很自然的样子,他看因子站在原地不动,以为她是在替自己难过,就将手搭在了她的背上,温柔的说:“因子,你不要这么的担心。看到你这样子我真的很痛苦!好了,上车吧!我真的没有什么事。只不过,你这朋友,要到医院去吗?”莫科看了看睡在后椅上的皑皑,她正在那个柔软的地方做上了春天里的梦。
“她没有什么事。只不过是昨晚上没有睡现在困了罢了。我想先把她送回去,她这样子我不放心让她走回寝室。”因子有点无赖,但却更多的是对这个大学里最好的朋友的担心。
莫科点了点头,表示应允。他打开了副驾驶坐的门请因子进去,然后将门关了,自己饶过车子上了车。
车子在大学公寓前宽大的运动场停了下来,因子扶着皑皑下车,皑皑还在迷迷糊糊的说着梦话般的客套话,因子让她别说这些见外的东西,她就是不依,外人见到她的这副模样,多数上都会以为她伤了什么感情,躲在哪个酒馆里灌了个半死后被人掺了回来。
但她是不会理会别人怎么用异样的眼光看她的,她到是很喜欢这种眼光,她从这些眼光里能够感觉到自己已经从了焦点,而从为焦点人物这一向就是她的梦,她做这个梦已经很久了,她曾经还羡慕过那些在校园里为了爱情而威胁自己的女友要跳楼自尽的男女双方,她也曾经幻想着自己是某个富豪的情妇,一到周末,那个绅士就会开着漂亮的车子停到她的楼下,在众多的孤独者、爱情的贫苦者面前悠然的飘去。
她现在也是惹人注目的,她能够从她那迷迷蒙蒙的睡眼中微微的感觉到,她也能够从她好朋友的匆忙中感觉到,她的好朋友,哦!还有她的好朋友的那个优秀的男朋友,大概是担心她的,他们大概是在想为她保住面子,让她那平日里平静柔和的淑女形象能够不被她这个白日里的幽梦破坏个干净,所以,他们掺着她迅速的离开了这片她第一次引人注意的苍白无力的操场。
皑皑想喝住他们,她想告诉他们不要这么快将她带回那个孤孤单单、清清冷冷的房间,她不喜欢这样,从昨天夜晚起,从她知道自己唯一的朋友有了男朋友起、从她看到了自己接了好朋友的他的电话引起了好朋友的不快起她就开始不喜欢这样孤单一个人了,她决定要改变这种尴尬的处境,她要与孤独斗争,她要杀死孤独,杀死一切心里的不快和伤楚。
而现在,在这个操坪上,她不仅终于过上了一把焦点瘾,她还拥有了别人的话语,别人用来构绘她的思维,她还拥有了别人的记忆。她在这里不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无足轻重,不觉得自己平凡无奇,不觉得上帝已经将她抛弃在了快乐和美好的门外。她喜欢这种感觉,真的,她想对这两个不理解她的感情的人大声叫喊,让他们滚开,让他们不要管自己的是,告诉他们其实他们不是在帮自己摆脱羞辱,他们是在付与她羞辱,在直观的向大众宣昌的羞辱,她愤怒的想摆脱这些个人,她也确实是用了浑身所有的力气,但她还是被人拖进了楼道,拖回了寝室。她几乎、差点绝望,她也是很绝望了,虽然没有人能听到她的声音,她那些发自内心出自肺腑的声音,但她确实是绝望的了,毕竟她已经回到了这个可怕的,会让她更为孤独无靠的房间,象往常一样,其他的人都不在里面,只有他们两个,哦!不!这回是多了一个男人,而这个可恶的男人,他将残忍的将她维持在孤独的外围不让她进入其中面对苍苦的她带走,最后,将她一个人留下,让她切底的不知所措,让她独自在这个清冷中啜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