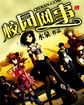我点头道:“我懂。”
“那你真的不管我和湛郎的事了吗?”西半芹可怜巴巴地看着我。
我默然吐出四个字:“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西半芹松了口气,其实我想说,若不是看在那药方的面子上,我早就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走了,何须如此费力。
若那药方真和红颜劫有关,到时候一定向司空易讨要报酬,也不枉我为他如此劳心劳力。
吃完饭,我回到房间瘫倒在床,现在整日里为别人的事忙碌,睡也没睡好,皮肤也变差了,我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叫下人打来热水,将门栓紧锁后,把人皮从脸上揭了下来,又尽数将身上衣服脱去,沉进了浴桶中。
不知过了多久,有仆人敲门:“公子,公子。”
我迷迷糊糊,答道:“何事?”话一出口,发现声音有些暗哑。
“公子,天黑了,需要点灯吗?”
我这才睁开眼,感觉浴桶里的水早已凉了,入眼处一片漆黑,看来在我沉沉睡去的时间里,太阳下山了。
“等会儿我再唤你。”
“好的,公子。”那仆人答话后就再也没有出声了。
我从水中站起,因为泡得太久,身上皮肤都有些皱了,一出水,一股寒意袭来,我忍不住打了个冷颤。
我正打算跨出浴桶,突然传来敲门声,接着是司空易低沉的声音:“阿蓟,在么?”
我一阵手忙脚乱,不过片刻,想起房门紧闭,门栓已插,有什么好紧张的,索性一下子坐回水中,冰冷的水让我的神智一下子清醒过来,我清了清嗓,问道:“司空,有事么?”
“今日的血还没给你。”门外传来司空易的声音。
我深深叹息了一声,面对如此敬业的献血者,我只能说自愧不如。扫了一眼放在床前矮柜子上的相思豆,因我悉心照料,又每日喝着人血,已经长得枝繁叶茂,格外壮硕,老的叶子上又抽了新芽,一副生机勃勃的景象。
我急忙道:“我现下有些不方便,麻烦你放在门口,我就去拿,多谢。”
听到门口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一会儿,只听司空易道:“放在门口,记得拿。”我应了一声,以为他走了,刚想站起来,只听到他又说道:“夜深水凉,早些出浴才是。”然后脚步声远去,这次是真的走了。
我感到有些窘迫,毕竟身上未着寸缕,虽隔着一道门,但那声音离得十分近,我感觉耳朵都烧起来了,急忙出浴,擦干身子穿上亵衣,收拾整理好,戴上人皮面具后才打开了门,门口果然放着一个小瓶子,我弯腰捡起,又叫来仆人点上灯,将浴桶搬出去,将房间清扫了一阵。
我关上门,立刻将脸上的人皮面具扯下,才坐到桌旁。虽有白玉膏护脸,但总这么戴着也十分不舒服,整张脸感觉都不透气,天天憋闷着,因为我从没有离家这么久过,所以这次戴人皮,也算破了往日的纪录。
我拿起司空易送来的小瓶子,打开瓶盖,一股腥气扑面而来。我将他的血和水兑好,缓缓倒入相思豆的花盆中,计算了一下时间,发现它很快就会开花了,心中暗喜,待它结果,就不需要司空易的血了。
这么一想,心情十分愉悦,毕竟我总怕他这么献血下去吃不消,何况受制于人的感觉并不那么愉快,这么想着,睡意袭来,懒懒散散地卸下面具,一下扑倒在床上,进入了梦乡。
第二日醒来,头有点疼,可能昨日在凉水里待太久的缘故,我急忙给自己开了副药,派西府的下人给我抓了药来煎好,面不改色地喝完了一大碗,送药来的仆人都看得目瞪口呆。
对于我这种从小在药缸里泡大的人来说,一碗苦药真算不得什么。
喝完药,我便兴冲冲地去找司空易,一来是谢谢他昨晚尽职尽责送来的鲜血,二来是跟他讨论说服湛文成的法子。
司空易没在住处,我问了伺候他的下人,下人也说不准,只说一大早就看他出去了,我无法,只得在园中游荡,找个人烟僻静处,好好理理思绪,想到那日夜游的蔷薇园,正是个好去处,于是随手抓了个小厮,让他领我去,他领着我在西府里七拐八拐,终于拐到了蔷薇园。
来时的路我早已忘记,还没来得及招呼一声,那小厮作了个揖一溜烟跑了,我叹了口气,只得作罢。
蔷薇园里花香袭人,白日里看那些蔷薇觉得更显璀璨夺目,一簇簇,一叠叠,拥在一起,把花枝都压得低低的,置身于一片花海当中,一切烦恼都随着花香远逝。
我就这样一路赏花一路往园子深处走去,直到有人唤我,我才回过神来,回头一看,竟是司空易!
“你们在这里?”我奇道。
他走近:“早起憋闷,想出来走走,想起你那日说的蔷薇园来。”
我见他神色无异,又想到他脸上戴了面具,根本看不出真实脸色,担心他胸中憋闷是失血过多所致,急忙道:“司空,我见前头有个亭子,我们到那里去坐坐。”
司空易点头称好,我和他一起,没走几步就来到了那个亭子。
待坐下后,我道:“司空,你摘了手套,我帮你把把脉。”
司空易也不多问,十分听话地摘了手套,将手伸了过来,我每次见他的手必会感叹一番,十指纤长,因常年晒不到阳光,又显得格外白皙。
我拉过他的手,将手指搭上了他的脉搏,半晌,我放下手,有些尴尬地说:“司空,你最近是否常感觉头晕乏力?”
司空易偏头想了想:“偶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