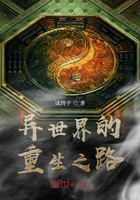“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去医院看望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三十五六的年纪,本来身体敦实,性格爽朗,可住院才三月有余,怎变得如此憔悴如此枯槁了呢?
待我问候、安慰了几句后,朋友长叹一声说:“谢谢你来看我。也许今日一见,就是永诀。”
“为何说得如此严重?”
“我不该去作放射性治疗,弄得身体元气大伤,如今癌症已全身扩散,自感有生之日不多了……”
我打断他:“不要悲观。就算是癌症,只要你豁达、乐观,再配合治疗,加强营养,也一样能好。”
他报以一丝苦笑:“问题是我心情不可能好。这几天我前思后想,越想越痛苦:‘文革’十年里我怎么写那些狗屁文章!”
“当时大气候就那样。谁不想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耐心劝解,“你作为新闻干事写了一些反映当时情况的报道,何罪之有?我看根本勿须自责。”
他神色黯然:“话虽这么说,可白纸黑字,一派胡言,我怎能问心无愧?”
我的这位朋友生前是某万人大厂的秘书,负责对外报道。“文革”十年里,他写了大量应时的消息、通讯和评论,这些作品中,当然免不了有肉麻的歌功颂德之词,有夸张的表功之语,也有尖刻的批判之言,但他本人绝不是那种刻薄阴毒、整人害人之辈,同他打过交道的人们都认定他是一个诚实宽厚、和善谦逊的好人。彼时彼地,写那样的东西是他分内的工作,完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说明不了他的品质和节操。遗憾的是,悠悠苍天,怎不借以年寿,让他有一个改正错误、提高认识的机会?
每每想起这事,我的心便不由一阵震颤。
我又偶尔在一本佛教经典中看到一则故事,说的是一位僧人写了一本宣传佛教的着作。他“凡心”未灭,成名心切,书稿出来后未经反复琢磨修改便匆匆付印。可当”生米做成熟饭”,他的认识水平、思想境界提高以后,才发现自己的着作,水平低劣,谬误百出,顿时愧悔无比,羞于见人,准备自杀以谢读者。
读了这个故事,顿觉一股寒流透过脊梁直冲脑壳,六月炎夏也让我打了个寒噤。
笔下有人格、寓品位,能见肝胆、观节操呵!
任何时候都不能为私利媚权媚俗。谄媚奉迎的文字,粗制滥造的作品,终究只能是纸张垃圾,让人憎嫌,让人耻笑;假、大、空、蒙或诲淫诲盗的精神鸦片,更是误人子弟,贻害无穷。有时文字留下的罪孽甚于歹徒的谋财害命,安能不慎之又慎!
吕不韦用借胎遗子手段,窃取秦国大权,固然可恶可鄙,但他在治学上的严谨仍然令人敬佩。由他主持编着的《吕氏春秋》出版后,曾布告天下,凡能增删一字者,赏千金。当然,如真有大作家、大学问家去琢磨挑剔,不可能找不出毛病,但这种一丝不苟自尊自信之精神,值得所有治学为文者学习和效法。
马克思的写作态度更令人崇敬。他深切地认识到,他的着作是人们的精神食粮和思想武器,任何错误和偏颇都将留下无穷的后患(若是因理解错误而造成祸患,责任不在马克思),故他对自己的任何一个论点都苦苦思考,反复推敲,甚或用十种不同的正、反面论据反复论证后才公之于世。难道我们是出笔成章、毫无谬误的天才吗?难道对自己的作品就不该多一点疑问多一点挑剔多一点比较多一点推敲吗?
何况,几千年的文明史,已经留下了多少光辉灿烂、精美绝伦的着作?如今世界上人口六十多亿,还将产生多少才华横溢、思想深刻的文坛高手?就拿科学巨人爱因斯坦来说,其聪明,其深刻,其文化水平之高,其思想作风之严谨,堪称世界一流;他的着作《相对论》无疑是一部科学巨着,至今世界上真能读懂的人仍然是凤毛麟角,可据一篇介绍外星人的文章说,“外星人”
认为《相对论》至少再修改三次,方接近真理(不要认为这是无稽之谈)。鉴于此,难道不该想一想,我们的着作有没有价值?还有没有错误?需要不需要修改?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是书生,是作家。书生、作家是红尘中人,不能不受尘世气候和环境的影响,不能不考虑自己的生活和发展。
但一定不能掺杂过多的贪欲,不能毫无主见地随波逐流。若确实是一时糊涂一时狂热,在“反右”斗争中写过痛打落水狗的檄文,在“大跃进”中写过亩产万斤的颂文,改革开放以后写过诲盗诲淫凶杀暴力的作品,该知错而忏悔,然后洗心革面,多做一些有益社会有益众生的事情,也算是立地成佛了。
许金坤
2006年3月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