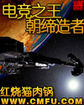“没错,是我。上次夜里要不是你那五十元钱,我就饿死在街头了。”不出景恺所料,他就是前次景恺上通宵时碰上的那老人。现今再看,白昼化妆的效果显比黑夜要技高一筹,皮肤通黑地提前行使夜晚职权吞噬白昼,唯一争气的发丝倒为其化妆师留下一缕银白。且这白重情义,讲义气,甘为恩人划舍青春,仅留衰老。景恺为这精神感动,对其莞尔一笑。
乍地一看,两人对视着笑颇有貌合神离之意,景恺想事深谋远虑,猜到这次定要跻身于国家的扶贫政策。刚想语出先行,却被自己的扁胃杀了气氛,闷得他只好改口换面支吾道:“你还没吃饭吧!我请你吃早餐。”那人一听到吃,显然是饿坏了,麻木的神情连口吃都忘了如何表达。
景恺对这一情形好生不快,也不管有无失身份,搭起他的肩就走。景恺这才发现,此人乞丐的名职与其实际不合乎。虽摆装一身臭样,却未曾从他身上闻到能使人窒息的气味,反是从他身上涌动着一股亲切的暖流。这暖流与当下天气的寒流相遇,给这冰封的冬日裹上一层厚重的和谐之趣。
他们来到一家小饭馆,闲许累了,景恺还是尊老先行,请那人坐下,自己方坐。景恺叫了几碗拌面,他处事多虑,一碗是为自身着想,剩余的为那人肚子服务。
那人狼吞虎咽的吃相吓坏了景恺,更吃吓了老板。好歹景恺被面前给吓,老板则被面钱给呵,景恺不做亏本买卖,迫想知道此人的背景来历,遂慰问着他:“老哥,怎么称呼?”
“我姓严,单名一个顺。”
“那严哥,您贵庚?”
景恺自以为用这文化口吻问能提高自己,贬低严氏。岂得严氏一反:“知天命有余。”
景恺出招不吉,被反戈一击,为避免虚荣忙道:“噢!”然后趁严氏继续埋胃时想那古语中“知天命”何解。惜景恺只对半百之前的古人略有兴趣,今次不巧撞上自己学识范围外那么一点精华,顿时束手无策。好比那群搞文学的人,叫他们搞数学,才华即刻不攻自破。一字之差而已,可遗憾当今社会搞文学就是比不上搞科学。这体现出当代青年的嫌老现象极其严重,朦胧的意识中,景恺开始了逻辑推理:既是知天命,就说明已近天年,也就是快死了。能知逝世之时,又不是昙花一现,景恺吃惊眼前这人是否神仙下凡。其好奇随他的胃口一起被扩大,又问:“严哥应该是个文化人吧!”严氏愣住,景恺以为他被噎住,忙递他一杯清水。严氏摆摆手继续埋胃。按常例,景恺这时已在网吧继而逍遥,如今摊上个累赘,只好怨天尤人。
一会,严氏的胃埋满了,他得到相应满足后,相反景恺却未满足,不论是发自胃还是出自慰。
“你对一个乞丐也很感兴趣?”
景恺被感兴趣,忙不迭地掩饰说明:“我没有那个意思,只是从你刚才回答我的问题中我觉得你挺有文化的。对你的来源也就——。”景恺摆出无奈的手势。
“你想知道?”严氏的口态诡异难辨,不知是陈述还是反问。
景恺也懒于理会,直说:“我想知道。”这只是他觉得理亏后应得的。
“老板,拿包红五叶神来!”
“你会抽烟?”
“嗯,略懂,略懂!”
“你读高中?”这话同样使得景恺再次不得要领,弃掉烦琐:
“高一!”
“你们学校允许学生抽烟?”
这第三次迷离,景恺总算是提纲挈领了,这口气是问句,便答:“这年代学校哪还有工夫管这个啊!管了也没用!”
“为什么?”
“你想啊!如果管我们抽烟,一个学生抽一次烟就被开除,抽两个开一双。那学校的经济来源靠什么?学生处又不是银行!”
严氏不以为然,凭他一己之见,即使没银行,纵然只要有个信用社就行,便语:“那学校不会就这么缺钱吧!而且那抽烟人数也只有少部分。”
“严哥,一听你这话就知道隐居多年了,简单地用我们现在流行的话来概述吧!叫‘哥抽的不是烟是寂寞’。”严氏显而被这“寂寞”给困住了,想自己抽了半辈子的烟倒抽出了个光棍,莫不予抽烟也同家庭纠纷同一属性,搞得好就缺胳膊少腿,搞不好就妻离子散。
景恺递上一根给严氏,为他点上寂寞,然后自己也跟着一起堕落。严氏口是心非,瞧这品味孤独的架势便知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为他而写,景恺自知无趣,只好一人打着查尔斯·狄更斯《雾都孤儿》的旗号浪抽寂寞。
“严哥,可以说说你的事了吗?”严氏吐出一团寂寞,点下一堆寂寞,看着一个寂寞,勾起一串寂寞,语重心长道:“姓名已说过,我今年五十八岁,广东佛山人。我有两个妹妹,她们在十八岁的时候就都嫁人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我这两个妹妹。因为家里经济条件有限,所以我只读到高一就辍学回家务农。二十岁那年我娶了个老婆,她是个文化人,不嫌弃我没文化没地位也没钱,我很感动。于是第二年我们便有了一个女儿……。”景恺认为这倒像在听罗曼罗兰的自传,若换作顾母在此闲聊,那这自传定会被景恺削为自灭。
“你在听吗?”
“呃,不好意思,继续。”严氏一眼道破景恺的心思,神仙算做成了心领神会。继而说:“在文革间,我的妻子被误为是反动派,被捕入狱,最后被革命人冤杀而死。我在悲痛欲绝的心情下带着女儿在一个挚友的帮助下,来到潮州一家厂里工作。然而,当我真正开始工作时才发现被出卖了,十八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工资连我一个人都养不起,最后,我女儿在饥寒交迫中离我而去……”说到这里,严氏搁浅着寂寞,嘴里哽咽着。这也让听惯了冗长话语的景恺得以存息。
严氏两眼的泪水经不起寂寞的考验,双落纵横。景恺见此一景,欲罢不能,欲慰又不愿,只好等他自行开脱。严氏不负景恺重望,擦干了泪,继而讲述着:“在经受失去双亲的痛苦之下,我决定回老家。经过长途跋涉后我回到了家乡,眼前却又是一幕凄惨的景象——我的父母双双过世,原因也是饿死的。家里的房子和土地也被他人利用非法手段给强夺了。后来,我到处流浪,以乞食为生,一晃过了三十年,现今已物是人非。今年是我呆在此地的第三年。”严氏的寂寞自怨自艾,景恺为自己的耳净自掘坟墓,能听得如此感人肺腑的故事,没有心服也有耳福。景恺的惭愧随感而来。
景恺顺势又抽出一根烟,点上。凝视着空气中缕缕散去的哀愁,心中激起无限感慨。严氏的经历让他知道:在同一片蓝天下,还有许多像他一样甚至比他更不幸的人都在顽强地生活着。从这些平凡人中间,景恺若有所思,他找到了生活对自己生命最深刻的含义——孤立在这世界上。
“我的故事满意吗?够不够感化你?”
景恺若无其事地笑了笑:“绰绰有余。”
“那能介绍一下你的事迹吗?”
景恺一听,甚觉自身经历与其作比微不足道,可也不想在这感慨中击落他人的兴致。于是,也让一根寂寞伴他遨回昔日的寂寞……
“讲完了!”烟落,事毕。景恺此时对网络的暇瘾已熬上心头。好似那被缠足的三寸金莲,本已一脚臭气,如今,放、走皆不能,只好等待中国封建礼教漫长黑夜的结束。可惜景恺作为现代人,对逝过的中国杳无兴致,便用现代口吻语出:“我去方便一下。”景恺这话显着的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鸿门宴》刘邦如厕被今人盗传,可怜严氏只上过高一,未能见识汉高祖作案的高深手法。刘家自鸣得意后继有人,千古未绝,一代狡诈得以传承,苦了项家唯我无双自以为高,挨到今天亦不变。
景恺善心未度,交完饭账后又递给老板一百元,嘱托他交给严氏。景恺目送老板将钱转给严氏。严氏接过钱后喃喃自语说了些什么,景恺不曾后悔,他知道严氏的身历要比自己悲惨得多,景恺看着严氏模糊的双眼,也模糊了双眼。他不愿再在这悲怆的情形下继续滞留,莞尔一笑,悄然离去。
景恺像雏鸟归巢一样自然,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网吧。疲惫的身体促使他忙不迭地找了个舒适的位置坐下来。经过刚才鲜为人知的捐款,景恺的脑子倒清醒了许多,困意全无。倒是在外呆得太久,寒风精神可嘉,景恺精神不佳,身体总是会不由自主地颤抖。
和往常不一样的是,景恺并未火速埋入网游世界。打开Internetexplorer,那浏览器的速度就像是二战时德国闪击波兰一样迅雷不及掩耳,对于除游戏外景恺最有兴趣的网上娱乐莫过于看电影。
土豆网名气大得可与顾父在家中的威信相比拟,但如今面对虚幻,相形失色,顾父的现实主义名存实亡。
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精神享受,景恺像是到站的火车,开始进入休眠状态。唯一与其不同的是:景恺要比它更富敬业精神,虽攀不上躺于棺材的死人了,但坐着连续睡上十一个小时也可以作盖棺论定了。
景恺扶摇起立,委屈的屁股已坚如磐石。难得太阳勤于自己的岗位,天黑了都迟迟不归,硬是让地下万物看着它脸红了才甘心。
景恺再一次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他暗自发誓再也不到什么偏僻的地方去独味孤寂,这该死的个性害惨他两次舍弃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红色印相。景恺忽想起他老人家生前曾说过:“你们年青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景恺却把希望托付给了一个素昧平生的“年青人”,不管怎么说,此时景恺只坚信吴运铎的警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旺盛的精力寓于健康的身体。”
来到一家沙县小吃,成语饥不择食,现用在景恺身上,算是有损他胃的尊严,想他平时在家被当少爷看作,一顿饭若荤菜的个数不达最小质数,他宁愿让胃受罪也不愿让舌尖受苦。这时的景恺堪不上朱自华,“不食嗟来之食”在菜谱的纸上司空见惯,一到餐桌便食空见惯了。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如鸿毛。景恺不愿在袁隆平的辱骂中含饿而死,放任自己的口舌对胃做自由落体运动。景恺到底是饿坏了,以至于当他付账时老板竟问他是否刚越狱出来。景恺触景生情,想到中国人的思想亦比中国的历史,古时便被禁锢,近代又被外人上锁,直到现代才被刑放。无奈这老板还停留在刑放初期,好比爱读书的低能儿,再怎么努力也长不了多少见识。纯粹的术语可称“井底之蛙”,还是那封了盖的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