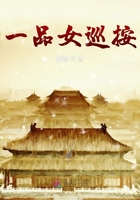“你胡说什么!”
刘府前院,此时可炸了锅。一高一矮,一斯文一壮硕,两个人扭打在一起,竟然谁也不让谁,谁也没有强过谁,皆挂了彩。
那个子高高瘦瘦,身着斯文长衫的是刘府的主人,刘先才。而那矮胖壮硕,却空有虚架子的,正是嚷嚷着要找人算账的季崇礼,季二。
刘先才虽看上去是个文弱的书生,可此时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子蛮劲,竟将季二按在了地上,额上青筋爆出,凸着眼珠子,恶狠狠地低语告诫,“你别忘了,我们可从没见过!”
季二此刻大有几分破罐子破摔的意味,不怵他,也不怵他的官帽,“姓刘的,当初可是你先找上的我。你要治我,你要翻脸,我就把事情抖搂出去,咱俩谁也讨不了好!”
“你闭嘴!”想起那件事,刘先才自然是怕得紧。一边死死地按着他,一边惊恐又疲累地喘着粗气,“事情,你办了。利,我也给你了。两边都结了,你还想怎么样!”
“姓刘的,别以为我不知道,银子从你手里头一转,打指头缝里流下去多少。这里头亏的帐,咱们是不是得好好算算!”季二不慌不忙,他没什么可怕的。
“要钱我可以给你!可你不该来!也不该说那些事!就从来没有那些事!”刘先才挣着脖子低吼,但手上的力道还是松了两分。
季二就势推开他的手,抓了抓领口,畅快地吸了两口气,嘲笑道,“早知道你会怕成这样,爷我就该早点来!”
说罢,他从地上爬起,装模作样地拍拍土,冲着刘先才啐了口吐沫,就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前厅,一屁股坐在了主位上,挽挽袖子,喊道,“茶!茶呢!给爷上茶!”
“家里没人,别喊了!”刘先才也是窝了一肚子火。才刚受了上官的数落,这下职回家又遇上这位爷撒泼,不知是走了几个背字。
“哼,想不到,你这个御史看着架子大,过得还不如我。”季二拍了拍坐着的半旧扶手椅,又敲了敲身旁半旧斑驳的杂木方桌,眼神四下扫了一圈,除了这套桌椅,屋里也确实没什么值钱东西。
刘先才此刻又是气短无力,又是沮丧无奈,索性一屁股坐在了门槛上,“两头受气,日子能好过得了嘛!”
“嘿,你也别难过,”季二无赖似的把脚蹬在椅子边上,欠腰伸手够了那半碟瓜子来嗑,“爷我也是没办法了,就‘气’你这一回。事情办好了,爷保证不再踏你们家门槛一步。”
刘先才闻言回头,看季二坐在了自己平时坐的位置,又是那样一个不招人待见的样子,他也懒得去计较,只想赶紧给银子轰人,“你要多少钱,直说!”
“爷不缺钱,爷要的是面子。”季二淬了嘴里的瓜子皮,二郎腿一跷,伸出小手指,自得地挖着耳朵,歪嘴道,“大理寺要辞了爷的差事,你得给爷保住。”
“大理寺的事情,我怎么管得着!”刘先才双手插袖,缩肩缩脖地往门上一靠,摆明了管不了,“谁给你找的这个差事,你就找谁去。”
季二就是怕他哥哥知道,才来寻的其他门路。如今一听刘先才这话,更是急了,“当年你们让我做这做那,等事情过去了,说不管就不管,哪有这样的!”
刘先才此刻也想明白了,那件事情都过去了多少年,走的走,亡的亡,早就烟消云散,连个影儿都不见。就算季二疯狗似的把自己咬出来,无凭无据,又能怎样。
他释然地合上眼,依旧坐在门槛上,半靠着门框,满不在乎地道,“诶,今天就让你看看,就是这样的。当年的事情两下里已经结清了,是,就算我扣了一千两,那还剩下足足四千两银子。四千两啊!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钱,躺着花都花不完,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有那些钱,你上别处再买个差事,不就行了。”
季二一拍桌子,“不行!爷就要这大理寺的差事!”
别看刘先才是个文人,他骨子里也是横的,一梗脖,叫起板来,“爱行不行!我管不了!”
季二气冲冲地过去,对着刘先才的后腰就是一脚,踹得刘先才在地上打了两个滚,哎呦了半天才缓过来。
“你疯狗啊你!我也是奉命办事,哪有那么大的神通,能管上大理寺的事情!”刘先才半坐半卧在地上,扶着腰,疼得五官都拧到了一起,“跟你说实话,钱,我也给不了你多少。门房里有几钱碎银子,后院东厢房柜子里还有五十两银票,你都拿走。还有,我这院子里的这点桌椅板凳,你都搬走,只有这么多了。”
“你办不到,可让你办事的人能办到!”季二跨到他面前蹲下,解开绑腿,正要把信从裤脚里拿出来,却又定住了。
季二顾虑重重。
他不是怕刘先才,而是怕刘先才上面的人。当年刘先才让他投信时,说是与同僚不睦,要告黑状,需要寻一个不相干的人来做这件事。可信投出去没多久,江州柳氏的案子就闹得沸沸扬扬,举国皆知。彼时刘先才只是一个穷酸的末流小官,连露出来的官服里衬上都打着补丁,可一出手就是四千两的大手笔,他更是心有疑惑。细细一想,只怕刘先才也只是个小小的马前卒,和他一样,用来冲锋陷阵,或是当炮灰的。
如今露了这封信,刘先才虽不能奈他何,可让刘先才上面的人知道了,又会否轻易放过?
季二思量再三,还是把手收了回去,把绑腿粗粗绑上,壮足底气,空口威胁道,“当年的事情,爷知道的比你多。爷要是过得不舒坦,咱们就鱼死网破,谁也好不了!”
刘先才以为他就是吓唬自己,气道,“破就破,谁还怕谁!”
可他看着季二那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却莫名的怕了起来。当年的那种夙夜惊惧的感受,好像又一次漫了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