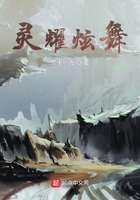还夕脑中空白一片,记不得自己是如何被抱上的马,更记不得自己是如何来到这个屋子里,只知道回过神来时,正有个郎中给她把脉。
“这位姑娘没什么大碍,只是极度疲劳,又受了惊吓,不用服药,休息两日就好了。”郎中说完,回头看了看神智已然清明的还夕,又随和地笑道,“姑娘,你要好好休息,不能再多思多虑,否则会伤及根本,要喝苦药汤啦!”
目送那郎中离去时,还夕才注意到了他身边的那个人。铠甲,佩剑,长缨,好像是个将官?
那将官一送郎中离开,回头见还夕正疑惑地看着他,就知道人已经清醒过来了,便立即乐得去敲了隔壁的门,“向将军,向将军,我们打猎带回来的那姑娘醒了!”
“向将军?”还夕低头自言自语,兀自思索,更为不解,“章台有卫戍将领姓向吗?”
才嘟囔两句,就听见门外传来一个无比熟悉的声音,“是我呀!”
还夕闻声抬头,就见了一个声音清亮,衣着却与此前截然不同的向彬向公子款款走来。墨发高束,剑眉入鬓,一身赭石短打,精干锐气,“咱们还真是有缘啊!短短几日,我都救了你几回了?”
向彬见还夕还在发愣,便无奈地挥退屋内屋外的护卫,把浑身的精干劲儿一卸,往门框上斜斜一靠,桃花眼一挑,妖妖娆娆地道,“这回认识了吧?”
还夕瞠目结舌,从没想过这样的一个纨绔少爷花花公子能够登台拜将。
然而,向彬早就习惯了这样的惊讶。当年他下战场回到安阳,那些旧日熟人再见他时也是这幅表情。英武阳刚四个字其实一直在他的心中住着,只是他有着不愿意担起来的担子,更不愿意一直活得那么累罢了。
他看着还夕灰头土脸的样子,不禁摇了摇头,“你也是真能跑,又从城里跑到这儿,难怪我前两天走的时候找你找不到呢!”
“你是将军?”还夕的反应始终慢上一拍。
“怎么?不信啊?”向彬直起身来,昂首挺胸,双目炯炯有神,倒真是意气风发,“小爷我可是北境一战的大功臣,如今拜轻骑将军。”向彬一边志得意满地说着,一边不屑地用手指着身后的空气,调侃道,“虽然比他怀文差了一大截,而且估计这辈子都追不上,但我已经很满意了。”
还夕正在疑惑间,就见另有一人从向彬手指的方向转出,不是怀文又是谁。
几乎同样式样的铠甲内衬,穿在这两个年岁相仿的人身上,一个就显得年少英姿,另一个却让人觉得另有一番的成熟睿智。
怀文在向彬身后略站了站,只冷冷看了还夕一眼,就转身离开了。
向彬也觉察到身后的人才来就走,有些尴尬地对还夕笑道,“你看,小心眼,生气了。”
殊不知,怀文只是默默地回房拎了一件干净外袍,便即刻走回来丢到还夕怀里,无甚表情地道,“驿站没有女子的衣裳,这件是新的,你将就一下。”而后就揪着向彬的衣裳,把那个恋恋不舍的花花公子给拽走了。
向彬被拽得步步后退,嘴里却忿忿不平地不依不饶,“没有女子的衣裳你就可以拿你的衣裳啊!我屋子就在隔壁,你为什么不去拿我的新衣裳!”
“你是定了亲的人,注意点言行。”怀文不怎么用力的一拉一推,就把向彬丢回了隔壁那间屋子,沉声道,“你这般模样,要是被三小姐知道,就有你的好受了!”
向彬一听‘三小姐’这三个字,登时浑身一个激灵,老老实实地坐在桌前,不敢再说,也不敢再动。
驿馆的主楼是三层的木质结构,隔音不佳。方才隔壁说了什么,还夕在这里听得是一清二楚。她很是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女子能将向彬这种纨绔子弟管得服服帖帖的?她真是该同那人好好学一学,免得以后再被向彬奚落。
低头一看怀中的外袍,想到怀文说的话,还夕这才意识到,自己现在定然是一副无比狼狈的模样。
当时从邹府出来时穿的细布衣衫被林间的树枝荆棘划开了许多小口子,有些甚至深深划破了里衣,刮破了皮肉。再抬手一看,指头缝里渍满了黑泥,手心手背没一块露着皮肉,沾满了薄薄厚厚的泥土,活像刚从泥堆里爬出来。一摸头发,蓬蓬糟糟,干枯结块,也就大致能摸出个当时发髻的形状。用手一抓,还能偶尔抓出些枯枝碎叶。从头到脚,不是沾了灰尘,就是沾了黑泥,脏兮兮的。
还夕看着脏手和锦衣形成的鲜明对比,忽然傻傻呆呆地笑了。心道,凭她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公然在皇城里转悠,也不会有半个人认出她来。
索性,就忘了那些所谓的“宏图大志”,从自己能做的做起。
正在发愣的空当,屋内的浴桶和水盆就已经被几名甲士拎来的水桶蓄满了。待他们拎着空桶离开,还夕立即上前放下了门锁,双颊涨红地抱着新衣裳靠门站着。
方才不见的窘迫羞怯,莫名地一下子涌了上来。